《紫荆论坛》专稿/转载请标明出处
王慧娟 | 紫荆杂志社主任编辑
2025年,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香港和澳门这两颗曾被殖民国家侵占的东方明珠,正以「一国两制」下特别行政区的全新政治身份,重新书写与祖国的关系史。这段80年的历程不仅是对战争的反思,更为现代国家治理与共同体认同构建提供了深层启示。
被侵占的双重性与空间政治的矛盾性
回顾历史,香港先后经《南京条约》(1842年)、《北京条约》(1860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898年)被逐步割让;澳门则自明代租借地演变为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下的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门」,在帝国边缘形成西方法权管辖的侵占地。这类空间具有鲜明的双重性:一方面,英国在香港推行「华洋分治」(如1888年的《山顶区保留条例》),葡萄牙在澳门确立「葡人治澳」体制,以种族隔离和法律区隔构筑殖民秩序;另一方面,两地又成为文明交互枢纽——香港维多利亚港一度承担著中国半数的对外贸易,澳门议事亭前地既矗立著葡国总督雕像,也是华人「茶话会」议政之所,权力符号与跨文化实践在此共生。
具有殖民性质统治香港的核心策略是「去主体化」和「去国家化」。英国在香港实行「没有代表的治理」,直至1985年才设立首个非官守议员占多数的立法局;葡萄牙在澳门长期推行葡萄牙化政策,禁止华人学习中文法律,甚至试图消灭中国传统文化。殖民代议制的虚置(香港)与文化同化的企图(澳门),终究未能根除华人的文化根基。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言,霸权的维持不仅依靠强制,更依赖文化认同的建构。殖民当局的文化霸权在抗战烽火中遭遇了根本性挑战:1941年香港保卫战,由600名香港华人组成的「香港华人军」(又称「香港华人集团军」)在黄泥涌峡与日军血战,他们身著英军制服,臂章上却绣著「保家卫国」的中文标语;1942年,澳门镜湖医院藉「中立区」之便,救治伤员、培训医护人员、秘密转运物资,支援中山游击战。这些行动表明,当民族危机超越殖民边界时,华人居民的身份认同便冲破了殖民当局设定的属地公民框架,回归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明母体之中,也为后殖民时代的「去殖化」——如香港更换步操、澳门强化爱国教育——留下历史根脉。

从被动包容到主动建构的民族身份觉醒
战争的残酷,反而促使港澳华人社会超越殖民边界,自发形成民族与文明的「想像共同体」。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与文明的保卫战,它迫使港澳居民在殖民国家侵占地居民与「中国公民」的双重身份中作出抉择。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香港各界踊跃发起救助活动,形式多样:上流社会举办各类餐会、舞会、赛马会为难民筹款,基层民众则以卖花、街头义演、逐户募捐等形式筹款。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香港学生赈济会透过街头卖花、卖物会、义唱、义演、节食活动等方式,共募集两万余港元。1938年10月,香港同胞将庆祝「双十节」的宴会款项改作捐募寒衣,76个商团联合募集寒衣36万件;1941年8月,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发起「一碗饭运动」。
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成立。1942年,百余名香港青年突破英军防线,加入东江纵队,组建了香港本土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他们在港九新界建立了20多个情报站,营救了800多名滞港文化名人(包括茅盾、邹韬奋、胡风等),并突袭日军启德机场,炸毁6架战机。队伍成员来自不同阶层——英资洋行打字员、香港大学学生、九龙城寨码头工人......他们以「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华民族抗日战士」为共同身份,殖民统治下的身份碎片化在民族危亡之际被整合为国家主体性——战争成为重构政治与身份认同的熔炉。
「澳门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简称「澳门四界救灾会」)是抗战时期澳门最重要的爱国团体之一。1937年8月成立后,该会除筹款赈灾外,更把后期核心工作转向组织青年回国服务团,深入广东抗日前线开展战地服务。先后有11批青年以血肉之躯,践行了「共拯我被难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宗旨。不仅填补了广东前线后勤与团员缺口,更以14人的牺牲诠释了澳门同胞与祖国同生共死的民族气节。这段历史也凸显了澳门在抗日战争中的特殊地位:不是「中立孤岛」,而是爱国热血汇流之地。
港澳同胞的抗战行动撕破了殖民国家当局「中立」「非政治化」的伪装,展现了华人社会自发的民族与文明共同体意识。正如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体》中指出的,当人们通过共同的苦难、共同的抗争、共同的记忆形成「想象的联结」,国家认同便超越了地理边界与政治制度区隔。
在殖民国家侵占秩序的裂缝处,港澳形成了「地方」与「中央」的隐性联动。表面上,葡萄牙政府在二战中宣布「中立」,然而澳门实则成为华南地区的抗战补给站。1943年,澳门商人何贤透过大丰银号将澳门博彩收益的40%(约500万澳门元)兑换成黄金,经澳门内港运往重庆;1944年,中共地下党在澳门镜湖医院设立秘密交通站,利用澳门的葡萄牙邮电系统向延安发送了1,200多份日军华南部署情报。这些行动之所以能够实现,正是因为殖民国家当局在商业利益与政治投机之间选择了实用主义:既不敢得罪日军(1940年日军曾在澳门边界陈兵三万施压),也不愿切断与中国内地的经济联系。这种「骑墙姿态」客观上为华人社会的抗日活动留下缝隙,使港澳成为殖民主权与国家主权博弈的「灰色地带」,而华人社会则在这种博弈中主动建构了与内地的隐性政治联动。
「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现实根基
(一)殖民治理与「去国家化」的破产。二战结束后,港澳并未迎来去殖民化的曙光。英国以「保卫香港」为由拒绝归还新界,葡萄牙则将澳门视为「海外省」。冷战格局下,两地殖民国家当局转而推行「去政治化的政治」:香港以「东方之珠」经济神话和消费主义淡化政治认同;澳门则以「博彩旅游」的产业定位和文化、产业多元化来包装殖民本质。此种治理策略导致部分港澳居民形成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虚无主义的混合心态——一些人甚至在2019年「修例风波」中,将殖民时代的港英政府奉为理想的治理模式典范,暴露出殖民化所遗留下的深层认同异化。
然而抗战记忆正成为破解这一异化的关键钥匙。2021年,香港特区政府将「国家安全教育日」纳入中小学课程;港澳特区政府和民间团体也多次以研讨会、艺术表演、观影展览等形式普及抗战历史、开展相关学习活动,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及对东江纵队、澳门难民潮赈济史实等的宣传,解构殖民叙事。当港澳居民认识到在民族危亡之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保护了他们的祖辈,是全国各族人民群众与海外华人同舟共济,担负保卫家园的历史使命时,「去国家化」的神话便不攻自破。
(二)爱国者治港治澳的三重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这是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推动港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有力保障。这一原则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必然性与理论正当性。
首先在主权层面,港澳先后完成由殖民国家当局侵占地区向中国主权下的特别行政区的历史性转变。被侵占时期的惨痛教训印证了主权、管治权对民生福祉的决定性意义。1941年香港沦陷后,日军以1:4的比率强制兑换军票(黑市实际贬值至1:10),令70%以上的华人陷入赤贫;1943年澳门因日军封锁而饥荒蔓延,米价暴涨167倍,约4万居民(占当时澳门人口的10%)死亡。这些灾难的根源在于殖民政权无力维护属地安全与发展权益,唯有回归国家主权框架,依托「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港澳居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才能获得坚实保障。「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通过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统一,彻底终结外部势力干预的可能性,确保港澳治理始终服务于国家与民族整体利益。
从共同体角度看,港澳实现了从表层地域认同到深层文明自觉的转变。抗战时期港澳华人的行动表明,中华文明共同体意识具有强大凝聚力,其根基不仅在于共同的语言、文化、历史经验,更在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伦理。香港国安法规定「行政长官、主要官员、立法会议员、司法官员必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这并非对「两制」的限制,而是通过法律将管治者责任锚定于「一国」根基,并确认「港澳的命运始终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的现实逻辑,这既是中华文明「以文化心、以天下为己任」治理传统的当代延续,也是对历史规律的现实确认。
从治理逻辑看,港澳实现了从被侵占霸凌向爱国者协商治理的转型。殖民统治的本质是排他性霸权,而「一国两制」的核心是包容性治理。被殖民国家侵占时期的所谓「协商」实为一种生存策略。抗战时期,港澳华人社会透过「抗日联合会」「救灾会」等民间组织实现跨阶层、跨行业协商合作,为今日制度设计提供了历史借鉴。今天的「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将这种协商传统提升到制度层面:改革后的香港立法会90个议席由直选(20席)、功能界别(30席)、选举委员会(40席)三方面构成;澳门立法会则包括直选(14席)、间选(12席)、委任(7席)。这些设计冲破了殖民时期的种族壁垒,确保分处不同界别、持不同意见的人士能在「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前提下参与治理。由此,港澳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通过制度化差异协商实现了多元一体的包容性治理,彰显了中国政治文明的独特智慧。
在「国家」与「地方」的辩证中走向未来
回顾港澳抗战史不难发现,一条清晰的政治命题贯穿始终:当「地方」遭遇外来压迫,「国家」便是最坚实的后盾;当「国家」面临生存危机,「地方」亦是不可分割的血肉,这种国家与地方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一国两制」的当代实践中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
对香港而言,「爱国者治港」并非对「两制」的收缩,而是对「一国」的强化。唯有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香港才能继续保持「超级联系人」地位,才能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展现「国家所需、香港所长」。
对澳门而言,从博彩单一经济走向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的转型,本质上是从殖民遗留的依赖模式迈向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抗战时期,澳门华人通过支援祖国完成身份觉醒;今天的澳门则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葡平台建设,成为国家对外交往合作的重要窗口。更深刻的启示在于,港澳的变迁颠覆了西方政治学中国家与社会对立、主权与自治矛盾的理论范式。在这里,「一国」不是抽象的法律概念,而是承载著五千年文明记忆的共同体;「两制」亦非制度对抗的产物,而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智慧的当代实践。
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重思港澳政治哲学,实际上是在回答一个更宏大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应该如何构建既有民族根脉、又具世界视野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从「殖民国家侵占地」到「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改变的是治理主体与制度形态,不变的是国家至上、民族为先的核心价值,是血浓于水、休戚与共的共同体精神。
爱国从来不是地理归属,而是一种文明自觉;治理港澳也从来不是权力游戏,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必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港澳需要把抗战记忆转化为建设国家的澎湃动力,「让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不仅成为制度原则,更成为全体居民的文化自觉。唯有如此,这两颗曾被割裂的东方之珠,才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5年7-9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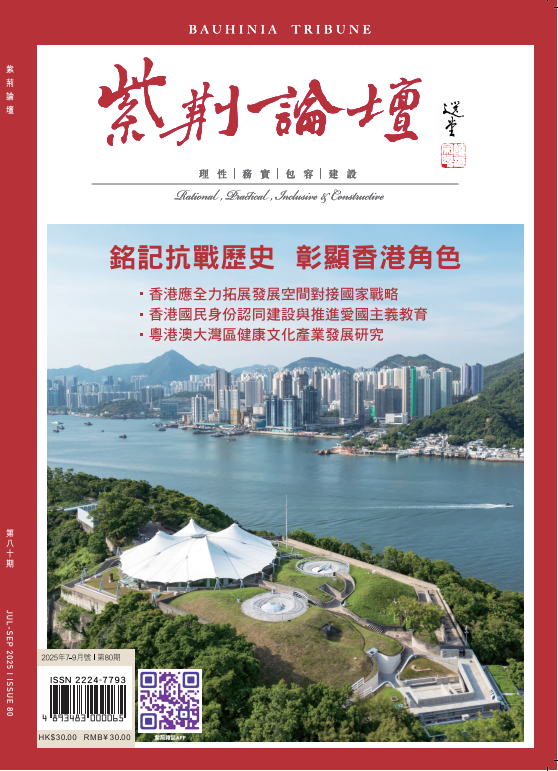







 今日热搜
今日热搜

 本周热搜
本周热搜

 本月热搜
本月热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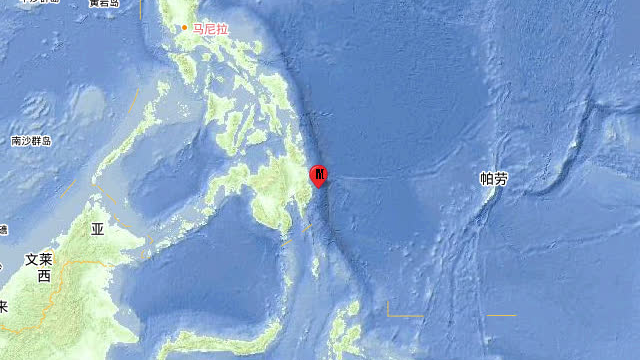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