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舟娜
一到夏天,就会在冰箱里存几盒雪条,炎热时,来上一根,凉意瞬间润过全身,暑气就消了一大半。买的时候,爱挑老式的,老式雪条里,最喜欢的是赤豆。每次吃都能让我想起小时候。
赤豆用的是红豆,缀在雪条顶部四分之一的位置,剩余部分则是红豆色的冰,所以又叫“赤头”。煮熟的红豆是粉粉的口感,和冰一起咬到嘴里,甜糯清爽,唯一的遗憾是数量太少。后来又出了一款,叫“全赤”,红豆里里外外长满整根雪条,可以一饱口福,当然价格要贵一倍,在小时候属于奢侈品,舍不得买,大部分时间还是买“赤头”。
买“赤头”也用不著去店里。一到夏天,就有男人骑著单车走街串巷,单车后座上绑著一个方方正正的木头箱子,箱子里塞一团破旧的棉絮,雪条就藏在里面。他一路骑一路喊,“卖雪条咯!”“卖赤头咯!”话音未落,被太阳烤得前后都不见人的弄堂里,像有预谋似的一下子涌出来几个小孩,每人手里攥著几毫子,等不及他支好自行车,小手们便迫不及待地扒拉木箱的盖子。男人佯装生气,一一拍走他们,小心打开箱子,但并不揭开棉絮,只把一只手伸进去掏,为了防止“出气”,连眼睛也不看。于是问题就来了,有人要“赤头”,他给拿成“盐水”,有人要“盐水”,他给拿成“冰砖”。他嘿嘿一笑,放进去再掏,出来还是错的,他也像故意似的,非得来回倒腾几次才肯甘休,把孩子们逗得乐不可支。
吃雪条时要一口一口舔舐水分,绝不能让一滴掉到地上,对小时候的我们来说每一滴都比珍珠更金贵。等到融化的水没了不得不下口咬的时候,速度也要尽量地慢,否则最后只能眼巴巴地看著小伙伴独享了。吃完之后的棍儿也不能丢,攒在一起送到小卖部去,可以换钱,大几十根才可以换来一两毫,所以没有谁乐意去换,倒是乐于捡。那时的棍儿上也不刻甚么字,只在形状和大小上略有区别。一个暑假过去,每个孩子手里都可以攒下一把棍儿,吃下的少,捡来的多,都经过仔细的刷洗,白灰色,脆生生,香甜甜。这些棍儿虽说形状不同,但只有一种比较特别,已经超过了雪条的范畴,是雪糕的刮匙。拉长的葫芦形,很少有人舍得买,所以这样的棍儿非常罕见,拥有一个基本上就可以睥睨全村。我有一次回老家,还在书房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根,因为潮气,已经腐坏,但凑近闻还残留著香甜的气味,只是那时候有一个怎么样的故事早已忘记了。
现在有一种文创雪条,做成各种好看的景点形状,长相精致,但奶多水少,咬下去是软的,化得也快,大部分都是被太阳舔去的。不像“赤头”,水分多,能吃的时间更长,可以用来回忆的时间自然也更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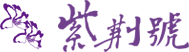





 今日热搜
今日热搜

 本周热搜
本周热搜

 本月热搜
本月热搜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