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26日,《学习俱乐部》首发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先生关于《十五五:三“重”命题的趋势、短板与建议》(发言录音及PPT),引起读者关注并留言:“希望看到录音文字稿”。现由常教授本人根据录音及PPT整理加工成此文,相对于会上因受时间限制的简短发言而言,本文字稿更完整也更有学术价值,现刊发,以飨读者。
我发言的题目是《十五五:三“重”命题的趋势、短板与建议》。三“重”命题,十五个字——“创新重数智、发展重人本、改革重要素”。围绕每个命题,各作三层分析:趋势、短板及建议,与大家交流、探讨。
一、创新重数智
我用“数智”二字:意指数字技术革命是基础,人工智能是其新的发展阶段,或曰“提升”。
(一)趋势(应然分析)
这里说的创新主要指“科技创新”,总的趋势是什么?我在主笔出版的《创新立国战略》(列入国家发展战略丛书,2013,学习出版社等联合出版)一书指出,从战略层面看,国家应走“创新立国战略”之路,以切实推动我国从“加工大国”向“创新大国”跨越。从科技创新本身而言,数字革命与人工智能(AI)是核心趋势。
去年(2024)我曾四次到杭州考察、学习,当地的“六小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它们不仅在技术上开源、免费、低成本(这有利于推进“平权化”、摆脱贵族化),更在生产关系上呈现鲜明特点:第一,全都是民营企业(不是国有企业);第二,全都由年轻人领军。这让我思考,在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后,“人才红利”特别是年轻人的“人才红利”已开始萌生,我国或许正进入“人才红利”发展的新阶段。
今年初,浙江开“两会”,他们访谈,我在1月13日《浙江日报》提出“创新三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建议浙江全省推广DeepSeek(“深度求索”)模式;半个月后,1月29日(中国春节期间),DeepSeek在海外爆火,引起关注。
当然,我知道,DeepSeek还不是原始创新,而属于一种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AI就本身来说,现在也尚处于“一般”人工智能阶段,下一步应向通用人工智能(AGI)及更高阶段的超级人工智能(ASI)发展。这也引发我的思考:下一步我们人类将面临怎样的变革,未来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二)短板(实然分析)
我国在高科技领域面临严重的“卡脖子”问题。中美之间,从五月瑞士日内瓦会谈——到六月英国伦敦会谈——再到七月瑞典斯德哥尔摩会谈,双方博弈显示,在高科技领域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存在相互“卡脖子”问题。虽然我们手中也有“杀手锏”——“稀土”(包括占全球61%的稀土资源和占全球90%以上的稀土精炼产能、技术与产品),但在高科技(例如芯片等)关键领域,我们确实也有“短板”。
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这是“十五五”我国必须突破的“瓶颈”。
(三)具体建议(四条):
一是强化创新精神。我认为,“自立自强”不仅是科技领域“单向度”的自立自强,而应是整个国家“民族性”的“自立自强”,此乃“国之魂”。欲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培育和铸就整个民族的自立自强精神。
在这一点上,要学浙江“古越人”那种“卧薪尝胆”的精神(《勾践栖会稽》载:夜间每过一更天,卫士就喊一句:“勾践,你忘了会稽之耻了吗?”“没有忘记”)。当代中国,亟需这种全国上下“自强不息”的精神。
二是营造创新环境。围绕创新者“心灵放飞”,首先要构建类似“大森林”般的大环境,同时也要培育“小树荫”式的小环境,即使一时难以形成“大森林”,也必须给创新者提供一个“遮阴蔽日”的“小树荫”,好让他们“心灵放飞”。如果大家“心灵不放飞”,你就是空谈创新。
三是完善创新机制。既要有宏观调节机制,也要有微观的“产权”机制。这里的关键是科创人员“职务发明”成果的产权分割机制。笔者在拙著《广义产权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曾提出:“还应将这部分‘知识’产权的一部分,分配给具体创造该‘知识’产权的技术人员。”即:“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该单位所有,另一部分由技术人员持有”(见该书,第207页)。
但,这些年,现实中教训惨痛,一些创新者因产权分割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被抓),这种“悲剧”无论如何不能再重演(已发生的,也要甄别、纠偏)。必须落实科创人员的“产权”,而且不应使用“恩赐式”的“赋予”提法,建议用“尊重和承认”或类似提法为好。当然,现在我们可不去计较“提法”问题,“赋予”终究比不“赋予”好。
四是推动国家层面编制并公布“中国创新指数”。目前“全球创新指数”由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与美国康奈尔等大学联合编制(中国的排名大体可以)。国内呢,我们现在也有研究部门(如科技部科技战略研究院)编制。我建议,十五五进一步提升层次,即提到国家层面,编制并公布中国的“国家创新指数”。
(四)由科技创新引发的个人进一步思考:
今天有很多老朋友在座(也有些新朋友),我们坦诚讨论一个涉及现代化问题:
日本明治维新前,教育家福泽谕吉讲过一段话:“一个民族要崛起,须改变三方面:人心(思想)、制度、器物”。这三者现代化,理论上是否有逻辑呢?实践上是否有顺序呢?我认为,理论上应该是有逻辑的,实践操作起来也应是有顺序的。
当前,我们国家层面高度重视“发展新质生产力”,很好。我认为,新质生产力本身也包括了思想和制度的元素,但是,人工智能AI这等技术本身可能还属于器物的现代化,应属于第三个现代化吧?面对今天这个格局,我们能不能从实际出发,可否提高一层,抓住“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切入点,作为一个突破口,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推进。
具体建议:当前应深入研究人工智能AI对制度(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影响或者“倒逼”问题。《浙江日报》5月26日“思想周刊”刊登了我的论文《十五五时期经济发展与改革思路初探》,提出了“三层倒逼论”,即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突破口、为切入点,实行“三层倒逼”:第一层倒逼“生产方式”(介乎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如经济结构问题),第二层倒逼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经济体制问题),第三层倒逼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我这里只说是“某些环节”问题,并非上层建筑之全部)。
二、发展重人本
(一)人类发展大趋势
当年,在南开大学经济系读政治经济学进修班时,老师教“社会主义经济经典著作选读”,第一本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2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书中讲的一句话记忆深刻:“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学后感到,这是《共产党宣言》中最闪光的思想。
现在简化成“人的发展”,其实,马克思原话是“每个人”和“自由发展”。我理解,“人”是抽象的,“每个人”具体的;发展是可贵的,自由发展是价更高的(“发展诚可贵,自由发展价更高”)。因此,这两个前缀词是不可删节的。2018年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出了最新版,我看了2018年新版,依然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我认为应尊重《共产党宣言》的这个原意。因为,马恩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理念不仅揭示了“发展的本质”,更揭示了“新社会的本质”。
当代国际上有良知的经济学家也秉持这一发展理念。例如,本人在《人本体制论》一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中,曾引述了法国经济学家佩鲁(Perroux)的“人本主义发展观”。他在其代表作《新发展观:基本原则》(1983)中指出:“真正的发展,必须是经济、社会、人、自然之间的全面协调共进”,核心是“人”。
阿马蒂亚·森(Sen.Amartya)凭什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是他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书中强调发展的本质在于“扩展人的可行能力”。
我认为,这些是“人类的共同文明”。最近(2025年7月10日至11日),北京不是正在召开“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吗”?(中宣部和中联部主办)。既然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我们得把“人类的共同文明”旗帜高高举起来才对。
正是在共同理念的基础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1990年5月首次公布人类发展指数(HDI),将单一GDP指标转变为“综合性评价指标”,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本人曾研究过这个“指数”,认为它反映了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发展的大趋势。
(二)短板分析
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情况如何?首先应该承认,2012年(十八大)以来的十几年,是有进步的。有数据为证:2012年排在世界第101位,2017年上升至第86位,到今年(2025公布)升至第78 位。但是,我国的GDP在全世界排第二位的。很明显,人类发展指数第78 位与GDP全球第二的排名,存在着较大的落差。
而更应引人忧虑的是,在浮躁的社会氛围中,有些媒体盲目地渲染“厉害了我的国”云云,以至于,全社会讲GDP“全球老二”者,众;讲HDI“全球第78位”者,寡。
对此,我自己很忧虑:对第二位与78位之间这个落差,怎么办啊?“人类发展指数”是要落到“每个人”的“人头”上的,同志们。按照党中央一再强调的“实事求是”精神,这种社会浮躁心理必须改变,我们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和改革空间。
(三)建议:
由此,我建议将人类发展指数纳入“十五五”相关指标。该指数包含三大核心内容,第一个是人的生命健康,特别是长寿,这个指标非常好;第二个是知识的获取,包括教育年限和教育水平。这个对我们来说太关键了;第三是生活水平,包含人均GDP等,它能更全面反映人的生活质量。因此,“十五五”我们是不是抓住“人类发展指数”来落实“发展重人本”?
与此相联,我顺便提一下与民生直接关的“居民消费”问题。现在,研究中国的消费,涉及“消费六率”。包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消费增长率”、“消费贡献率”、“最终消费率(含政府消费)”、“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倾向”。“消费六个率”各有各的内涵,也各有各的用处,都不应否定。
现在,电视报纸等媒体宣传、更加广为人知的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这一指标确实反映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现实增长情况(大家也都比较习惯),但是根据自己的研究,这一指标存在两个重要缺陷:
其一,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指标内涵,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包括商品性消费+“餐饮类服务性消费”,它除了不包括“非实物商品”的网上零售额外,更重要的是,它不包括除餐饮服务外的其他大量的“服务性消费”(如住宿居住、交通通讯、教育培训、医疗健康、旅游体验、文化娱乐,以及其他用品服务等多领域的服务消费支出)。
而根据最新数据,中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已经占到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46.1%(即央视说的“老百姓每花10块钱,4.6元‘买服务’而不是‘买实物”)。可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虽然包括部分交叉性的“餐饮消费”,但不包括绝大部分的服务性消费。而居民“服务性消费”,正是我国在当前和下一步要大力激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经不能适应居民“服务性消费”增长的新格局。
其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既“短缺一大块”,又“多出一大块”,即:相对于居民而言,多出了“机关、社会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等”)的消费支出。根据相关数据及分析,从支出法核算GDP角度研究,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和政府等消费这两部分构成,两者相加中国现在为54%,其中:“政府消费率”长期在15%左右(即政府消费在最终消费中占到30%),“政府消费率”( 15%)是不应该算在居民消费头上的。现行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多出了政府消费这块,是应该“剔出”的(其他不再分析,略)。
比较起来,从战略上说,我建议国家应更加重视和侧重抓“居民消费率”。
“居民消费率”是“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与“支出法GDP”之比,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率具体数据如下:2022年居民消费率为37.2%(低于38个可比国家53.8%的平均水平);2023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公式之分子)493,247.2亿元,GDP(公式之分母)为1,262,642.5亿元,居民消费率为39.2%。这39.2%处于什么水平?这里不便引用国际比较相关的数据,简言之,国际比较,很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
我认为,居民消费率是研究消费的“十环”之所在(当然个中比较复杂,难度也大),应作为国家监测和考核指标。第一,有利于真正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促进“每个人”的发展;第二,也有利于提高中国全民族凝聚力,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第三,更有利于提高我在国际社会中的排名位次,强化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主动权。
至于老百姓关注的“支出法GDP,都支出到哪里去了”?这是另一个更宏观的命题,很值得研究,以回答老百姓的“时代之问”(拟另文论述,本文不再展开)。
三、改革重要素
(一)趋势
十五五期间,中国改革将出现什么新趋势?就经济领域而言应该抓什么?我认为,应该抓“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这是改革的新趋势。
2024年12月,由本人主笔、蔡继明教授副主笔,并带几位年轻朋友耗费四年心血完成的新著《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大纲》(54万字),已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并被中宣部列为“2024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基于新趋势的需要,我们重点聚焦于七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功能与收入分配功能”,这是十五五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短板
中国改革已过46年,前一阶段的“商品市场化改革”之战,打得很艰苦,也取得不小成效,2021年,中国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市场化程度已达到97.5%。但是,相比之下,七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长期滞后,成为中国改革的短板。
例如,土地、技术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数据要素的产权问题,有的已破题,有的尚未完全破题,如“人脸识别”数据的产权界定和产权交易等;至于“管理要素”(企业家要素),虽然中央已经列入“七要素”之中,但是我们的文件、报告、讲话等,对此仍然采取回避态度,以至于至今“管理要素”(企业家市场)处于“缺位”状态,这是“不可或缺”的。基于此,我在书中专门写了第十章:强调“不可或缺的”管理要素(企业家市场)。总之,这些“短板”必须补上。
(三)建议
为提高中国的全要素市场化指数,建议十五五期间,可从“市场配置功能与收入分配功能”相统一的更高层次,“双线”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双线”之一:发挥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市场配置功能。去年我在全国县域经济发展大会上提出“要素三放论”,即:“人本要素要放手”;“物本要素要放活”;“数据要素要放量”,十五五期间应秉持“要素三放论”。
双线”之二:发挥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收入分配功能。党中央在国内学者多年研究(包括南开学者谷书堂教授和蔡继明博士1988年首次提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基础上,借鉴当代人类共同文明的成果,确立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思想:
从中共十六大(2002)提出这一“原则“,到中共十七大(2007)提出这一“制度”,再从中共十八大(2012)提出:“完善”这一“初次分配机制”,再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2013):提出“健全”这一“报酬机制”;再到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2015):提出“优化”这一“机制”……
特别是,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2019):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包括“七要素”在内的“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直到去年(2024年)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一字不易地赓续十九届四中全会上述关于“……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正是在学界此前多年探讨基础上,深入学习和领悟中央自十六大以来一系列文件的一贯思想,本人经进一步思考研究,于今年(2025年)1月9日在《中国经济导报》访谈中,提出要素分配功能的“唯一标准论”——即“要素贡献是决定要素报酬的唯一标准”“市场是评价贡献的基本尺度”。1月10日《中国改革报》转载(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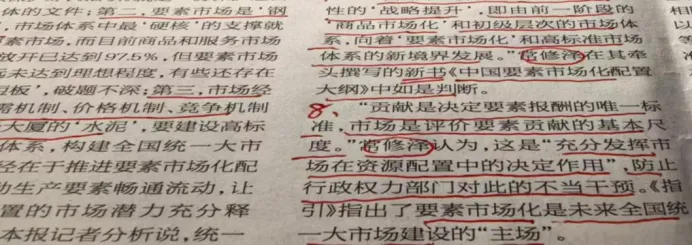
这里,我尝试提出“唯一标准论”,“唯一”就不是“唯二”。我希望:不要离开中央上述《决定》提出的这个“标准”,再去另立“别的”标准。
以上观点,愿与学界朋友共同切磋。







 今日热搜
今日热搜

 本周热搜
本周热搜

 本月热搜
本月热搜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