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曦
近日朋友圈的“荷花”开得如火如荼,我刷著精修过的九宫格图片,忆起老家的莲田。莲叶田田,荷花朵朵,风一吹,香味便盈满鼻腔。“旋折荷花剥莲子,露为风味月为香”,那是诗人的风雅。种莲人的记忆里,只有果肉的饱满与莲心的微苦,顾不上“花之夭夭,灼灼其华”。
读小学时,老家很多人种莲。种莲性价比高,莲田还可种一季水稻。母亲说,我们也种点莲子变几个钱吧。父亲便腾出弯丘那一亩多田种莲子。家里有五个人吃饭,要上缴八百多斤稻谷的农业税,莲子价格再高,也不敢全部种莲子。
种莲子貌似比种稻谷清闲,实际上很繁琐,一粒白莲要经过采摘、褪蓬、剥皮、去芯、晒乾等程式。
我们还在睡梦中,父亲就拿著蛇皮袋、打著手电筒出去采莲蓬。父亲扛著大袋莲蓬回家,已是早餐时,他的头发湿答答的,被汗水泥水打湿的衣服贴在身上,裤子上沾满泥浆。他去洗澡,换了汗衫、短裤出来吃饭,手臂与小腿好几处血痕,那是被莲茎上的刺划拉伤的。
莲蓬摘回家,要手工一粒粒剥。不过采莲的季节正好不用上学,我和弟弟可以剥莲子度过漫长的暑假。
弟弟坐在小板凳上,把莲子从莲蓬褪出来,太嫩的,他剥了粗壳直接往嘴里塞。我捏著一粒莲子,竖著塞在上下门牙间,用牙齿固定莲子位置,拇指、食指捏住,稍用力往外拉,“啵”的一声,莲子的绿罩衫就被一扯两开,露出月白色的中衣。我用大拇指指甲,沿著顶端灰色晕划一圈,再往中撕开剥离,白白嫩嫩的莲肉搁在塑胶脸盆里。
剥好了的莲子用一根竹签,从莲肉底部的尖尖肚脐处穿过去,绿色的莲心从头部冲出来,落在瓷碗里。我把一枚枚莲芯并排放在掌心,幻想是孙悟空的毫毛,吹一口仙气,就能变出无数个猴头。自家的莲子剥完,我也会帮别人家剥莲子。一毛钱一斤的手工钱,一天好几斤,一个暑假能攒不少钱——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呢!
母亲把处理好的莲子洗乾净,倒进簸箕,拿到外面暴晒两日。母亲双手托著簸箕抖动,莲子相互撞击,发出清脆的空响。若天气不好,没有太阳,就要发一炉煤火,烘乾莲子,否则莲子变色,发黄发黑,便卖不出好价钱。太阳暴晒的莲子成色好看,乾白亮黄,而煤火烘乾则色泽偏黄偏暗。人工剥的莲子晒乾以后总有牙齿印,商家会以这作为检测标准,确定价钱。机械剥莲子,经过咸水泡,果肉虽白,味道却差了许多。
有一幅摄影作品,是遗落在茎上老莲子。这种老莲子晒乾叫铁莲子,剥开皮叫红莲,红莲泡发祛皮可做莲子羹。如今的我已经咬不动铁莲子,却经常炖银耳莲子羹。软软烂烂好入喉,温温润润养心肺——犹如儿时记忆。







 今日热搜
今日热搜

 本周热搜
本周热搜

 本月热搜
本月热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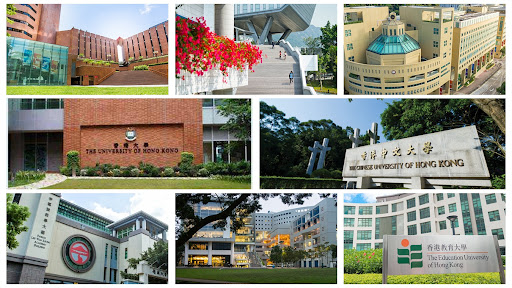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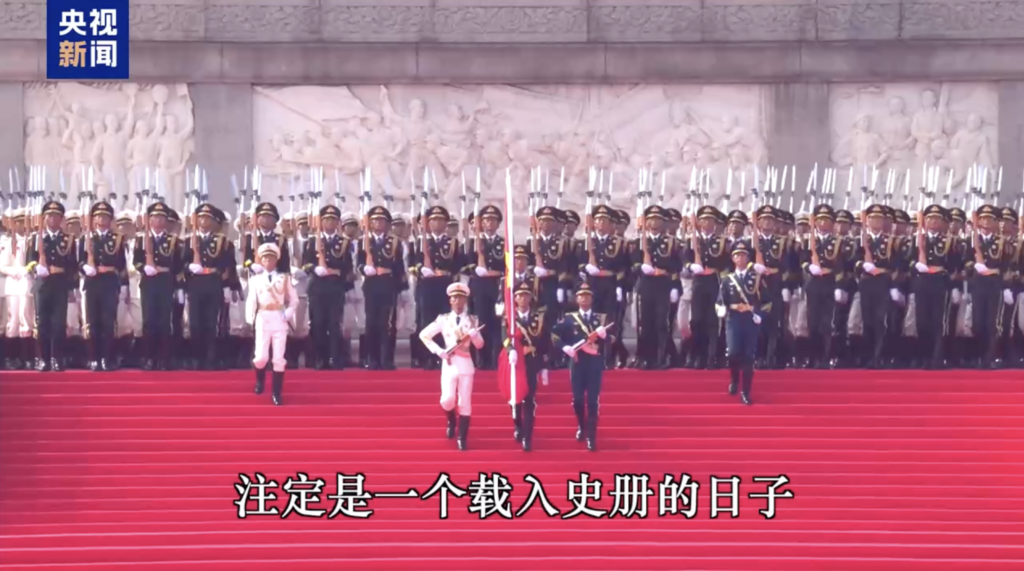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