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指尖
傍晚西天云层缤纷,仿佛油彩不小心被打翻,斑斓色彩毫无秩序地涌成团状或条状。这样情形下,总生出想靠近仔细端详一番的冲动。怀著如此心境在路上,急切又欣然,眼见得天越来暗,恨不能跑将起来。轻浮莽撞,仿似回到年轻时。
但年轻时代的记忆并未存储过类似画面,更多的是雨和雪,寒冷又热闹。也是,繁弦急管的日月,哪有时间去抬头观云识雾呢。再往前,竟撞上童年。自己站在泉子沟陡坡上,痴望著天边浩大的云彩,我看见羊群和马群,河流和远山,草丛和树木,还有马群奔跑时蹄下腾起的黄尘。有一天,我竟看见一张眉眼清晰、表情丰富的脸,一会微笑,一会愤怒,一会眉眼拉下,竟然一副哭相。凉风吹来,灌进衣服里,我鼓囊囊地站在那里,母亲的声音从深处传来。更多时候,担水的母亲会跟我一起观望西天变幻无穷的云层,好像有某种极其神圣的东西在控制著我们,我们从不说话,就那样静静地,让风吹拂著额发,让彤云印红我们的脸。我曾坚信,母亲水桶里的彤云会被她藏到水缸里,这是我愿意回家的理由。
有时,在小河口等大人们从对岸的地里散工回家。一群小孩叽叽喳喳,觉得是河水把天空染成七彩色的。我们在河水里洗脸,洗手,将脚伸到河里,缓慢而神圣地抽出来。没有变化,我们还是以往的愚蠢模样——被夏日晒得黝黑发红的脚面和小腿,胳膊、脖子和脸。有人又说,温河是从天上流下来的。这个结论我们基本赞同。只是,为甚么天上有那么多颜色,河水却没有任何颜色呢?极目远望,流水与长天相接处,到底有怎么的秘密?我们发誓,长大后,一定要沿著温河,像鱼一样,逆流而上,像鸟一样,逆风飞翔。
后来呢?我看见一个在时光影像中快进的自己,无数张表情快速变换——树杆上刻字的自己,雪地里跋涉的自己,被冷雨浇灌的自己,被嘲笑的自己……好不容易按下暂停键,一个茫然四顾、神情疲惫的自己定格。已经不年轻了。惊觉无数日子被虚度,被忽略,忘记抬头,也忘记低头。像一粒尘土,被命运的大风吹著,滚动著。终将停驻在生命的黄昏,却永难抵达那些拥挤的、厚重的,诡谲云层。它们在前方,上方,远方。
我当然没有永远朝著天空走下去的胆量。随著天色昏暗,云层呈现出更加纯粹、深厚的重墨浓彩,在壮阔的美和忧伤面前,我们哑口无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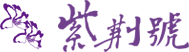





 今日热搜
今日热搜

 本周热搜
本周热搜

 本月热搜
本月热搜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