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荆论坛》专稿/转载请标明出处
陈学然 |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及副系主任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时刻,我们不能忘却当年香港上百万市民经历的战火苦难。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是香港史上称作「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军占领岁月。在此期间,日占政府施行高压统治,人人自危;加上物资短缺,粮食不足,民众被逼离港归乡,无业者则被押送至无人岛活生生饿死。留下的民众无不挣扎求存,说是人间炼狱,实不为过。然而,在这最为黑暗的时刻,香港不乏民众参与抗日救国行动,留下不少抗战史迹与救国故事。回顾历史,不只是要新一代认识香港曾经有过这样一段黑暗、痛苦的岁月,同时也是要缅怀先烈的壮举;铭记历史,不是要记住仇恨,而是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日子,并且时刻保持居安思危的警觉性。
黑夜来临前:港人反日救国运动受港英政府打压
英国于上世纪初与日本签订「英日同盟」条约,规定两国在远东的合作关系,包括双方在所属辖境内互保双方利权。该条约虽于1923年失效,但二者既合作又猜忌的关系一直延续。日本日益强盛的国力,使英国为之忍让,避免自身在华利益受损。故此,香港居民的反日救国运动,长期受到港英政府打压。五四运动、济南惨案、「九一八」悼念殉国同胞活动,香港市民奋勇上街抗议日军恶行的义举都受到港英政府打压。直至香港沦陷前,香港报刊但凡出现抗日、批评日寇的标题或文章,都受制于港英政府新闻审查条例,或不准刊载或大幅度地以「打天窗」形式见报。
1930年代中后期,港英政府当局两手准备,一方面压制反日言论,一方面因应日军的广东军事行动而加强防务,建立起号称东方马奇诺防线的「醉酒湾防线」,也在要塞位置加建机枪堡、炮台等工事。但是,这一切相比日军的强大兵力,薄弱得不堪一击。香港防务的缺陷问题,与英国把亚洲军力回调至欧洲主战场有莫大关系。即使英国当局意识到日军可能犯境,最后也只能让万余「杂牌军」防守香港;当中包括千余名华籍英兵外,逾百万华人虽然热心于支援抗战救国,但对于香港存在怎样的日军威胁毫不知情。英国无意派驻正规军增援,在于不欲把有限资源浪费在香港这个不可能守住的地方。故当日军一旦进犯,英国军民可以做的只是争取尽快撤离香港。那么,死守香港岛以待救援或撤离,成为了港英政府的基本战略考虑。香港人口中占比95%以上的中国人,长期来得不到港英政府信任,一直被排除于政府体制外,以致港英政府防务是否得当,备战是否充分,他们都没有置喙之余地。香港社会上下不能团结、难以齐心,快速沦陷不是什么意外之事。

国家有难,香港绝大部分居民表现出热烈的救国热情,投入抗日救国的筹款、认资活动。香港各大商会与东华三院自「七七事变」以来,便为受影响军民筹款救济。由华人领袖周寿臣担任要职的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香港分会,筹得逾五百万港元善款。就连贫苦低下阶层市民也节衣缩食,合力义卖;1938年8月,小贩发动的筹款更高达百万港元。其他华人领袖眷属如罗文锦夫人、李树培夫人成立香港中国妇女会,组织香港妇女参与救国慈善工作。影艺界、教育界、南来文人团体,纷纷组织筹款赈济活动,以人道救援之名行抗日救国之实。宋庆龄与政商要人则借助香港创办了保卫中国同盟,发起「一碗饭运动」,大力呼吁海外华侨抗日救国。八路军更在香港成立了办事处,由廖承志担任主任,为中国抗战作出巨大贡献。
然而,港英政府在日军威胁日深之际,也加强了中文报刊审查工作,限制华人公开发表抗日言论。英国对日妥协让步,一厢情愿地把处于中日战争边缘的香港定位为「中立」角色,求取香港免受军事进犯。为稳定民心,港英政府公开宣称香港是安全的,强调英军有能力保护香港。港英政府的表态,让香港某些人对于英军的防守能力与抵抗决心过于乐观。但这些反过来使香港社会整体的备战意识不强,一些南来香港的富贵「难民」更是醉生梦死,寄情于声色犬马,使沦陷前夕的香港呈现一片纸醉金迷的假象。1941年11月,香港各大报纸最瞩目的是「刘美美」案。该案涉及英国将领在一宗防空工程上的贿赂事件,中间人刘美美与该将领有染,其豪奢生活与桃色关系成为案件最大新闻,被市民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只是,人们对于逾六万日军陈兵港深边境的事实,却是置若罔闻。
1941年12 月,香港弥漫著庆祝圣诞节的欢庆气息。12月6日,就在陷入日军占领的最后一个周末,跑马地照常赛马,甲组足球联赛如期热烈举办。12月7日星期天,市民奔往皇后戏院观赏《英宫十六年》,外藉人士如常在私人会所参加各种球类活动与海上活动。唐海《香港沦陷记》的第一章《宁静的星期日》指,香港没有人会想到战争即将于第二天清晨来到,而他们都沉醉于最后的一个休假日。在这个假日里,人们的安闲──「表现在电影院满座,酒吧间堆满了客人,舞场里不停的发散著爵士音乐上,四周找不出一丝的战争气息;只是近二三天来香港政府在举行开玩笑般的防空演习而已」。1941年12月8日早上七时,48架日本军战机空袭香港启德机场,五分钟内炸毁香港仅有的五架军机和八架民航机,其他军事据点与交通设施,无一幸免。六万日本陆军兵分两路从上水及锦田向市区推进,醉酒湾防线于12月10日因兵力薄弱而被日军攻破,日军打开了通向九龙市区的大门。
对于大多数香港居民而言,生活世界的彻底改变,比预期的来得更为突然、更为痛苦。
日军登陆:人间炼狱,惶恐终日
1941年12月18日晚,日军于北角一带登陆香港岛,与英军相继在黄泥涌峡、浅水湾激战。12月22日,跑马地为日军所占,爆发了屠杀平民的「蓝塘道惨案」。死者包括了最早响应「五四新文学运动」在香港发展的「策群义学」成员屈柏雨,他是香港著名教育家梁省德的丈夫。他当天正在华人领袖邓肇坚的蓝塘道大屋作客,屋内共计48名男性被杀害,包括邓肇坚妻子在内的女性惨遭凌辱。根据日军攻占香港指挥官酒井隆的判决书所述:「(1941年12月22日)同月二十二日下午六时,在蓝塘道二号,屠杀居民四十八人,并奸杀孕妇,轮奸年甫十二三岁之幼女,洗劫财物而去。」在日军攻占香港期间奸淫虏掠,地痞流氓也趁乱肆虐百姓,烧杀抢掠,洗劫平民,社会完全失序失控。
12月25日傍晚,港督杨慕琦和驻港英军司令在日军司令部半岛酒店正式签署投降协议,香港史将当天称作「黑色圣诞」。12月28日,日军分别在九龙弥敦道与港岛轩尼诗道举行胜利入城仪式。日军在仪式后四处狂欢庆祝,这是香港居民经历噩梦的伊始。日军四处搜刮物资、寻索女人。日军中将酒井隆后来招供,他自率领部队进驻港岛后之半个月来,纵容部属「实行大规模之屠杀奸掠,借以报复,而逞淫威。」又据唐海记述:「他们三二个一起,敲打随便那一家的门户——这几个晚上,许多女人吓得在三四层楼的屋顶上乱跑,瓦片被踏得发出破裂的声音,很多女人遭到了侮辱,他们有被三个敌人一起轮奸的」。圣士提反书院伤兵医院里的170名伤兵,即使是投降了,也全部遇害,而七、八名护士则难逃被奸杀的恶运。
用「人间炼狱」形容沦陷后的香港境况,绝不为过。著名诗人戴望舒因从事抗日活动而被捕入狱,他于域多利监狱受尽折磨。他的《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诸诗,十分形象地描述其受到的虐打:
做柔道的呆对手,剑术的靶子,
从口鼻一齐喝水,然后给踩肚子,
膝头压在尖钉上,砖头垫在脚踵上
听鞭子在皮骨上舞,做飞机在梁上
荡……
戴望舒还是幸运的一个,没有惨死狱中。对于当时不少市民而言,人命贱如草芥,朝不保夕。日军滥杀无辜的事件无日无之,血腥场面随处可见。据当时人的忆述,一名小童在没有挑衅日军的情况下,被日本士兵开枪射中腹部,以至「肠脏溢出,已出现腹膜炎」,幸好小童母亲懂日语,否则「会被日兵弃在路旁」,忆述者声称「这些事件不胜枚举……」。另有中立国居民忆述乘坐渡轮过海时的所见所闻:「海里全是漂浮发胀的尸体。市内已有太多尸体尚未埋葬,浮尸因此无人理会」。她也在回家路上看见多个男性华人被吊起绑在栏杆上,双脚离地一呎。这些被打伤的人或已死去,或仍在垂死挣扎。她形容这种情况「举目皆是」。如今读此文字,仍教人触目惊心。
香港沦陷期间,日本籍牧师鲛岛盛隆恰好派驻香港。在他帮助下,香港圣保罗女书院逃过被日军蹂躏的厄运。他笔下讲述了日军在港疯狂行径以及香港居民受到的深重伤害。其中一人便是香港女教育家、香港第一位女博士兼第一位获得英皇勋衔的女性华人胡素贞。她作为圣保罗女书院(圣保罗男女中学前身)校长,鲛岛指她下定决心舍命保护四十多名女学生,「不遭军士的暴乱或强奸,她以这种悲壮的决意,尽力设法,掩护学生」,「保护她们不受像其他占领区所频频发生的那种暴力凌辱」,这让他深深佩服胡素贞的担当与勇气。然而,为了保护学生及校舍免受日军蹂躏,胡素贞承受著极大的精神压力。她因过于惊恐,三、四年下来,双膝因颤抖而永久损伤,不能再上下楼梯,导致她后半生要依靠轮椅代步。
日军的残暴统治,对于时人的精神如何折磨、造成何等的伤害,从上可见一斑。
实行「归乡计划」:草菅人命,饿殍遍地
日军在香港先后成立军政厅、总督部,暴力执行社会管控规例。《香督令》是香港占领地总督矶谷廉介颁布的法令,内容细如牛毛,日军可以随意指控华人是否触犯法例,当街打骂,甚或将之囚禁,乃至杀害。如果市民在街上没有向站岗日军行鞠躬礼,轻遭拳打脚踢,重则开枪杀害。宪兵队更常以搜查抗日分子为借口,擅闯民居,奸淫掳掠。
为了管制言论和消息传播,所有新闻通讯及文化活动均遭严格审查。取而代之的,是当局强力移植日本文化,建立神社、筑造忠灵塔,灌输日本帝国意识和价值观,向香港华人进行思想洗脑,实施赤裸裸的「日本化」文化侵略。以教育范畴为例,当局以日文取代中英文教育。华人办学权利被剥夺,1941年香港学生人数约12万人,至1945年仅余3,000人,学校则由600所跌至20多所。香港固有的公元历法被日本历法(如「昭和」年号)取代,日本节庆(如天皇寿辰)被列作香港公众假期。香港的时间被调快一小时,保持与日本时间同步并行。日本的街道名在香港也大行其道,港岛的干诺道改为「住吉通」,德辅道改为「昭和通」,西环改为「山王区」,太子道改为「鹿岛通」;英资连卡佛百货公司改称「松坂屋」,动植物公园改称「大正公园」,半岛酒店改名「东亚酒店」。「日本化」、「皇民化」的景象,于当时触目皆是。
文攻武吓,是日本占领地总督府统治香港的基本方式。但对于管治香港这个地少人多的地方,单靠文攻武吓在当局看来还是未能稳定香港的。太多的人口,会使这个地方产生很多问题。香港早于沦陷前,人口便已高达160多万。太平洋战争一旦爆发,输港物资停顿,粮食供应短缺。故当日军从英人手上夺得香港统治权后,便开启了「归乡计划」,逐步迁移没有固定职业或专业技能的平民离开香港。日军为便于人口管治与粮食管制,设立住民登记证及离港通行证。一些从事机械作业、工厂、农业及生活必须品生产等固定职业,或者是军方认为有需要的人士,得以留下。他们平时上街必须随身携带住民证,否则要面对日军当街随意施加的军罚。当局于1944年3月进行了严厉的户口调查,若有人没有整齐站在屋前街道候查而走出马路,即被开枪击毙。若家庭成员不齐,整家会被拉往刑讯。一次人口调查,便有数千市民被捕或被杀。
1943年后期,日军在东南亚与中国的战事相继受挫,香港的货运停顿,各种物资被日军优先调运前线与日本本土。为控制粮食与物资,日军采取残暴的武力抓捕乞丐、无业游民、流浪者,或把他们遣送至离岸孤岛自生自灭,或将他们强行押解出境,甚至是半途弃置,酿至多人饿死、病死或因风暴葬身大海。小林英夫指出:日军「将处于弱势的老人、妇女、儿童遗弃到偏僻的小岛或者人迹罕至的中国沿岸地区。以一天减少1,000名中国人为目标,在占领香港一个月的时间就让23,000名华人惨遭如此命运。 」
一些身体健壮的劳工,被运送至海南岛开采铁矿,他们在恶劣条件下因疾病或虐待而死亡,五万人中有四万五人因工作过劳或被日人虐待致死,还有120名华工被日军刺死。1941 年 12 月至 1943 年 9 月,近 100 万人被强制遣返,香港人口因而骤降至战前的一半。至1943年底,香港人口急降至80万,1945年日本投降时则仅余50至60万人。进言之,香港于日占期间每月平均减少二万三千人,而1945年的首八个月出生率则只有三千七人,说香港成为死港,实不为过。
1943年后期,香港经济濒临崩溃,万物通涨几近失控。日军把香港居民原有的银行存款冻结,以军票全面替代港币。1941年 12 月底是 1日圆兑换2港元,大半年后即调升至 1日元兑换4港元。日军禁止港币流通,强制兑换,这导致港币大幅贬值,民众悉数沦为破产者。但凡有抗拒不用军票者,均会受到严刑对待:
在日本总督通令禁止使用港币后,日军便大肆搜查,一经发现居民依然藏有港币而未兑换的,则施加酷刑,毒打、「灌水」(把污水或辣水灌入腹中,然后踏受灌者腹部,使水从口鼻喷出)、「老虎櫈」、「脱指甲」、「夹手指」、「放飞机」等,无奇不有,被施刑者往往因抵受不了痛苦而死亡。
至1945 年 8 月,军票发行量高达 196 亿日元。军票泛滥,不只香港居民财产贬值破产,更加导致通货膨胀失控,经济崩溃,百业停顿。米、肉类、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价格飙升。如1945年米价高达90元一斤,花生油128元一斤;百物腾贵,涨价数倍乃至数十倍,远超一般市民的承受能力。如有军票者,还可以换取粮票,然后再凭票换米。然而,粮荒下每人一天最多只能换取六两四钱大米,即约200克或一碗白饭的份量,是不可能让人吃饱的。于是,市民面黄肌瘦,饿殍满街,每天大批人饿死。小林英夫指出,社会出现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惨不忍睹景象:
街上到处都是死人尸体。搬运尸体的人一个抱着头、一个提着腿, 然后再把尸体放到车上。即使是尚有一丝气息的人也会被当作死人埋到坑里。
在贫困生活中饿死的人增加,尸体被随意搁置,甚至出现抢夺尸体争相食用的悲惨境地。据说小孩子被随意带走杀害、贩卖孩子肉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据鲛岛隆盛所见,饥饿迫使部分穷人捕食犬、猫、鼠类,甚至传闻有人食人肉。街头可见剔除老鼠毛发者及被剥皮的婴儿尸体,反映生存环境极度恶化。他描述了这样的人间地狱:
天下再没有比那些受军队淫威所欺凌的民众更可怜的了……战争的恐怖、不安与暴虐仍然到处弥漫。——日渐面临粮食、饮水、燃料、电力等生活必需物资的缺乏,因而民面有饥色,野有饿莩,街巷且常见有无人照顾的遗尸。当时,有一种叫做「尸体搬运车」的令人生惧的车箱,每日巡驶清理路上的尸体。路上的遗尸越来越多……兼以美军飞机开始了频繁的轰炸,每次突袭,总是死伤惨烈。
值得注意的,民众惨受日军逼害外,他们数年来也如鲛岛所说的,一直承受来自盟军空袭造成的二次、三次伤害,以至骨肉分离,朝不保夕。日军投降前夕,整个香港早已是满目疮痍,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今天回首,仍不禁使人胆颤心惊。
直至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香港终于摆脱了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痛苦岁月。
以史为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就在1941-1945年这「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岁月中,值得自豪的就是──香港仍有一支勇敢的队伍在抗敌护土。以新界居民为主力的港九独立大队(1943年年底并入中国共产党广东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为香港境内的重要抗日武装。东江纵队在山区开展游击战,袭击日军据点,扰乱日人的运输补给,以武力对抗巡逻日军,惩戒汉奸,营救数十名外国人脱离险境。纵队还未成立前的游击队员还参与了「秘密大营救」的工作,于1942年冒险护送邹韬奋、茅盾、何香凝、胡绳、胡愈之、于伶、柳亚子等八百名抗日文化人逃出日军包围圈。获得他们救助的,还有1944 年被日军击落的美军飞行员克尔,此举不但呈现了香港民众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身影,还向日军展示香港居民抵抗外敌的意志、勇气与能力。
香港的抗战历史,留下了无数的伤痕与抗争故事,这一切不仅保存于史料字缝间,同时也成为数代香港人的历史记忆。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岁月,是香港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也是铭刻在香港历史深处的一道永难愈合的伤疤。蓝塘道惨案、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日军擅闯民居奸淫掳掠、大批无辜生命被放逐至荒岛、满街饿殍垂死挣扎……侵略者的罪行,已被一一记入史册,也烙印于幸存者的口述史与回忆录中,这一切都成为中国人抗战历史记忆的组成内容。
抗战胜利纪念日,是召回历史记忆的时刻,提醒我们民族曾经经历的伤痛,让新一代知道中国曾经受到何等的欺压与伤害,从而了解国家的过去,认识当下的国家发展前景,培养出家国观念与保持清醒的时局观念,让父祖辈曾经承受的苦痛不再延续,也从先烈的抗战事迹中承传他们守土卫国的情志与爱国精神。
「和平」,从来都是得来不易的,它不是凭空而降的;无数人在实现和平的过程中受尽了磨难与苦痛,也有无数的先烈为此作出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我们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乃是为了延续和平的岁月,同时也要以史为鉴、自强不息,并且常存忧患意识,保持居安思危的清醒头脑,齐心合力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5年7-9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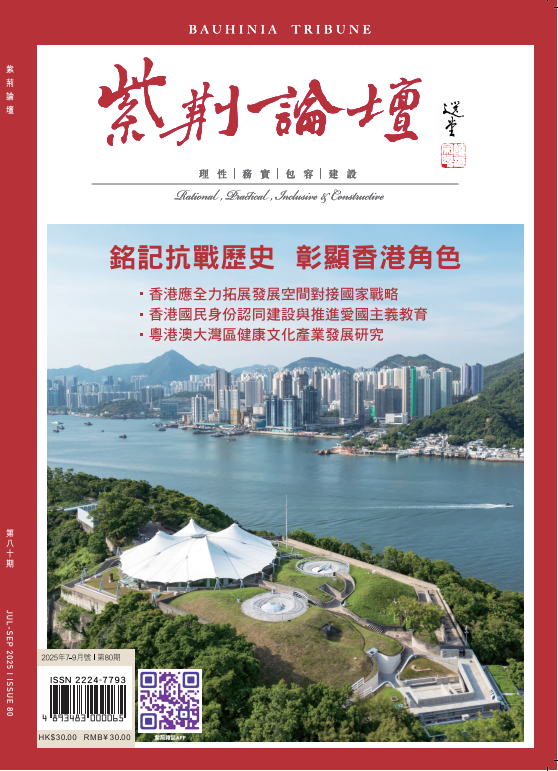







 今日热搜
今日热搜

 本周热搜
本周热搜

 本月热搜
本月热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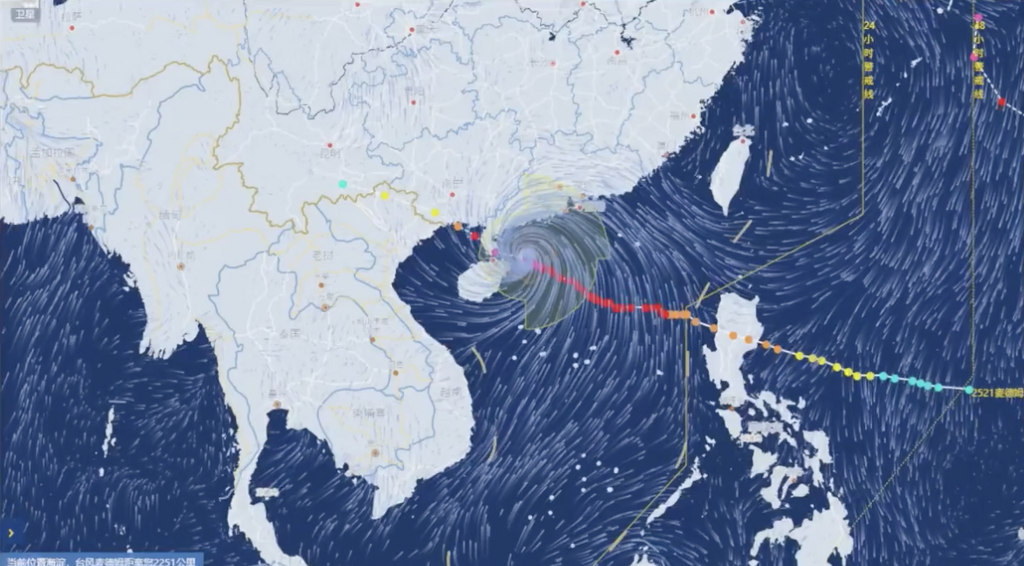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