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荆论坛》专稿/转载请标明出处
邢文威 | 亚太城乡永续发展学人
2021年,香港特区政府提出建设「北部都会区」(北都),力求媲美以国际金融中心为标志的维港都会区,成为引领香港创科发展的新引擎,形成「南金融、北创科」的全新经济格局,以促进深港合作,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随著北都建设进程的推进,此前少被提及的香港城乡关系成为关注的焦点。
引言
香港的发展常被描述为「从小渔村变为国际都市」,但香港目前仍有近600个乡村,其中北都范围内就有234个认可乡村。这也使得「城乡共融」成为北都六大规划原则的首位,愿景之一便是营造「城市与乡郊结合、发展与保育并存」的都会景观。
香港乡村发展面临著城市化背景下的普遍困境。作为高度城市化地区,香港无城乡户籍之分,逾700万人口中绝大多数生活在城市,但乡村面积远超城市,城市建成区仅约占总土地面积的25%,广阔疏落的乡村地带与高楼密集的城市地区相邻。自上世纪60年代工业化兴起后,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或移居海外,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诸多偏远乡村沦为空心村,香港遭遇了全球城市化进程中常见的乡村衰败问题。
北都整合元朗、北区多个新市镇、新发展区和发展枢纽及相邻乡郊地区,陆地面积约三万公顷,占香港总陆地面积的近27%。妥善解决乡村发展困局、处理好城乡关系,不仅对北都建设的顺利推进至关重要,更关乎香港的长治久安和「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
香港城乡发展失衡的历史脉络与成因
(一)港九优先发展导向下的新界发展空窗
1842年开埠之前,香港还是清朝边陲之地,受广州府新安县管辖,人口不足一万,是典型的农业社会。香港开埠初期,被定位为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外贸交易站,经济上以转口贸易为主,实行「自由放任」「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政策,城市规划重点在于香港岛及九龙地区,建立了规划制度和相应机构,维港两岸逐渐发展成为商业中心,形成了以维多利亚港为中心、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为两翼的城市格局,香港开始兴起以自由贸易港为核心的工商业发展及城市建设模式。
1898年,英国租借新界99年。不同于香港岛和九龙半岛是永久「割让地」,新界作为租借地,新界乡村原居民对土地永久持有,在土地权益方面与「割让地」不同。为了妥善处理新界原居民的合法权益,英国对新界并没有进行深远的改造,新界基本保持了农业社会的面貌。香港的城市与乡村,出现治理体系、产业类型、基建发展的高度分化,香港人口也主要聚居在城市地区。有学者认为,英国租借新界的真正目的就在于窥准新界土地的升值潜力,英国人在新界的统治以政治经济利益先行而不是注重社会文化实践,在处理新界村民的固有价值和制度上,也限于以土地为主。
(二)城市化主导下新界乡村的衰败困局
香港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一样,同样经历了城市化过程中乡村的衰败。二战之后,香港经济结构的改变,导致从城市转移出来的产业急于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内地移民来港叠加婴儿潮,人口由1945年约60万急增至1965年360万,同样需要增辟空间解决房屋供应问题。1973年,港英政府出台新市镇计划,于1973至1987年间,分三阶段在新界乡郊发展九个新市镇,将市区过于拥挤的人口和产业逐渐迁至新界。九个新市镇面积超过160平方公里,占新界土地面积达21%。到1996年,香港622万人口中已有292万人住在新界及离岛,占全港人口的47%。
在香港新市镇进程中,推行的土地流转制度,对拥有土地的原居民提供了经济诱因,但也导致了乡村农地弃耕、农业衰败。在人口方面,城乡产业结构、经济收益的日渐悬殊,令乡村居民投身于第二、三产业,乡村人口大幅外流。而临近城市建成区的乡村,因交通便利、相对廉价的住房成本、吸引不少城市人口居住,其传统的乡村形态日渐被城市同化。
香港城乡的互动关系,主要由城市化过程主导,乡村衰败与城市化相伴而生,加之未有完善的政策措施保障,偏远乡村未能吸引市场资本的投入,乡村发展陷入政府、市场的双重失灵,出现普遍的人口流失、产业不兴的衰败困局。
(三)历史遗留政策对乡村发展的深层制约
随著香港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港英政府时期的诸多政策措施成为了历史遗留问题。基于乡村传统的管治措施,与社会发展需要、现代法治观念等产生冲突。特别是实施的一系列土地政策,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方面,都存在较大的模糊空间。在随后的乡村发展中,土地问题成为核心的掣肘因素,衍生出棕地问题、祖堂地问题、丁屋问题等。这些都极大地限制了目前的乡村发展,甚至造成香港社会发展的重要矛盾。因此,检视历史遗留的乡村政策问题,破解发展阻碍,成为城乡统筹发展阶段的重要政策诉求。
因新界不同于香港岛、九龙半岛的租借地性质,以及港九地区快速的转口港发展,新界延续了成熟的传统农业社会面貌,乡村发展未受到重视。港英政府租借新界之初,即遭到强烈反抗,更无意深入介入新界治理,并积极利用新界的宗族传统、社会网络,维护新界管治。对新界乡村的管理,主要是以土地政策为核心,以行政手段将村民拥有的土地永业权改为承租权,挖掘新界土地价值,并以怀柔手段,安抚民众情绪。在这一时期,港英政府的乡村政策,主要基于传统的乡村功能,以建立土地管理制度、稳定管治为核心。
(四)乡村发展系统性支持缺失与治理困境
香港1,1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只有约4平方公里用作耕种,700多万人口中农业人口仅4,000余人,第一产业整体农业人口比例和农业GDP占比均低于0.1%,乡村对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较弱,常被政府忽视,也没有全面的政策来促进乡村发展和城乡融合。
此外,不同于内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香港乡村的农地属原居民私人所有。在香港进行乡村建设时,不仅要面对众多产权拥有者,往往还要面临私人产权与集体利益的冲突,这不仅给集体行动带来困境,而且阻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也让原居民缺少了经济层面重要的维系纽带。基于城市场景而制定的经营政策和牌照发放政策,往往也不适用于乡村场景。由于乡村人口的外流,政府减少了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这些问题都让原本已经衰败的香港乡村的振兴之路更加艰难。
在治理层面,历史上,香港一直缺乏系统的乡村发展政策,相关政策在不同时期分散于土地、治理、产业、生态等方面。自香港回归以来,虽已陆续开展对乡村历史遗留政策的检视和政策创新。但是,针对某一具体政策范畴的单一检视,并不能从整体上回应乡村发展面临的错综复杂的难题。
促进香港城乡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前文梳理了由1842年至今香港城乡变迁的主要发展脉络,香港乡村经历了城市化过程中的普遍衰败,并在可持续发展热潮中,以城乡共融探索复兴之路。随著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乡村功能不再仅局限于向城市输出人口、土地等发展资源,深刻认识当代乡村多元价值,成为妥善处理城乡关系的必要前提。围绕改善城乡关系、推动乡村发展,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相继开展探索乡村振兴,积极回应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问题。
(一)构建综合系统的乡村发展政策体系
香港乡村发展面临的问题具有复合型特征,既包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乡村衰败现象,也存在因特殊历史背景形成的独特挑战。自回归以来,特区政府虽对部分历史遗留政策进行了检视与调整,但单一领域的政策优化难以应对乡村发展的复杂局面。当前,香港土地房屋问题突出、社会贫富差距显著、城乡矛盾时有显现,亟需将乡村发展纳入整体发展战略,构建系统性政策框架。
建议成立跨部门的「乡村发展统筹委员会」,由政务司司长牵头,整合发展局、地政总署、民政事务总署、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等部门资源,制定香港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该规划应明确乡村在香港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定位,划定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文化传承等功能分区,建立「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社区主导」的多元协作机制。同时,设立「乡村发展专项基金」,重点支持土地整理、基础设施改善和产业培育项目,并通过政策创新吸引社会资本投入乡村建设。此外,应系统梳理现有乡村政策,消除政策壁垒,借鉴内地乡村振兴经验及国际乡村发展案例,结合香港实际进行本土化改造,形成覆盖土地、产业、文化、治理等多领域的政策合力。
(二)破解历史遗留问题,疏通乡村发展梗阻
历史遗留的土地问题是制约香港乡村发展的核心障碍,其中棕地利用混乱、祖堂地管理不规范、丁屋政策与现代规划脱节等问题尤为突出。这些问题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处理不当易引发社会矛盾,需以审慎态度推进改革。
针对棕地问题,应建立「分类整治、多元利用」机制,对污染严重、效益低下的棕地实施生态修复,对区位优越的棕地通过「土地共享计划」整合开发,确保原土地权益人参与开发收益分配。对于祖堂地,需修订相关法律,明确祖堂地权属登记规则,规范司理的管理权限与责任,建立祖堂地流转交易平台,在保障宗族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关于丁屋政策,应在尊重原居民传统权益的基础上,完善申请资格审核机制,鼓励集中建设新型丁屋社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避免零星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同时,针对空心村和偏远乡村的发展困境,需实施「精准扶持」政策。对人口流失严重的空心村,可通过「村屋活化计划」改造闲置房屋,发展乡村民宿、创意工作室等业态;对基建落后的偏远乡村,优先完善交通接驳系统,建设小型污水处理设施、社区服务中心等基础配套,打破「发展滞后—资源匮乏」的恶性循环,激活其作为城市人口疏解空间的潜力。
(三)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拓展可持续发展空间
新界乡村地带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北都建设为城乡融合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应总结新市镇发展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城市扩张—乡村衰败」的覆辙,构建城乡功能互补、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在空间规划上,建立「城市核心区—乡村转型区—生态保育区」的梯度发展模式,明确各区域的开发强度与保护要求。加强城乡交通网络衔接,规划建设连接新界乡村与都会区的快速公交系统,缩短时空距离。在产业协同方面,依托北都的科创产业优势,在周边乡村培育科技农业、创意设计、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形成「城市研发+乡村转化」的产业链条。
完善城乡要素流动机制,允许城市资本有序进入乡村投资符合规划的产业项目,同时保障原居民在土地增值中的合理收益。建立「城乡发展基金」,从城市开发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反哺乡村建设,用于改善乡村公共服务。通过制度创新,使乡村地区既能为城市发展提供拓展空间,又能借助城市资源实现自身振兴,形成城乡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
(四)珍视乡土文化价值,增强身份认同与社会凝聚力
乡村是中华传统文化在香港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承载著独特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对增强市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保护和活化乡村文化资源,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
建议开展乡村文化资源普查,建立「香港乡村文化遗产名录」,对传统村落、历史建筑、民俗活动等进行系统保护。支持太平清醮、林村许愿节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结合现代艺术形式开发文创产品,提升文化影响力。修复抗战历史遗迹,挖掘其背后的爱国爱港爱乡故事,将其打造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建议推动乡村文化体验与旅游融合发展,规划「香港乡村文化走廊」,串联特色村落、民俗景点和自然景观,开发研学旅行、文化体验等旅游线路。在学校教育中增加香港乡村历史文化内容,组织青少年参与乡村志愿服务、农耕体验等活动,增强对本土文化的认知与认同。通过文化赋能,使乡村成为传承中华文脉、凝聚社会共识的精神家园。
结语:以城乡共融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
北都的建设,标志著香港进入新一轮新界城市化进程。作为香港最具潜力的发展空间,这一进程必然围绕乡村地带展开,其核心挑战在于如何落实「城乡共融」原则——既要规避历史上新市镇发展导致的「城兴村衰」教训,破解发展与保护的长期争议,更要超越传统城乡二元思维,让乡村的历史、文化、生态多元价值与城市功能形成互补互动。
实现这一愿景,需以系统性政策为支撑,制定全域性、前瞻性的乡村发展战略,整合土地、文化、治理等多领域政策,破解棕地、祖堂地、丁屋等历史遗留问题,通过「利益共享」机制平衡各方权益;需借鉴内地乡村振兴与国际乡村发展经验,结合香港实际,构建「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社区主导」的协同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更要将乡村发展纳入香港整体可持续发展框架,让北都真正成为汇聚科技与文化、串连历史与现代的典范。
从根本而言,香港乡村振兴绝非局部地区的单点改善,而是关乎「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社会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唯有珍视乡村价值、激活乡村活力,才能拓展发展新空间、缓解社会矛盾,让城市与乡村在共生共荣中,为香港沉淀更深厚的人文精神打造更良好的生态环境,筑牢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5年7-9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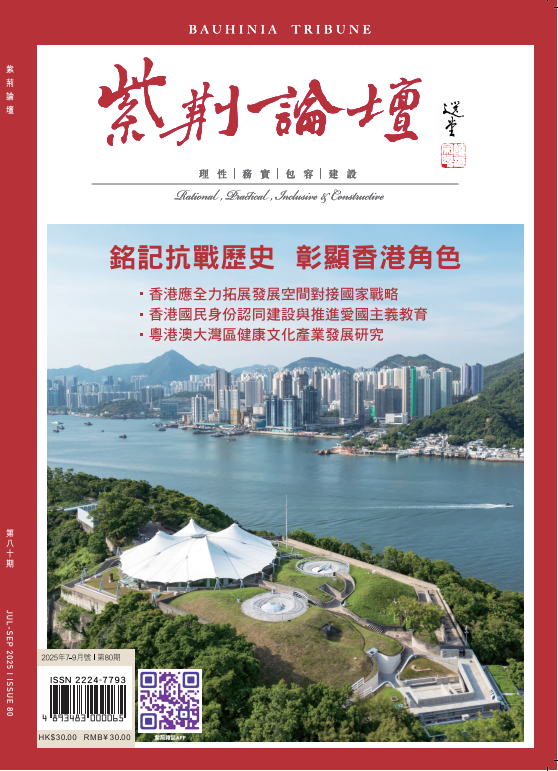







 今日热搜
今日热搜

 本周热搜
本周热搜

 本月热搜
本月热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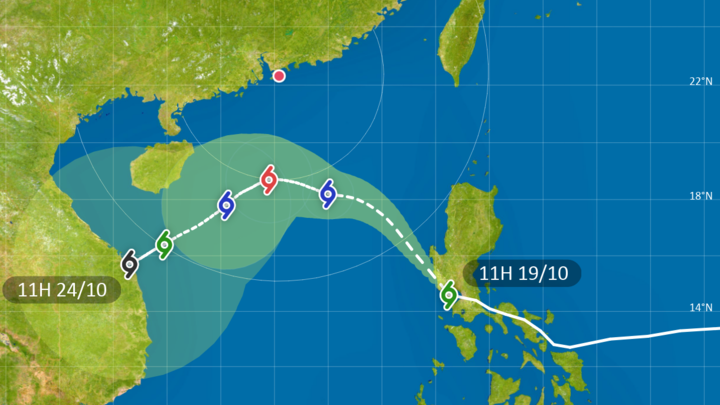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