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杨晨
“作为紫禁城和凡尔赛宫的主人,清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以及各自的宫廷成员,不仅以其品味与喜好各自主导两个宫廷的各方面,更以宽阔的视野和向外探索的意愿,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推动者。他们从未谋面,却在彼此的凝望和想像中,将两座宫殿、两个国家、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为其特别展览“当紫禁城遇上凡尔赛宫——十七、十八世纪中法文化交流”作上述序,将时间推回三、四百年前,欧洲法国与“远东”中国两个宫廷长达百年的“隔空之交”。两国不互派外交使团,但法国教士来华、器物跨洋远行、以及君主们对彼此国家和文化的浓厚兴趣与诚挚探索,使得中法双方在科学技术、工艺制作、思想艺术等多方面达成深刻且多元的交流。在与法国凡尔赛宫首席策展人玛丽-劳尔.德.罗什布吕纳女士(Marie-Laure de Rochebrune)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副研究员王文欣博士的对谈中,我们试图揭开浸润于中法文化交流时空缝隙中和缓浮现的细腻密纹。
科学天文迷与学院创始人:
康熙皇帝与路易十四
康熙帝自幼酷爱天文和数学,重视欧洲科学。此次展出的南怀仁款浑仪、盘式手摇计算器、黑漆彩绘钟等展品,以及一系列清宫仿制天文、数学仪器,都将康熙帝对科学的浓厚兴趣向当代观者“和盘托出”。同时期的法国,路易十四推动设立法国科学院,其中一部分成员组成“国王数学家”使团被派往中国,他们精通天文历法、地理测绘、数学、宗教,以及基本的中国文化与艺术常识。两位同是冲龄即位,推动各自国家成为区域性强国的君主以此种方式隔空相遇了。
玛丽-劳尔:
法国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并非法国最早成立的学术机构,法国首个学术院是为文学艺术而设的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 Française),法国科学院则成立于1666年。路易十四时期,财政大臣和海军国务大臣柯尔贝尔贡献了卓绝的远见,深刻意识到科学知识对高效政府体制及法国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科学院的创立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至17世纪,学院已吸纳70名成员,涵盖数学、天文学、医学、化学、地理学等领域的精专学者,成员间的交流对话极大激发了学术活力。
路易十四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君主,柯尔贝尔亦满怀壮志,他们希望将法国发展成当时欧洲最重要的国家。出于军事、地理等多重因素的考量,他们意识到必须借助学者们的博学广识来推动国家不断进步,各位科学家所作出的贡献也对这对君臣的蓝图构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创立法国科学院不久后的1670年,路易十四下令建造巴黎天文台,这座出自克劳德.佩罗之手的优美建筑直至今日仍然存在。克劳德曾著手设计卢浮宫柱廊,亦是现代童话奠基人夏尔.佩罗的兄弟。巴黎天文台的创立标志著天文学对法国君主的重大意义。彼时,天文学在整个欧洲是一门重要学科,修道院修士们在修习过程中需进行天文学方面的学习,以此构建起他们坚实的科学素养,在研习学院中,天文学与数学等学科均被正式纳入教学体系。
康熙皇帝和路易十四都对科学有著深厚兴趣,这一共同志趣令我在凡尔赛宫开展策展工作伊始十分着迷。在北京,我们曾展出一幅精美画作,当中路易十四被刻画为一位艺术与科学的庇护者。遗憾的是,这幅画作因过于脆弱而无法被带到香港来,但它却很好地诠释了本次展览的主题:两位君主虽相距甚远(8,000公里),素未谋面,但对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抱有同样的热忱。
另一件无法在香港展出的藏品是一条精美的法式挂毯,上面描绘了顺治皇帝和幼年康熙的形象,画中二人身旁站立著南怀仁(佛兰德人)和汤若望(德国籍)两位神父。南怀仁时任钦天监监正,负责观察天象、制定历法,该机构在当时的中国具有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康熙皇帝在幼年时期便已培养了对天文学的浓厚兴趣。而这件制于17世纪90年代的法国挂毯,也记载了中国帝王的历史,成为法国艺术界对中国审美意趣早期探索的典范之一。该挂毯所隶属的“中国系列”共包含九幅挂毯作品,通过这些瑰丽的针织品,世人得以一窥昔时挂毯制作工艺的精妙。
至于由中国传回法国的农学和地理学的相关知识,科学院成员们很可能仔细研读过耶稣会士寄回法国的信件,神父们曾撰写大量书信发往法国,详细记录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这些信件在18世纪早期便已公开刊行,因此科学院成员必然接触过其中部分内容。
不过,我认为真正迫切需要这些信息和信件的群体应该是法国政府官员,他们当时正著力寻找提升农业技术的方法,而彼时中国已掌握许多法国尚未知晓的技术,了解这些方法至关重要。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考量,政府对这方面的内容表现出浓厚兴趣。
“双向奔赴”的“痴迷”:
珐瑯工艺与制瓷艺术
在器型小巧、颜色亮丽、纹样细腻生动的金胎画珐瑯菊花纹壶壶底,曾经隐匿在跨洋定制时空烟云中的珐瑯工艺的秘密被发现,叙述这一故事的恰恰是珐瑯器表面釉料颜色的细微差异。法国制珐瑯使用锡石作为白色釉料的呈色剂,釉面呈锡白色,中国制珐瑯使用不同染料,釉面则呈砷白;法国制珐瑯的黄色成分为铅、锡和锑,含锑的黄色视觉上偏橘,中国制珐瑯的黄色则为铅锡黄II型。除此之外,法制珐瑯的壶柄和壶流部分并未施釉。展览将产自两个不同国家的同一器物同时展出,揭开文物身世之谜的同时,也将中法两国对彼此顶尖技艺的痴迷传达给观者。
玛丽-劳尔:
黏土特性的差异来源于所使用工艺与材料的不同。在法国,珐瑯工艺有著悠久的历史。珐瑯技艺最初起源于古代欧洲,主要兴盛于欧洲东部,即为今人所知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以及古拜占庭帝国的部分疆域。中世纪初期,珐瑯技艺在法国得到显著发展,并于13至14世纪演变为法国独具特色的工艺,发展极为成功。
至16至17世纪,法国形成了多种珐瑯制作技法,珐瑯逐渐成为法国一项重要的文化传统。当时最负盛名的珐瑯工作室多集中于利摩日地区。正如瓷器在中国拥有悠久绵长的文化传统,珐瑯在法国同样承载著深厚的历史积淀。
菊花纹壶采用画珐瑯工艺,法国作此类器物通常以金胎为基底。据现有考证,乾隆皇帝曾下令向欧洲订购珐瑯器,这批器物出自18世纪巴黎著名的珐瑯工艺师约瑟夫.科托之手。他曾为法国国王和王室显贵服务,在这次订单中则被要求在中国器型之上进行创作。
我第一次在北京见到这件小茶壶时,一度以为它出自中国工匠之手。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郭福祥先生向我展示了茶壶底部镌刻的“科托”款识,著实令人惊叹。清廷当年从巴黎购入这批器物,为广珐瑯提供制作范本,试图仿效法国珐瑯技艺。
同时展出的另外两件提篮型器,一件制于巴黎,另一件则制于广东。广珐瑯成功复刻了器物造型,但在釉色呈现上仍有所偏差,我猜想这也许是由于原材料所含化学成分的差异或所用技艺的不同导致的。术业有专攻,我并不十分确定,不过此种在釉色效果上的分别,恰好可以成为中法工艺对话的生动见证。
如同广珐瑯对法国珐瑯工艺精雕细琢的研习与模仿,欧洲和法国在挖掘中国制瓷技艺的道路上也屡遇崎岖。
玛丽-劳尔:
对制瓷工艺的追求不仅存在于法国,更遍及整个欧洲。13世纪初,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首次将中国瓷器带回到欧洲,人们惊叹于其工艺与品质,之后便陆续有国家试图仿制中国瓷。第一次成功的尝试发生在义大利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宫廷。时值16世纪中叶,文艺复兴将近尾声,美帝奇宫廷成功烧制出外观近似陶瓷的器物,但这并非真正意义上含有高岭土的中式瓷器,其原料为一种成分复杂的混合材质。尽管如此,美第奇宫廷设法制成了他们所得到的中式瓷器的仿制品,这些物件晶莹漂亮,表面施以酷似中式瓷器的釉料,虽然所用原料是完全不同的。
法国亦多次尝试烧制瓷器,其首次成功突破在17世纪。1670年,有人成功复刻了与此前弗罗伦萨所作器物十分相似的品类,在法国我们称其为未使用高岭土制成的软质瓷;另外,靠近巴黎的圣克卢和尚蒂伊也屡见陶瓷仿制品问世。仿制瓷器的每一次成功问世,背后都有一位重要人物推动其生产发展,譬如在尚蒂伊的瓷厂由王室旁系成员支持。各地瓷厂各自专注于对不同形状、外观的器物进行尝试。
直至1769年,有化学家在法国利摩日地区发现了高岭土,人们立即转而尝试使用高岭土制作瓷器。1770年,瓷厂成功烧制出第一件硬质瓷器,此后,人们便开始大量制作硬质瓷,软质瓷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但其生产数量锐减。硬质瓷的一大优势是更易烧制出尺寸较大的器物,例如大型花瓶;相较之下,软质瓷质地脆弱,在窑烧过程中容易塌陷而使器型遭到损坏。高岭土的加入使硬质瓷更加坚固,同时可以承受更高的烧制温度;同时,高岭土使得高温烧制釉面成为可能。硬质瓷的表面不易出现划痕,而软质瓷的釉面则较易受到损坏。
除了法国,其他欧洲国家也在尝试制作硬质瓷,例如德国的萨克森地区最早于1710年开始烧制硬质瓷,高岭土矿在萨克森的发现使烧制硬质瓷成为可能。
法国则经历了更长的探索过程。直到1730年,科学家对中国瓷器进行了成分分析,发现了高岭土的存在,但他当时认为法国境内没有高岭土矿。事实上法国境内确实分布有高岭土矿——如今我们已然知晓其存在,但在18世纪人们尚未意识到这一点。
交错美学:以金玉置饰以土石呈现
鼓形缠枝莲纹狮首耳瓶作为瓶器,体型较大,通体萤蓝,凹凸莲花纹环饰瓶身,瓶口和底座镶嵌大量金属,两侧手柄的兽首造型雕琢更见生动精美。金属与瓷的碰撞美学,是金玉和土石在质地和色泽上的独特交错与融合。
玛丽-劳尔:
这些金属镶饰并非用以保护瓷器,它们的存在在于彰显和强化瓷器之美。以金属装饰瓷器的做法源自中世纪,当时瓷器初传入欧洲,因其极度稀有珍贵,人们为之倾倒,在惊叹之余也加入这场对于美的展示,以最贵重的黄金为材料,辅以珐瑯工艺制作镶饰。例如14世纪法国贝里公爵所藏的一件著名青瓷花瓶(现存于都柏林的一间博物馆),最初便配有华丽的金质镶饰和珐瑯彩,直到19世纪,这些金饰件才被从花瓶上移除。在巴黎保存的一幅绘画中仍可见到该瓶当年配有镶饰的样貌。此种工艺为凸显器物的绝美与珍罕,与防护功能并无密切关联。

镶饰风格在此期间也经历演变。早期巴黎是闻名欧洲的镶金工艺之所;至18世纪,因金价高昂转为使用青铜。尽管材质改变,其核心目的仍在于雕琢器物美感,提升其艺术价值。此种审美取向或许今人看来略显奇特,但确为当时风尚。
一些镶饰还会彻底改变器物的原始功能。例如这件曾属路易十六的藏品,带有镶饰的花瓶造型显得神秘独特,独具异域风情,但仔细观察其原始部分,可知其此前被用作花园矮凳。饰件的加入完全改变了其功能,将其转化为花瓶陈设,既可置于华宅内装饰家具,更适宜摆放在庭院景观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在北京时,我们将上面的镶饰取下以作清洁,意外发现狮首饰件下竟隐藏著瓷制狮首造型,这表明当年的镶金工艺师并未随意增添任何元素,而是精准呼应了器物的原有形态,在其基础上进行创作。
令人惊异且意外的是,狮子的形象不仅在中国艺术中频繁出现,于法国艺术和古典艺术中亦占据重要地位。尽管狮子的造型存在差异,但其作为艺术形象在两国文化和艺术表达中均频频出现,此次展览令我深切体悟到这一点。早在16至17世纪,法国艺术作品中已出现类似中国“狮戏绣球”的形象,而中国艺术中的狮子母题同样源远流长。
王文欣:有趣的是,狮子并非中国本土的动物。
玛丽-劳尔:确实如此,所以狮子在中华文化中是否被视为异域意象?不过在欧洲,自古典时期狮子便是力量的化身。中国是否同样视狮子为百兽之王?在欧洲语境中,我们因狮子强健威猛尊其为百兽之王。
王文欣:狮子意象在中国文化中更侧重其守护属性。自西汉被引入中国后,其象征意义历经演变,逐渐成为镇守祥瑞之兽。
玛丽-劳尔:对我们来说,狮子更多的作为权力图腾存在,常被君王用以彰显威仪。法中两种文明赋予同一意象不同精神内核,实在耐人寻味。
在暗色展厅里,我们三人围坐光影交织处,地板上铺著厚重的、纹理细密的草绿色地毯,踩去颇有绒质感;身侧墙面上,路易十四致康熙帝的书信通过现代投影技术在墙上圈出明澈的矩形光域,17至18世纪中法两国对彼此的想像于此流转。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时间中两个遥远帝国的王公与民众,以我们此刻的方式,在思想与器物的褶皱间描摹彼此的轮廓。
(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5年4月号)







 今日热搜
今日热搜

 本周热搜
本周热搜

 本月热搜
本月热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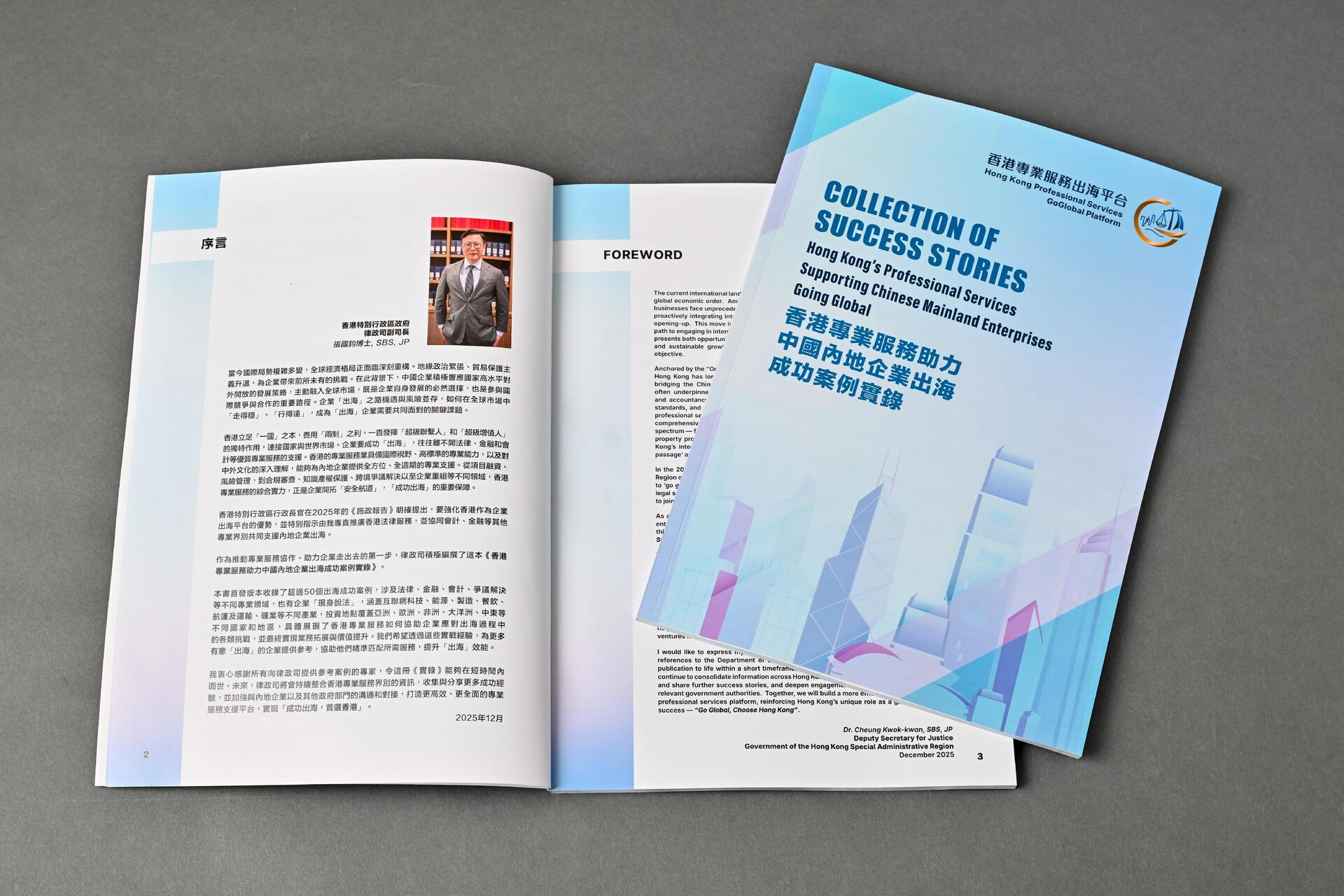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