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梦姣
五月芳菲,槐香沁人。
香港动植物公园就有一棵槐树,高8米,郁郁葱葱,据说是引进的树种。但真正能漫山遍野闻到槐花香的,却是我魂牵梦绕的老家。
返回老家,薄暮时分,散步于街心公园。道旁转角处,槐树林暗香氤氲,“槐花开了。”我快步走进槐树林,抬眼望,浓密嫩绿的卵圆形树叶之中,悬挂著层层叠叠的紫红花串,盛开的花朵密密匝匝拥挤在柔枝上,像一只只振翅的蝴蝶;含苞的花骨朵就如一颗颗紫红珠玉,圆润妩媚。攀下花枝,贴近面部,连续几次深呼吸。摘下一串仔细嗅闻,清香扑鼻,萦绕于心。“为甚么这里没有白色的槐花呢?”仰头站在槐荫中,脑海里浮现的却是一树树奶白色的槐花。
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一个学校完成的。那时,学校很大,没有围墙,校舍是一幢四合大院,院子后面是一个山坡,山坡上是一片槐树林。每到四月插田后,槐花就开了,花白如雪,白得纯粹、洁净,花香飘逸,每间教室里都可以闻到槐花香。
“叮铃铃”的下课铃一敲响,“摘槐花去!”一群男女生就急不可耐地冲出教室,跑到槐树底下。男生跑上坡,有的拿著长竹篙,有的拿著铁钩子;胆大的女生跟在后面,追上来,她们手里拿著各种各样的空书包,有军绿色的挎包,有手工缝制的花布包、蓝布包、灰布包等。他们聚集在槐树下,笑著、喊著、追打著。会爬树的男生蹭蹭几下就上树了,他们坐在比较粗壮的杈枝间,摘下近处的槐花塞进口里,放肆地吃,吃饱了,才会伸出铁钩,胡乱地钩断花枝。高大的男生仰头站在树下,举著竹篙猛扑树枝。不一会儿,绿色的枝叶、白色的花束飞落而下,铺满了光秃的黄土地面。叽叽喳喳的女生们拾起一串串奶白色的花束,摘去沾著的绿色枝叶,快速塞进书包。
少不更事的孩子,没心没肺地扑打著、钩断著、摘取著馨香的槐花,他们的脸上洋溢著欢乐和满足。他们抖落花束上的灰尘,捏著一朵朵白花塞进口里,吧唧吧唧地嚼著,不时发出一声声感叹,“沁甜的”。自卑胆怯的我总是站在远处,眼巴巴地看著那热闹的场面,咽著口水。槐树无言,树下那凌乱的残花、落叶、断枝亦无言。
上课铃声响了,大家一窝蜂似地跑回教室。同桌递给我一大捧槐花,他歪著头,扬起下颌,得意地笑道:“嘿,给你吃!”羞怯的我不敢接,他把花放到了桌上。老师进来了,我赶忙将槐花胡乱地收进桌屉,呆呆地坐了整节课,我的眼里心里全都是那洁白的槐花。下课后,我小心翼翼地将一串槐花拿出来嚼食,那种甜甜的、香香的、滑滑的感觉顿时充塞全身。
那一年,我10岁。没吃完的槐花带回家,妈妈用它炒蛋,给全家人当小荤。
成家以后,在很多地方生活工作过,也在很多地方走马观花过,但再也没有遇见过那种成片的、开满白色花朵的槐树林了。
今又闻槐花香,所见槐花,一串串、一簇簇、一朵朵,全是妩媚的紫红。那种奶白色的花朵,那种纯真的友谊,还有那快乐的少年时光,定格为影像,温暖余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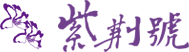





 今日热搜
今日热搜

 本周热搜
本周热搜

 本月热搜
本月热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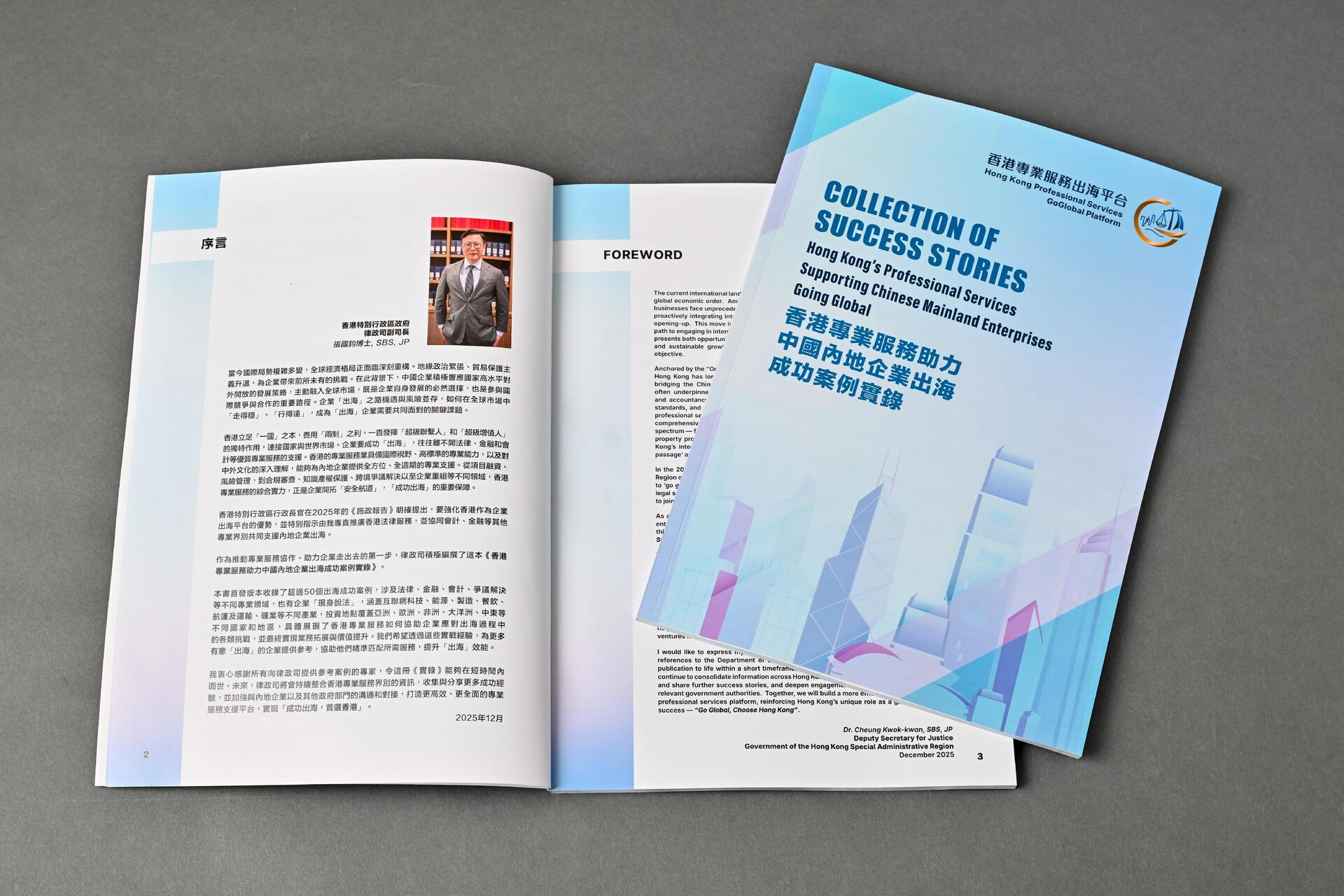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