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冯琳
2025年4月24日,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揭晓。按年代早晚排序,四川资阳蒙溪河遗址群、浙江仙居下汤遗址、甘肃临洮寺洼遗址、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成功入选。这十大从全国1,740项考古发掘项目中脱颖而出的重要成果,时间纵深漫长、空间分布广阔、涵盖内容丰富,进一步实证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度解码“何以中国”的历史基因。
发现世界级“百科全书”式遗址
在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中,有一项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评价为“世界级的发现”——四川资阳蒙溪河遗址群。这是一个包含了丰富石器与动植物遗存的“百科全书”式遗址,是旧石器时代中期唯一发现丰富植物遗存的遗址,埋藏著一系列国内最早阶段的行为现代性证据。
蒙溪河遗址距今8至6万年,处于早期现代人演化的关键阶段,其特殊的饱水环境难能可贵地保存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信息。独具特色的硅化木小石器与骨器、木器构成的立体工具体系,说明蒙溪河遗址的古人类已经拥有了因地制宜、灵活机动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认知能力。特别是86处以硅化木为主要原料制作小型石器的遗址群,有力地证明了过去被认为“落后”的东亚古人群实际拥有独特的聪明才智,他们不仅继承了本地的石器技术传统,还创新性地加工和使用了有机质材料的工具。遗址出土的核桃、橡子、花椒、接骨草等丰富的植物遗存组合前所未有,为认识世界范围内早期现代人采集行为提供了唯一性的新材料。

陈星灿指出,东亚现代人的由来是当今学术界与公众聚焦的热点问题,四川资阳蒙溪河遗址群为揭开这个谜题提供了系统性全新证据、填补了很多空白,是对东亚现代人起源、演化研究和源远流长的华夏早期文化发展认识的重大突破。
通过蒙溪河遗址,我们知晓旧石器时代人类已发展出复杂的适应生存行为。那么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又是什么场景呢?浙江仙居下汤遗址勾勒出了一幅画卷。
下汤遗址已发掘面积不大,为2,250平方米,但发现了几乎所有因素的遗迹,包括房址、“器物坑”、灰坑、墓葬、食物加工场、红烧土广场、沟渠、道路等遗迹,全面揭示了距今9,000年前上山文化中晚期中心台地、外围人工土台、环壕的三重聚落结构及其动态发展过程。
下汤遗址历经上山、跨湖桥、河姆渡、好川文化,纵贯本区域新石器时代的始终。陈星灿告诉记者,下汤遗址保存完好,各类遗迹和遗物极为丰富,全景式地呈现了早期农业社会的聚落形态和结构,为多学科研究提供了丰富材料,为研究我国南方地区早期稻作农业社会提供了重要样本,是我国南方早期稻作农业社会对一万年文化史、一万年文明起步的重要实证。
老遗址结出考古新果
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有许多是老遗址。所谓“老”,即发掘时间长。比如甘肃临洮寺洼遗址,自1924年起至今已持续发掘达百年。陕西宝鸡周原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等,也都经历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发掘和相当长时间的研究。
周原遗址是西周乃至先秦考古中罕见的大发现,过去曾发现大量窖穴以及零散的西周遗迹,但不成系统。“过去没有发现城,现在不仅发现了西周时代的三座城垣,而且发现西周之前先周时期的大型遗址。所以这样一下纲举目张,把过去几十年我们发现的一些散乱窖穴都可以画在这张图上。”陈星灿解释称,“有了这张图,有了现在的发现,把过去的发现都带活了”。
此外,周原遗址的发掘成果还使得诸多重大学术问题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比如,确认周原乃古公亶父迁岐之地,陈星灿认为这是先周文化近百年探索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近300字西周甲骨文的发现,特别是西周中期甲骨文、月相、国族名等诸多首次发现,为研究西周王朝以及它和各个诸侯国的关系都提供了重要线索。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最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之一,地处黄河上游核心腹地。寺洼遗址经过多年考古工作,发掘出一处马家窑文化的大型聚落,发现了三重长方形布局的围壕、近百座房址、大量的灰坑窖穴,另有疑似“道路”和大面积“人工堆土”的线索。其中,首次发现史前时期三重长方形布局的围壕,首次发现马家窑文化大规模制陶区,首次确认马家窑文化高等级、中心性聚落。陈星灿点评道,上述发现展现了4,8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地区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彰显了黄河上游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新高度。

盘龙城遗址是夏商时期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聚落,是探索长江流域早期文明进程的关键遗址。盘龙城遗址新发现的铸铜手工业作坊,更新了过去地方城市不能生产青铜礼器的认识。根据遗址景观环境的变迁,首次从考古学证据明确夏商时期长江中游水位变化趋势。首次发现的长江流域夏商时期石构遗迹,进一步表明盘龙城城市聚落的复杂性和突出规格。整体来看,盘龙城遗址的考古成果展现出中国最早的中央对地方的治理模式,以及早期中国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文明互动所催发出的璀璨文化,为深化了解长江流域早期文明进程、黄河与长江的文明互动提供了关键材料。
琉璃河遗址是目前发掘时间最长、面积最大、内涵最丰富的西周封国遗址。其新发现外城墙和外城壕,首次明确了西周封国中的两重城垣结构,城址范围由60万平方米扩大至近100万平方米。出土作册奂器有关“太保墉燕”的铭文,是北京城市建设史最早的出土文献,证实周初三公之一的召公亲自到达燕地主持燕都营建,实证了首都北京三千年建城史。通过人类全基因组测序,首次在商周考古领域复原古代家族树,是研究古代家族关系、社会结构的重大突破。
2024年考古界最大的“网红”,是安徽淮南的武王墩墓,被学界惊叹为“江淮遗珍、楚风绝唱”。武王墩一号墓的发掘,改写了楚文化研究的时空框架,为研究楚文化政治格局、礼制变迁与艺术成就树立了里程碑式的考古标杆。其中,“亚”字形九室多重棺椁为国内首见,椁木墨书数千字,内容涵盖方位、分室、木材性质与编号,是迄今等级最高、信息最系统的先秦墨书文献,为破解楚国职官制度与营造流程提供了“活字典”。
“因为考古工作是一门科学研究的工作,尤其是大遗址。我们现在说的最新发现,其实是长期研究的一个结果。”陈星灿指出。在他看来,这些连续发掘至今所获得的重要发现,把过去的重要发现也带动起来了,是“老遗址结出了新果”。
边疆考古发现汉代已实施“一国两制”
与以往入选项目大多分布于华夏中原地区不同,本年度入选项目还覆盖西藏、新疆、云南等边疆区域。这些考古项目为中华大地边疆地区的文化发展与文明演进提供了重要证据,充分彰显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大气包容。
在藏语中,“错”是湖泊的意思。玛不错遗址位于中印、中不边境的西藏中南部康马县嘎拉乡政府驻地东北面的玛不错湖岸,地处喜马拉雅中段北翼的高原,海拔4,410至4,430米。玛不错遗址距今4,800至2,000年,是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唯一一处新石器时代湖滨遗址,也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腹地海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也最为清晰的文化序列,展现了“世界屋脊”上先民依湖而生的渔猎图景。
“原来我们对西藏的了解是比较零星的,某一个区域某一个地方。玛不错遗址在长时段的4个时期可以看到有明显的变化,而且大约在距今3,300至3,000 年的时候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休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王巍分析指出,“这使我们对这个区域聚落的演变、聚落的布局、遗存的特点,特别是社会的分化有了解。通过它的遗迹和遗物,还可以看到和内地、和四川包括长江上游有密切的联系,也是证明了我们的交往、交流、交融”。玛不错遗址的发掘和发现,不仅对西藏考古,对世界范围内认识和理解高原人类适应演化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的发掘及其收获,是云贵高原地区考古的重大突破。考古发现揭露了汉代益州郡城址的主体布局,包括发现了主干道路、高规格衙署建筑区等城内主要功能分区,还出土了“滇国相印”“益州太守章”等官印封泥、大量有字简牍及“益州”铭文瓦当等重要实物。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教授霍巍称,这些考古发现实证《史记》《汉书》等文献所记载的“西汉置益州郡”的史实,也弥补了汉代基层治理考古发掘资料的缺失,揭示了中央王朝通过“赐滇王王印”、推行郡县制的柔性治理,对云南实施了有效行政管辖,最终推动西南边疆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霍巍总结,这样一种灵活统治的管理方法是中央王朝在边疆治理中最早实施的“一国两制”。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始建于公元1世纪,废弃于9世纪末10世纪初,延续约900年,是迄今发现我国最西部年代最早、延续时间长且发展演变清楚、保存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筑佛寺遗址。经过六年持续发掘,清理出大规模寺院建筑群,出土了极具特色的石膏佛教造像、铜钱及石、陶、木、丝织品等大量遗物,系统地揭示了寺院建筑构成,主要建筑的形制结构和功能性质,以及寺院布局变迁,理清了遗址的兴衰历程。
莫尔寺遗址地处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交汇处,是佛教东传我国第一站,晚期遗址融合了印度、犍陀罗、中亚、当地和中原多种文化元素,并且存在与武周时期所建造汉大云寺关联的可能性。“在这个佛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多种宗教在这个地方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融合的。”霍巍指出,莫尔寺遗址提供了我国早期佛寺布局及其发展演变的样本,推进了丝绸之路佛教考古、我国早期佛寺起源和佛教中国化研究,是文明交流互鉴和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有力见证。







 今日热搜
今日热搜

 本周热搜
本周热搜

 本月热搜
本月热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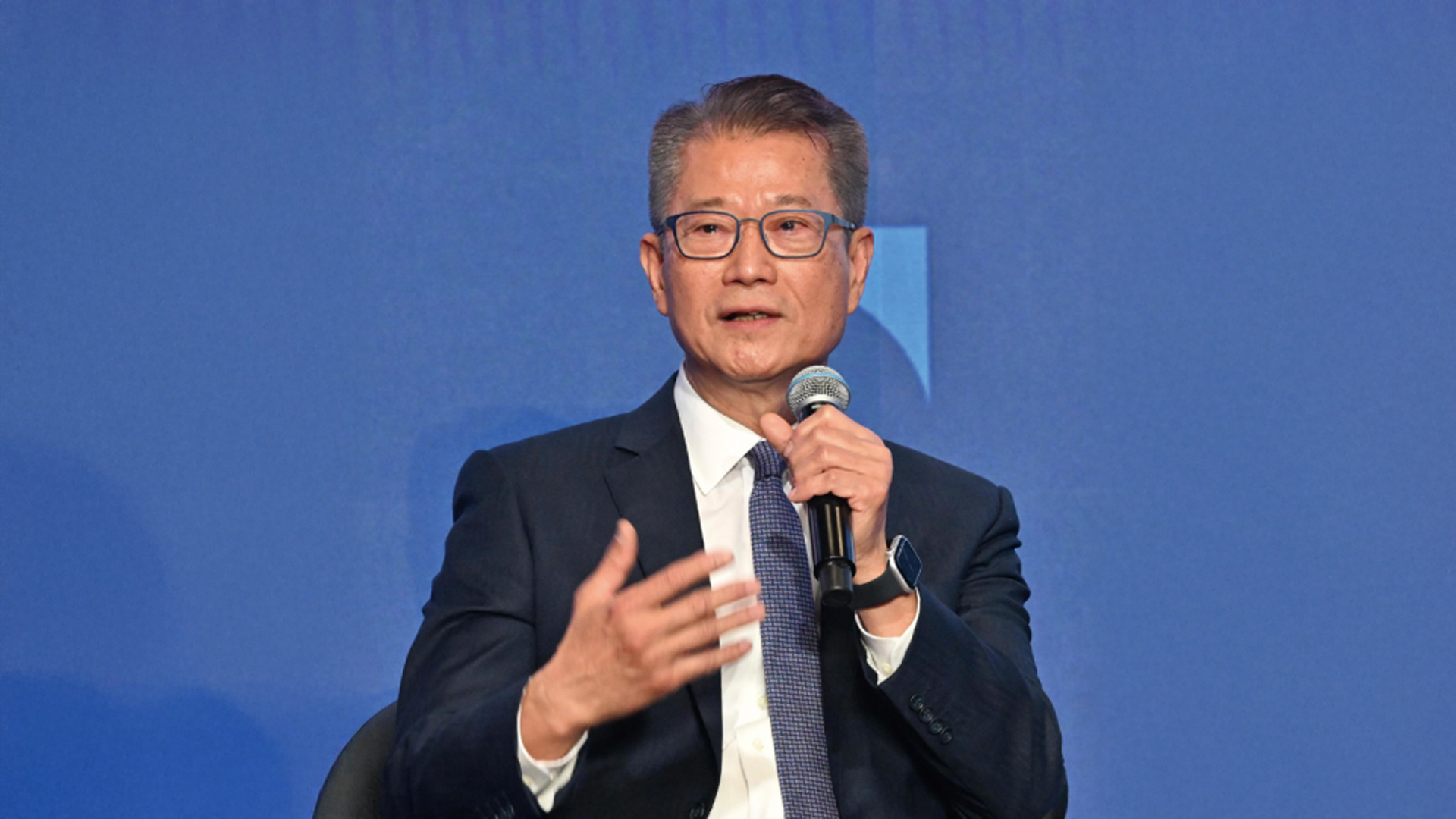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