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酸枣小孩
天下大一统,古今同此热。虽然现代人拥有了名为“冷气”的降温良品,但是此物你又不能出门携带,吹冷气时间太久还容易生出“冷气病”来,不如热点好。
古代虽然科技不发达,多少也有几个可以抵御炎热的“法宝”——最常见的:竹夫人、扇子、冰块。冰块属于高级避暑设备,非寻常人家所能享受的。即使如李太白、秦少游之文人雅士有所权位者流也未必能够或者时常享用。
秦少游写过一首自然主义派的《纳凉》诗:“携扙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秦少游是江南人,江南多水,夜幕降临,凉风乍起,水畔柳下自然是纳凉避暑的好去处。
相对于秦少游的婉约式纳凉法,李太白则是颇具魏晋风度的豪放款了:“懒摇白羽扇,裸体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
——洒脱不羁如吾故乡人。
吾之故乡,茫茫大平原。无水,亦无山。眼中所见,只有连绵起伏的大沙岗。大沙岗是故乡人的避暑圣地,也是我记忆中的乐土。
无数个月明星稀、热火缭乱的夏夜,人们在自家院子里吃过了晚饭,丢下饭碗,甩一把汗水,抱著凉席枕头床单,扶老携幼,呼朋引伴,浩浩荡荡向村东的大沙岗进发。
大沙岗上的沙是质地细腻的黄沙,里面含著一些矿物质。白天的太阳光照耀下,还会金光闪闪。我曾经拿著吸铁石去里面找过金子,想发点意外之财,结果只吸上来一层细碎的铁屑。
夜晚的月光下,沙岗并不会银光闪闪,而是像水波一样宁静。白昼的余温消逝之后,人躺在沙土上就仿佛卧于清凉的水波之上。不远处是飒飒生风的大杨树,身边的母亲正和相好的妇人窃窃话著家常,远处的父亲正和他的死党们边吸烟边说著乡村版聊斋故事。头顶上皓月当空。不知不觉间,你就会沉入黑而甜的梦乡。
小时候经常在沙岗上过夜,早上被露水惊醒,一睁眼,大人们早就下地干活去了,只剩下几个睡懒觉的小孩子。睡眼惺忪地爬起来,抱著睡具踉踉跄跄地回家去。
闹过一个笑话。有一次睡到半夜,尿急,起来小解,然后摸到凉席倒头便睡。早上被大伯母喊醒,发现自己竟然睡在三堂哥的凉席上。“睡错床”这件事后来被当作典故取笑了好久。
夏日炎炎,夜间屋子里待不住,除了刮风下雨的天气,整个夏天的夜晚,我们几乎都要在室外度过。大多数时候会去大沙岗上纳凉,不去大沙岗的时候,就在院子里铺上凉席,一个挨一个地睡觉。有时候也会爬上厨房的平房顶上,铺上凉席,一个挨一个地睡觉。没风的时候,母亲就在旁边为我们扇扇子。
有一年夏天带小哈回故乡,夜里热,于是一大家人全都爬上房顶凉快。一字排开,躺了七八十来口人。夜空晴明,繁星密布,一条银河横穿其中,看得见北斗星和牵牛织女星。这样的情景也是许多年不曾有的。
那天晚上后半夜突然起了大风,呼里哗啦的,一家人全被惊醒,逃窜回屋里了。小哈耐不住热,哭喊著非要再回房顶上睡,于是只好抱了厚厚的被子再次爬上房顶,在狂风呼啸里过了惊心动魄的一夜。
想起杜子美的那句诗来:“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虽然不合时宜,气势却是相当的。如果那夜的风再大上一二级,说不定我们也会如那屋顶上的茅草被卷上天去了。
纳个凉也得具有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今日热搜
今日热搜

 本周热搜
本周热搜

 本月热搜
本月热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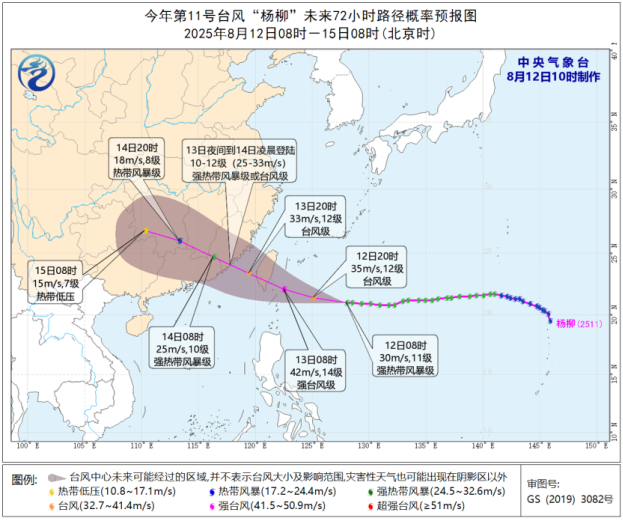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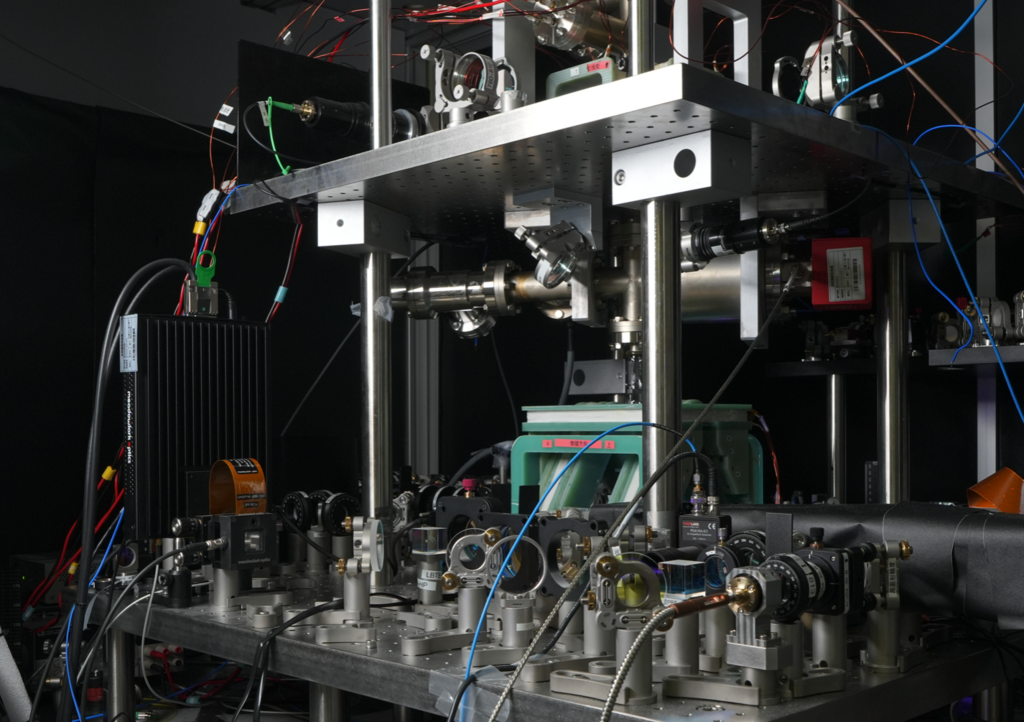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