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张清语 李天源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本刊记者近日走访部分香港抗日老战士及其家属,冀以历史细节留存香港抗战的珍贵记忆。曾经的港九大队“小鬼通讯员”、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会长林珍及“香港抗日一家人”罗氏家族后人黄俊康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讲述了那段烽火岁月中香港同胞的家国担当。
林珍:
8岁小通讯员传递“火柴棍”密件

受到家人的启蒙,爱国之心与家国情怀早已根植在童年时的林珍心中。1937年抗战爆发后,林珍的姐姐林展创办刊物、参与赈济活动等,于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从事地下工作,在日、台军人寓所做洗衣女工,期间因拒绝一名日本军人调戏,惨遭诬陷,被日本宪兵打得全身青肿。林珍告诉我们:“姐姐那时候绝对不低头的形象,对我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林展通晓英语,于1942年成为港九大队国际工作小组的主要成员,并于1945年任敌工科科长。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林展先后担任北平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中共代表方的译员及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的英文秘书。
1943年,8岁的林珍与母亲、哥哥参加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一到游击区,只有大概一周的时间进行准备,然后就正式开始战士的生活了。”林珍当时仍与母亲同住,但早晨军号一响,就要和部队一起出操,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虽然每天出操跑步的时候,我站在(操场)里边最小的圈里,他们可能跑两圈、三圈,我才跑一圈,但是也要跟著步伐一起走,那种马上要投入集体战斗的气氛,对我来讲影响是很大的。”
最开始,林珍被分配了通讯员的任务,“通讯班的班长大我七八岁,也只有十几岁左右的模样。”每次去新的地方送信,当时的通讯班班长都要带著她走第一遍,一开始是一个小时以内,后来距离慢慢加长,一路上需要经过哪些水沟、山坡、村庄,班长都会给林珍做记号。目的地交通站的名称、站长名字,接头时要讲什么话,都交代得清清楚楚。“那些密件像火柴盒那么小,卷起来像火柴棍,每次运送二至三个,藏在腰间、裤头。当时的任务执行得很顺利,老乡们也非常支持我们,我们什么也不害怕。”传递情报之余,林珍也帮忙印刷油印宣传品。“一整天总是没有闲著的时间,也因为自己能完成作为一个战士的任务而自豪。”
1944年,因战事愈发激烈,林珍与母亲被调至伤兵医院(战地医疗所)工作。“所谓医院,其实也只是大一点的寮屋。”林珍负责照顾伤员,后来也进行护理工作。当时医院的物资十分紧缺,“用过的药棉和棉纱不能丢,都要收集在一个篮子里,然后我们这些小护士拿到河边清洗,洗乾净后再晾晒、消毒,重新利用。”到冬天,因长时间泡在冷水里,林珍的手生了冻疮,“当时痒得刺挠,妈妈整个晚上给我搓,怎么搓也好不了。”被老乡知道后,给林珍煮了萝卜水,等水温降下来后把手浸在水里一直搓,慢慢地就痊愈了。“生活在游击区,跟大家在一起,什么难处都不怕。”
在伤兵医院中,如麻药等基本药品也十分缺乏。一些中弹的战士经常在手术的时候没有麻药用,“那喊疼的声音就像刺到我们心里头一样。”手术中的伤者喊叫得口乾舌燥,林珍就用沾湿的棉布给他们润湿嘴唇。“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等战士们的伤口好一点,他们就申请要回部队、继续战斗。”林珍亦曾协助救助在安装地雷时被误伤导致双目失明的蓝天洪和曾九,直到现在也仍旧与他们的后代保持著密切联系。
1995年,林珍重新联络上了当年的老战友,投入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的工作。“前辈们流的血换来了现在的和平,但现在的世界并不完全平安。要敢于保卫和平,才能永享和平。”
黄俊康:
“抗日一家人”是亲人更是战友

对家国的真挚情感,写就了“香港抗日一家人”罗氏家族的抗战史诗,罗氏家族的后人黄俊康亦为建设“香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作出卓越贡献。在罗氏家族中,罗雨中、罗汝澄、罗欧锋、罗许月及其配偶等11人曾参与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香港抗日战争。在战争里,他们既是血脉相连的亲人,更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国家的命运牵动著家族与个人的命运。罗氏一族为巴拿马华侨,罗雨中、罗汝澄、罗欧锋都是当时香港的高材生,“我大舅罗雨中高中毕业后在香港的洋行学做生意,二舅罗汝澄在念大学一年级,三舅罗欧锋在读高二。”据黄俊康回忆,因为自己的外公当时身体不好,三个舅舅已办好护照,准备去巴拿马接手家中生意。随著抗日战争爆发,南京大屠杀等惨烈消息传到香港,“他们看到了这些消息,于是开始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香港沦陷前,罗雨中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罗汝澄、罗欧锋到内地参加抗日游击队,日军进攻香港后,罗雨中担任第一支抗日自卫队“南鹿人民联防队”首任队长,罗汝澄担任过沙头角中队、西贡中队中队长和港九大队副大队长,三舅罗欧峰是海上中队中队长。母亲罗许月则是港九大队大队部交通站站长。黄俊康告诉我们,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一家人过了一段时间和平的生活。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他的长辈们又按组织的要求,到内地参加解放战争,并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攻坚。“他们百折不挠、坚守信念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曾为罗氏家族祖宅的罗家大院,以罗家后人出房和出相当比例的资助,已于2022年作为“香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揭幕,并向公众开放。黄俊康告诉我们:“2017年,罗氏后人从世界各地回来祭祖,一致决定将祖宅让出来作抗战纪念馆。”因为祖宅不能当、不能卖、不能捐,所以最后决定将其以每年一港元的象征性价格永久租出。在香港广州社团总会牵头下,总共筹集了两千多万捐款,历时五年,用民间的力量建成了香港第一个抗战纪念馆。黄俊康广泛参与纪念馆的设计、收集、筹建、运营管理等工作,“我曾与雕塑团队多次讨论纪念馆门口的雕塑,希望雕塑能够反映港九大队的特点:首先是知识分子较多,所以雕塑中的机枪手是戴眼镜的,这是我提出来的。他拿的机关枪是从日军那里缴获的歪把子机枪。女战士们在港九大队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雕塑人物里也有女战士。港九大队还有个特点,小鬼多,大部分是12 岁到15 岁左右的交通员,所以雕塑中也有少年的形象”。
“以前,一些香港人说,从不知道香港有这么英勇的抗日队伍。”黄俊康提到,“两年多来,即使沙头角地处偏僻,纪念馆仍接待了将近9万的参观者。”这让他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那些曾被淹没的历史,终于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重新回到了公众视野,可以为社会尽责,为前辈们尽孝。采访中,回忆起与父母、亲人共处时的点滴,已逾古稀之年的黄俊康忍不住落下眼泪。“我想告诉他们:你们的牺牲、拼搏,终于开始在香港被人认识和重视了。”
采访的最后,黄俊康告诉我们,他幼时身体不好,母亲曾向他讲过“铁沙梨”的故事:铁沙梨是港九独立大队里一个十四五岁的交通员,在一次战斗中,日军包围了他所在的游击队,他受伤后滚下山坡,连滚带爬走了五六公里山路才找到交通站,到了站就晕了过去,交通站的人立刻将消息转送总站,各部队随即做好应变准备。“铁沙梨”这个名字源自广东一带的沙梨:每棵树上总有几颗硬得像铁、摔不破的果子。讲述抗战故事,就是在延续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那些曾在硝烟中拼搏的、与我们血脉相连的人,那些如铁沙梨般坚韧的战士,他们的精神从未远去,正通过老屋、展品、口口相传的故事,化作滋养香港的养分,让爱国的种子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生长。这份在亲情与硝烟中生长的家国魂,终将代代相传。







 今日热搜
今日热搜

 本周热搜
本周热搜

 本月热搜
本月热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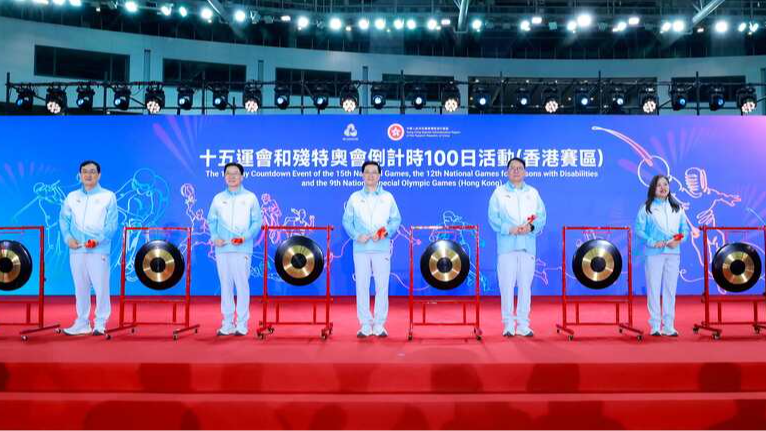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