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荆论坛》专稿/转载请标明出处
张瑞威 |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教授
2019年,时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中,提出重建三个市区寮屋区,即茶果岭村、牛池湾村和竹园联合村,以高密度发展增加市区公营房屋供应。之后,政府著手处理这三个村落的重建工作,其中牛池湾发展项目占地2.2公顷,除供应约2,700个公营房屋单位,还会提供多项配套设施,包括社区会堂、公共休憩用地及零售设施。在2.2公顷的发展土地里面,政府土地占1.6公顷,私人土地占0.6公顷。根据政府的资料,两种土地上共有约580个住户(涉及约900人)和约30个业务经营者。另外,工程将清拆约950个大部分为寮屋的临时构筑物。由于政府规定,所有受影响的牛池湾村民须于最迟2025年下半年分阶段迁出,目前的清拆行动可说是如火如荼。本文将叙述牛池湾乡的历史、现状,以及分析清拆结束后在古迹活化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
百年客家村落及其转变
牛池湾作为一个地名已经超过一百年了。在1866年由一位意大利传教士所绘画的《新安县全图》中,在今牛池湾位置上标示了「牛屎湾」的地名。对于这个富有乡土气息的名称,有年老的村民虽表示有听闻,但却不认同,指出牛池湾实本名「龙池湾」,亦正由此,现时村内一条主要的小径亦被命名「龙池径」。但无论如何,早在1819年编的嘉庆《新安县志》,已注明了「牛池湾」。
今日的牛池湾,由于二十世纪填海造地的关系,已经成为内陆地区。但在这之前,它是靠近维多利亚港的小湾区。雨水从北面的飞鹅山经两条溪流进入牛池湾,再出大海。这种靠山面海的河区,是发展农业的优秀地域。鉴于「客家人」的名称,是清初迁入香港地区的「客籍」人士转化而来,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牛池湾作为客家村庄,是在清朝以后发展出来的。
2001年,笔者曾两度探访了牛池湾乡,并与当时年纪最大的几位村民进行访谈。李先生说他的身份证的出生记录是1918年,但真实年龄已达87岁(即1914年出生)。据李先生的记忆,在他童年时期,牛池湾村以种禾为主,但在战前,稻田耕种已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种菜,俗称「耕菜园」,除了种菜外,村民亦养不少猪只和家禽。不过,李先生强调,耕菜园只是当时村民生计的一部分。不少村民,包括其父亲,都在当时当了海员,以补家计。也许是这个缘故,在李先生年少时,牛池湾村民房虽约有二百所,但年轻力壮的村民却不足二十。
离乡别井去当海员,反映出以往的牛池湾村并不富裕。李先生在回忆往事时,更以「穷乡僻壤」来形容牛池湾。直言是等于内地的贫困山区,建造房屋的材料很不统一,有的是泥砖屋、有的是散石屋(即是用不同大小形状的石头砌成),唯一比较可观的青砖屋,是刘姓村民在某年中了几万元马票而建成的,当时很「巴闭」(意为了不起),其实之前也是泥砖屋。很多人在三四十岁便去世,很少活到五十岁的,人丁很少。他们都是客家人,在牛池湾耕菜园、养猪。部分客家人打石为生,打地头石(即石板),但也强调牛池湾村本身是没有石塘的。也有许多人行船,主要是在远洋轮船上当西厨,做饼、蛋糕之类。
李先生告诉我村内的姓氏包括了杜、钟、刘、朱、李、谭、张、申、陈、廖、黄、杨、余、叶、冯、卢、曾、彭、吴。他估计牛池湾乡的历史大约有二百年,认为杜氏比较早来,然后是刘氏。至于他本人,是从祖父开始迁来牛池湾定居的,父亲则于光绪四年(1878)出生,所以自己是第三代。他一直讲客家话,到16岁才学白话没有认真读过书。他说卜卜斋(私塾的俗称)相当于中学程度,不是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的,穷人读两年书便要打工。
当询问到祖先的历史,李先生似乎有点模糊,说祖父迁来牛池湾之前,曾在西贡烂泥湾住过。他本人也曾回到烂泥湾找寻祖先的历史,发现当地是讲围头话,又叫「畬话」。他找到了当地的李氏宗族,看了族谱(不准带走),但没有发现自己祖父的名字。李先生似乎对此耿耿于怀,对笔者说族人名字不在族谱内可能有很多原因,例如族人在乡下曾被欺负,于是离开乡村后便不肯再承认自己的宗族。无论如何,这次的「寻根之旅」,也厘清了祖先的源流。他从烂泥湾的李氏族谱内,知悉了自己祖先来自江西。
李先生说牛池湾本身没有墟,也从没有听说当地有什么天光墟的市集,无论读书抑或买东西,村民都要去九龙城。按道理说,牛池湾可以是西贡人出九龙城的中途站,但李先生说,以前的人都觉得牛池湾人很恶,很不讲道理,所以西贡人都不敢走近。
牛池湾也有祠堂。杜氏在牛池湾的历史最久,在座的杜先生也说家有族谱。经笔者要求,他从家中找来了。那是薄薄的线装本,封面缺乏标题。翻阅之下,不难发现内容主要是杜氏简单的世系资料,包括了开基祖杜念五郎,杜氏后来迁到永安(即广东永安县,民国初改紫金县,与五华县相邻),而族谱最后一个祖先,便是杜先生的父亲——十五世祖杜庆荣。换言之,牛池湾的杜氏,只是纯粹延续永安杜氏,并没有自己的九龙开基祖。李先生告诉笔者,牛池湾有很多祠堂,例如刘姓有三个祠堂,杨姓也有三个。笔者参观了杨氏祠堂,那是一座用锌板搭成的房子。杨先生说由于政府在1970年代收地,原有祠堂被拆,但政府容许杨氏在之前的青砖屋旁边的官地上盖建一所寮屋作为祠堂。杨氏祠堂平时是锁起来的,开门进去,发现只放有一个古老神龛,神龛内写有四代祖先名字的木板。
作为一个杂姓村落,古老的牛池湾乡村民有两个祭祀中心。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是大王爷。大王爷虽是土地神,却是整个牛池湾乡的保护神。在以前,若牛池湾村民添丁,会在大王爷诞的时候去拜大王爷,并挂上灯笼以示感恩。另一个是社公,也是土地神,地位不及大王爷,属于水口伯公,社坛则建于自飞鹅山流下来东西两溪的汇合点。显然,这位社公的职责是盯住这一带的水势,确保不会泛滥。
牛池湾乡村民还举行十年一届的打醮,客家人叫做「安龙」。安龙的意思是「安置龙」,是将全乡代表龙脉的风水格局再次安顿,从而为该乡带来繁盛昌稳。牛池湾乡首次做「安龙」的年代已不可考,但前述的李先生在 1924年见过「安龙」。李先生指出牛池湾乡的「安龙」,与新界地区的「打醮」以及潮州人的「盂兰」作用相近,目的是「侍阴」,意即藉著向无主孤魂布施,祈求阖境平安。「安龙」是牛池湾的大事,村民除搭棚做戏外,还邀请道士做仪式。而附近乡村,包括衙前围村,均组织景色队,前来贺诞。最后一届「安龙」是1965年。
战后内地新移民的涌入,使牛池湾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简陋木屋。村民遂以社公为分界,将社坛以东地区称作东牛池湾村,而社坛以西地区则称作西牛池湾村。新来定居的村民不尽是客家人,他们除了耕菜园,还在村内搭建俗称「山寨厂」的小型工厂,其中包括了发泡胶厂、漂染厂和藤器厂等等。
来自五湖四海的新移民突然大量涌入,使原有的村落变得品流复杂。为了维持区内治安,乡公所应运而生。据《华侨日报》报导,1953年1月5日,牛池湾乡公所开幕,理事长和副理事长分别是赖富和冯荣,并在当日举行了一场小型足球赛作为典礼。牛池湾乡公所成立后,大部分乡内的土地业主都登记成为了会员。乡公所利用会员费,兴建学校、组织防火队、改善卫生、并向逝世的会员提供金钱帮助等等。于是乡公所成为了牛池湾乡的中心,完全取代了大王爷的祭祀组织。大概在这个时期,牛池湾村民添丁后在大王诞开灯的习俗也停止了。笔者考察牛池湾,当时的老人家还记得大王诞,但已经没有人记得诞期。
1976年,政府兴建彩虹邨地铁站,大大改变了牛池湾乡的面貌,包括了不少老屋被拆。作为对原村民的收地赔偿,政府在地铁上盖的地段建了两排平房店楼,即现今进入牛池湾乡大牌坊后看到的左右两旁的街市店铺和店铺上面的房子。
当时,建于地铁站附近的大王爷社坛也被清拆,迁至目前所在的位置。新的大王爷社坛坐落官地上,占地颇大,村民称之为大王宫。大王宫一共有三组社坛,呈品字形。中间的社坛是牛池湾的大王爷,有石香炉一个,刻著「甲寅吉年吉月」,应是指1974年。它的右边社坛,分为四个神位,从右到左写上了田心伯公、老屋伯公、杨屋伯公和河沥背伯公。村民告知,这些都是政府兴建彩虹地铁站的时候被拆的小乡村土地神。乡村被拆,这些土地神便被搬到这里安置了,过著「寄人篱下」的生活。
牛池湾社公虽然保存下来,但情况也不太妙。原因是社坛旁边的两条小河已经变成了污水沟,前面则建了公厕,造成社坛一带不单臭气难当,而且老鼠和蚊虫滋生。为了改善这个情况,2025年村民在污水沟放了至少两个老鼠捕笼,可能产生些许作用,但蚊虫还是挺多的,信众难以逗留片刻。
万佛堂的活化计划
2019年开始的牛池湾市区重建项目,将把牛池湾作为一个乡村格局彻底改变。除了大王宫以及被列为三级历史建筑的万佛堂将会原址保留外,许多旧建筑,包括牛池湾乡公所以及社公坛很大可能会被拆卸。
万佛堂是先天道妇女斋堂。坐落的土地来自两幅私人土地(SD2 Lot 1332、Lot 1656)的部分地带,另外也占用了部分官地。在Lot 1656的政府土地登记册显示,1915年,一位名叫Lai Yuk Tsing的人向Li Kung Po购买了这片土地,并在1931年以祖堂方式向政府注册,名万佛堂,而Lai Yuk Tsing 则成为司理人。
2001年,笔者考察了万佛堂。考察所见,它是三座相连的两层高建筑。笔者估计上层建筑都是给斋姑的住房;至于下层,位于中间的建筑物挂上石制「万佛堂」牌匾,是接待室。笔者在那访问了90岁以上的黎姑,以及负责日常打理堂务的女士,估计60至70岁之间,询之姓名,她说可称她作师太。访问中,师太说开山祖二姑婆,来自西樵,向牛池湾当地人买地,也不知是跟谁买,总之是分了几次买入土地,才逐渐扩建成今日万佛堂的规模(这个说法,相当配合目前的田土登记)。八十多年前,黎姑八岁,跟随姑妈来到万佛堂,从此住了下来。这位姑妈,就是开山祖二姑婆。
万佛堂的开山祖二姑婆应该就是土地登记册内创立万佛堂的Lai Yuk Tsing。Lai Yuk Tsing的事迹不详,但在1964年可能已经逝世,因此万佛堂的司理人改为Lai Wong Tai、 Tang Sze、Lai Ngau Nai和Lai Yiu Fong四人。四人之中,Lai Wong Tai应该比较重要,除了她在名单排首位外,还在1953年代表万佛堂登记成为牛池湾乡公所会员。会员登记册显示,Lai Wong Tai中文名字为黎旺娣,广东南海人,入会当年43岁(即1910年出生,在笔者2001年访问的时候是91岁)。如果八岁来到万佛堂,那便是1918年。至于师太,名字不详,据牛池湾乡村民介绍,她姓赖,也是从小进入万佛堂,被培养成为管理万佛堂的接班人。
万佛堂除了提供房间给独身的妇女安享晚年,还为她们安排死后的祭祀。在万佛堂的左边建筑物,挂上蓝色木板牌匾,上书「诚格幽冥」四个大字。进入这个建筑物,可以看到超过1,000个神主牌,分列左右由高至低排列,正中最高位置,安放了地藏王神像。访问期间,师太以「祖先」称呼这些神主牌,笔者估计她们都是曾在万佛堂居住的斋姑。
根据访问,万佛堂曾参与两次安龙清醮。师太强调,打醮期间,牛池湾乡全村吃素,市场和商店也不准卖肉,而村内的四间斋堂(金霞精舍、永乐洞、净室、万佛堂)积极参与,一齐拜忏三日。进行访问的2001年,当年参与安龙的四间斋堂,除了万佛堂,均已拆卸不存。不过,万佛堂的大厅内仍然挂著一张若干斋姑做「放焰口」仪式(作用是超渡孤魂野鬼)的照片。照片没有年份,但主要负责仪式的斋姑,隐隐就是师太本人。
万佛堂虽然是妇女修道的斋堂,一直与牛池湾乡公所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万佛堂司理黎姑是乡公所的会员,此外在万佛堂的大厅,挂有一个题为「显圣慈航」的大玻璃镜面,上款是「万佛堂惠存」,下款是「乙巳年牛池湾乡安龙值理会敬送」。考乙巳年是1965年,那是牛池湾最后一次的安龙清醮。访谈期间,笔者听到村民以「牛奶姑」称呼师太,当时虽然不知其意(许多年后的访谈才知悉原来师太小时候因为皮肤白,故有此暱称),但也感觉到双方亲切的关系。
在牛池湾发展项目中,万佛堂这座三级历史文物将被原址保留,而且会研究活化作商业用途。但据闻在政府进行收地的时候,一直难以接触万佛堂的司理或斋姑,因此传闻她们俱已过身,后继无人。
神明的安置问题
根据规定,牛池湾乡的村民须在2025年的下半年陆续迁走。在地政总署完成收地后,土木工程拓展署便开始进行土地平整和兴建相关基础设施,之后再把土地交给房屋协会分两期建筑三幢公营房屋。第一期公营房屋将提供约1,200个单位,预计在2031年第四季入伙;第二期将提供约1,500个单位,预计在2033年第一季入伙。换言之,将来的牛池湾,新型屋邨将完全取代原有乡村。
社公坛很有可能难逃被拆卸的命运。这对社公来说,可能是好消息,社坛的卫生环境实在恶劣,而且在将来的发展中,渠道应获得大大改善,所以也不大需要水口伯公来镇守河道了。失业的社公有可能被迁入大王宫内,反正目前大王宫左边社坛,由右到左,只是简单的写上伯公、伯婆。若社公迁入,便可以有专属的名号了。
大王宫坐落官地,一直是由牛池湾乡公所进行管理的。不过,乡公所也在清拆之列,那么大王宫的一众土地神,将来应由谁打理和祭祀,仍然是一个疑问。
神明安置问题上的最大挑战莫过于「诚格幽冥」屋内的地藏菩萨以及过千斋姑木主的去向。过百年来,这些木主的生前妇女,包括笔者访问过的黎姑和师太,进入万佛堂居住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死后有人持续供奉。在后续的活化过程中,木主应该留还是不留?如果把这些木主留下来,那如何对所在建筑物进行活化?若不把木主留下来,又应如何处理?在牛池湾发展项目进行的过程中,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5年4-6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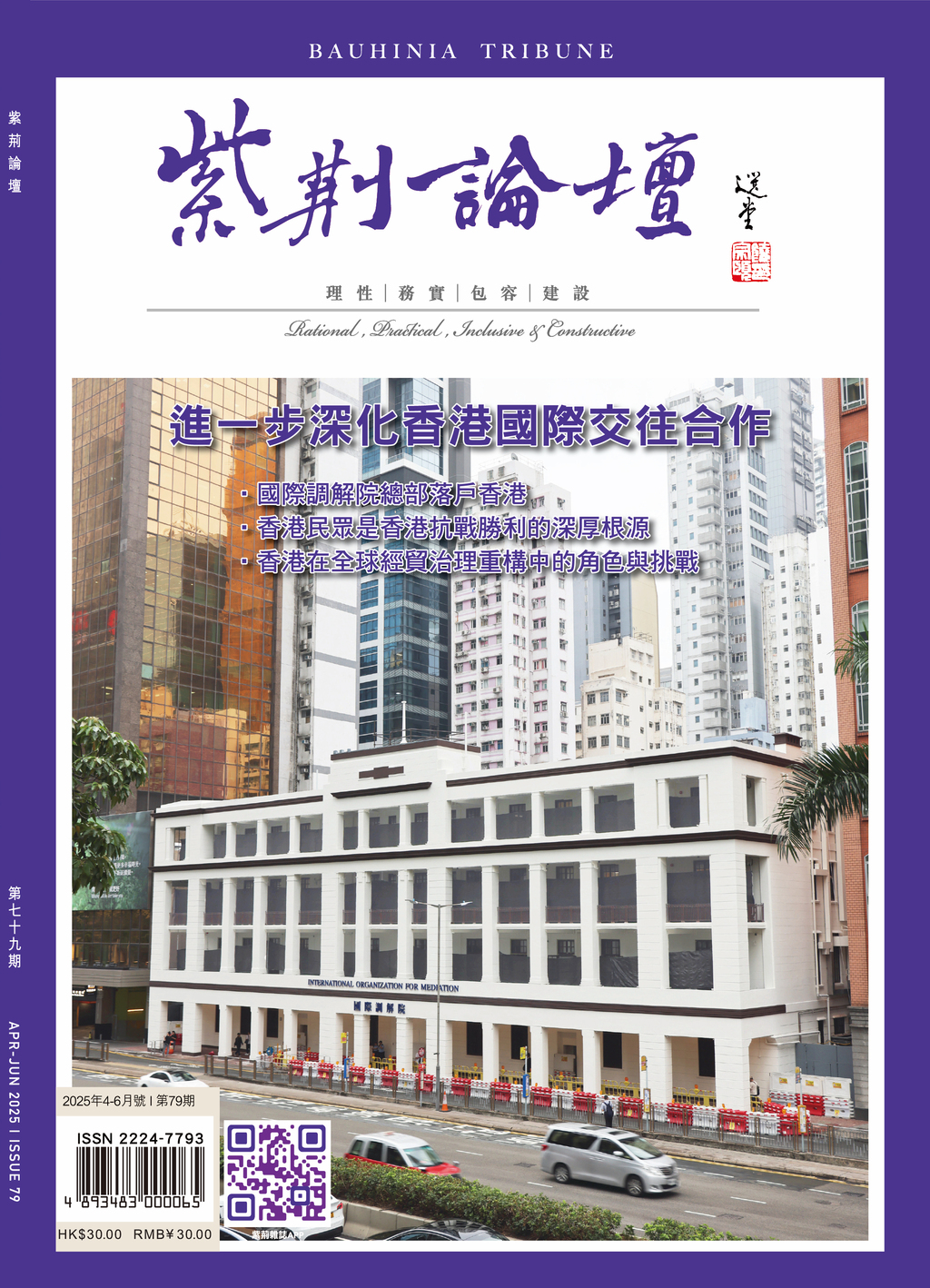







 今日热搜
今日热搜

 本周热搜
本周热搜

 本月热搜
本月热搜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