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荆论坛》专稿/转载请标明出处
刘智鹏 |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岭南大学协理副校长(大学拓展及对外事务)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武力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侵华罪行。发生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抗日战争是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斗,中国战士前仆后继,为捍卫家国献出了生命,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数以千万计的中国百姓以血肉之躯抗击日寇,取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可歌可泣,令人肃然起敬!
爱国精神深植于香港民众心中
战争期间,香港一如其他中国沿海城市,难逃被日寇侵占的厄运。不过,香港甫一沦陷即有游击战士在港展开抗日战斗,令香港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唯一能够坚持不断抗日的沦陷城市。这一时期的香港战斗基本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港九大队)执行。港九大队也是香港沦陷三年零八个月期间唯一一支成建制、由始至终坚持抵抗的抗日武装力量,是香港抗战的中流砥柱。港九大队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香港这一战略要地开展农村游击战、海岛游击战、海上游击战和城市游击战,有效地干扰了日军的战略部署,亦使驻港日军和汉奸终日惶恐不安。港九大队之所以能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之下克敌制胜,除了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指战员英勇无畏的爱国精神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香港民众的大力支持。正如毛泽东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所讲的那样:「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抗战时期,香港民众除了提供物质上的支援外,有的直接参军参战投身游击队行列;有的冒生命危险,为游击队传递信件、情报及物资,或借出住所,供游击队使用;有的甚至为保护游击队牺牲了宝贵的性命。在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回顾香港民众当年所做的贡献,对于弘扬香港的爱国传统,促进「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特别的意义。

香港民众举家投身游击队支援秘密大营救
日军的侵略行径和残暴统治激起了香港民众的反抗情绪,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许多香港市民争先恐后投入抗日军事斗争,更有一家多人参加游击队,如蔡国梁一家、叶文秋一家、黄作梅一家、林展一家、林传一家和有「香港抗日一家人」之称的沙头角南涌罗家等。罗氏家族有11人先后投身抗日游击队,当中以罗许月、罗雨中、罗汝澄、罗欧锋四姊弟的表现尤为杰出。
为配合部队的工作,罗雨中兄弟发动群众,组成「南涌人民联防队」(由港人组成的首支民兵队伍,罗雨中任首任队长),并将父亲罗奕辉的枪械献出,加强民兵的军事实力。该队伍积极执行剿匪及抗战任务,有力地牵制了日军。罗雨中通晓英语,多次参与营救国际友人的行动;罗汝澄是首位引领抗日游击队进驻香港的港人,后来成为首批潜伏于香港日伪部门的游击队员,并任西贡中队中队长、沙头角中队中队长及港九大队副大队长;罗欧峰是海上中队中队长;罗许月则是港九大队大队部交通站站长,曾参与护送抗日文化人及国际友人的工作。
日本侵占香港初期,中国共产党抢救滞港抗日文化人的秘密大营救是香港抗战史上的一个奇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武工队能够在日军严密控制之下,把几百名抗日文化人无一伤亡地护送到安全地带,香港民众的配合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2年1月1日,江水的短枪队护送廖承志、连冠、乔冠华等为秘密大营救开路的领导人到企岭下转船去沙鱼涌,途经山寮村休息,打算弄清情况后,转往企岭下经海路前往中国内地。江水事前将此事告知山寮村村长王亚元,请他帮忙接待客人并叮嘱他时刻注意敌情。为确保安全,王亚元预先派人到远处放哨,防范日军突然来犯,其后又在家里热情款待客人。他的真诚和友善,使游击队感激不已。
爱国华侨杨竹南则将自己位处杨家村的房子「适庐」借予游击队,作为秘密大营救的中转站及港九大队元朗中队的据点长达一年。当时约有一二百名文化人和游击队员在「适庐」居住和停留,包括茅盾、邹韬奋等。杨竹南深受队员尊重,被尊称为「杨伯」。1942年夏秋间,因走漏风声,日军曾前来扫荡,游击队闻讯早已迅速携枪械撤往屋后的担柴山。日军查无所获,于是将杨竹南带走问话,囚禁于元朗市区近一个月。杨竹南虽年近六旬,但面对严刑拷问,始终坚贞不屈,守口如瓶,日军最后只得将他释放。
香港民众为抗日队伍热心提供后勤支援
港九大队主要活跃在新界地区。不少乡民通过协助运输物资、捐献粮食、传递情报、照料游击队的起居饮食、救治伤病员等方式,默默支持游击队的抗日行动,谱写了不少军民协同抗日的动人事例。
港九大队大队部曾设在西贡赤径村。该村村长赵丙喜一家热心支援游击队的抗日行动。只要接到游击队的委托,他都会迅速组织村民完成任务;他的儿媳李有娣是赤径妇女会会长,曾多番动员妇女支援游击队,包括唱歌演戏宣传抗日、收割柴草、协助运输粮食、物资及传递情报、安排住宿场地、打扫卫生、帮战士补衣服、照顾伤病员等;他的三名儿子赵天富、赵华、赵天福都曾参加港九大队,其中赵华在大鹏湾患肺炎病逝。赵丙喜的兄弟赵新喜曾出洋打工,操流利英语,曾与赵丙喜、赵连胜在英军服务团成员驻守赤径期间提供食宿,照顾20多名从集中营逃脱的印籍英军战俘,并为他们安排交通工具横渡大鹏湾。赵连胜是港九大队一员,后来获授权在沙鱼涌收购食米,他将部分食米以原价售予赤径村村民,解其燃眉之急。
昂窝村村民凌娘无微不至地照顾游击队员,就像母亲照顾儿女一样,因而获得「游击队的母亲」之称。1943年初,民运员梁雪英患上大热症,病情严重得连医师也不敢贸然开药。凌娘得悉后马上到屋后把芭蕉树砍掉,搾汁救治她,使其得以康复,继续推动抗日工作。凌娘的居所曾是大队部和军需处的驻地,后山有一个岩洞仓库,供军需处人员收藏物资及躲避日军的搜捕;凌娘亦曾参与修建仓库。凌娘一家上下都很支持港九大队,长子刘己长经常协助游击队刺探敌情,其妻是妇女会会长,每当有游击队员进村,都会动员每家送一担草给队员煮饭、烧水。次子刘茂华则参加游击队,任税收员。
鲫鱼湖村村民李亚新(称「新姐」)对待游击队员亲如手足,被称为「游击队的好姐姐」。她的居所曾是大队民运干事刘志明的长驻地。她热心款待驻村游击队员,提供食宿、柴草并常协助运送物资。她对伤病员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她亲自上山采摘草药,熬药给病至休克的女队员倪珍美服用。抗战结束后,两名游击队员感念李亚新当年的恩情,曾重返鲫鱼湖村探望。
北潭涌村曾是港九大队西贡中队中队部驻地。村民李申娇对驻村的游击队员关怀备至。她经常放下农活,亲自上山采摘草药替伤员治病。当时粮食供应紧张,她宁愿自己吃杂粮,也将仅存的米粮给伤病员熬粥。她将自己酿造的黄酒给一位即将分娩的女游击队员服用,好让她补养身体,早日重返战斗岗位;家中鸡蛋连儿子也不许食用,特意留给产妇调理身体。她对游击队的关怀和爱心,得到游击队员的热情称赞:「不是亲人胜亲人」。
西贡桥嘴村村民袁容娇一家三口则时常冒生命危险支持游击队。袁容娇的丈夫早已病故,她独自一人带著儿子石观福和女儿石桂好,驾著小艇于西贡、坑口、滘西洲、北潭涌一带,为游击队送达情报资料和补给物资,并送队员外出执行任务。后来,她乾脆带著船和孩子,一起加入了部队。她送年仅13岁的长子石观福到海上队,勉励他像岳飞那样「精忠报国」。
1943年7、8月间,港九大队军需处的欧连(欧伟明)乘坐容娇母女的小船,从北潭涌出发到滘西检查税收工作。由于雾大未发现敌情,谁料船近滘西入口处,突然发现后面约60米处,一艘敌船驶来,已经无法躲避。容娇镇定地让欧连下到水里,掩蔽在船的另一边。敌船开过来未发现异常就开走了。
有一次,日军在海面大扫荡,海上队一个班在某处海岛上钻入岩洞掩蔽起来。敌人长久不退,乾粮都吃光了,只好以海草充饥。敌人一退,容娇母女的船就送粮食来了。
老战士梁雪英在《忆战友容娇的一家》诗歌中写道:「回忆战友容娇姐,全家革命将船献。子女带来当水兵,容娇班长领在先。带信护送同志们,连夜冲过封锁线。不论刮风和大雨,乘风破浪勇向前。」这是抗日战士与香港爱国爱港民众最真切的情感表达。
香港民众誓死保障游击队安全
日军为了消灭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频繁扫荡新界村落,并捉拿当地的乡民,严刑拷问,企图找到突破口。为掩护游击队,不少乡民坚毅无畏,不怕牺牲,即使遭受严刑折磨,也从不动摇,守口如瓶,最终被折磨至重伤甚至死亡。其中的杰出代表有乌蛟腾村村长李世藩、李源培和李宪新。
1942年9月25日,时维中秋节翌日,日军扫荡乌蛟腾村,将村民赶到晒谷场上,逼迫他们交出自卫武器及供出驻村游击队员的下落。村长李世藩抱著宁愿牺牲个人,也要保护村民和游击队的决心,坚定地说:「冇……我唔知……我唔知道我哋村里有枪支,我亦唔知道有咩叫做游击队,嗱大家咁多人喺晒呢度啦,你话边个游击队你讲啦。」(没有……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村里有枪支,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游击队,大家都在这里,你问问谁是游击队。)日军对他没有办法,对其灌水、殴打,还残酷地用军马将其拖在地上奔跑。最终,李世藩被活活折磨至死,壮烈牺牲。
港九大队经常在村内宣传:「我哋有气节、有骨气,唔做汉奸呀。抗日一定能够胜利。」(我有气节、有骨气,不做汉奸。抗日一定能够胜利。)这种思想深入人心。另一位村长李源培目睹李世藩甚么都没有说,又被日军拉出去没有回来,知道他凶多吉少,仍然大义凛然地对日军说:「冇。」(没有。)日军残暴地拷打李源培,将其左手打断。几个日军士兵用几十斤重的木梯和军马马蹄,在李源培灌满水胀鼓鼓的肚子上施压,又用熟烟将其背部烧得皮开肉绽,流血不止,休克过去。日军撤走,李源培被村民救治醒来后,马上动员女儿李玉森及其他村民参加游击队抗日。1943年春,日军再次包围乌蛟腾村,继任村长李宪新被逮捕,拘禁于大埔宪兵部,从此下落不明。
抗战时期,西贡黄毛应村是一条只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是港九大队成立的地方。当时全村共有青年14人,6人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村内还有民兵、青年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在日军的疯狂扫荡中,黄毛应村村民不顾自身安危,誓死保护游击队。1944年9月21日,日军扫荡黄毛应村,未能发现游击队员踪迹,于是将村民邓福、邓德安、邓戊奎、邓新奎、邓三秀及邓石水带到天主教堂玫瑰小堂严刑逼供。为保障游击队员的安全,即使遭受严刑拷问,他们始终坚贞不屈,守口如瓶。日军的酷刑令村民身心均留下无法磨灭的创伤。邓福遭日军火焚,脊骨严重受伤,治愈后仍常感到背痛和脚步不稳。邓德安遭日军毒打,施以火焚、「吊飞机」等酷刑,被严重烧伤,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年仅20岁。邓戊奎则遭日军虐打及施以「吊飞机」、火焚的酷刑,腿部被严重烧伤,经治疗三个月方才痊愈。日军在搜捕游击队方面一无所获,竟洗劫全村,将牲口财物掠夺一空,村民损失惨重。
1945年1月,元朗中队与民兵配合,在山下村展开铲除密探的行动。战斗期间不慎让密探逃脱,上百名宪兵随即到山下村扫荡,游击队撤到山上躲避,敌人穷追不舍,双方陷入激烈枪战。在此过程中,女民运区委陈瑞腿部不幸被敌人击中受伤,幸得山下村村民帮忙,得以及时藏匿起来。日军对山下村围村搜查,扬言不交出女游击队员即放火烧村。日军查无所获,于是将七名村民押到宪兵部严刑迫问。七名村民中,张金福年纪最小,日军想在他身上找到突破口。严刑拷打下,他只说一句话:「我是农民,只知耕田种菜,别的什么也不知道。」日军不肯相信,把他打晕过去,醒来又再打。折磨七八天后,张金福死在狱中,年仅20岁。山下村群众张耀枢等冒著生命危险,护送陈瑞通过敌人封锁线,到西贡的大队卫生所治疗。
抗战时期,西贡十四乡设有游击队的交通站和税站。1943年5月初,日军包围企岭下村,将全村村民集中起来,逼问游击队的下落并要求他们交出税站人员,村民沉默不语。日军于是将西径村李观妹拖出审问。即使遭受灌水、抽打等酷刑,他始终拒绝透露有关游击队的半点消息。日军将李观妹绑到树上,并用刀割下他的耳朵。面对直流的鲜血,李观妹却始终默不作声,最终被折磨至重伤昏迷。日军无计可施,只得灰溜溜撤走。日军一走,乡亲们立即上前解开绳索,将他抬回家救治。港九大队短枪队队长萧华奎闻讯,立即派人送来钱和药物,慰问这位拼死掩护游击队的乡亲。
1944年12月28日,日军派出150多人到大埔南华莆、坑下莆、塘上村等多条村落执行大规模扫荡。扫荡行动中,包括南华莆村村长郑保(又名郑子宏)在内的30名村民被日军拘捕,押回大埔宪兵部审问。拘押期间,郑保被施以水刑、电刑等各种酷刑,并被山田规一郎用砖头击伤腿部,双脚肿胀一直流血不止。尽管如此,他坚拒透露任何有关游击队的消息,最终被折磨至死,壮烈牺牲。他在囚室曾告诉其他村民:「不要承认是游击队员,否则全部都会被日军杀害,如果能救其他人,我一个人死去也没问题!」
宗教人士在保护游击队员安全中发挥特殊作用
大屿山宝莲寺住持筏可大师不但在港九佛界中有地位,在华南地区佛教界中也有影响力。筏可大师支持抗日,在筏可大师的影响下,当地和尚、尼姑都支持游击队,平时为游击队采药治病。1943年初夏,经陈亮明联系,了见尼姑收留了港九大队副大队长鲁风暂住庵堂养病。1944年5月,日军到地塘仔展开包围搜索。幸得了见尼姑帮忙,鲁风及时躲进秘密石洞,避过日军的搜查。了见尼姑随后请人帮忙带鲁风到宝莲寺请求住持筏可大师庇护。日军前往寺内搜查鲁风时,筏可大师安排鲁风伪装成僧人,随数百名僧尼和居士在佛殿内听其讲经。日军穿行于僧尼等听众间,逐排逐座检查。鲁风镇静如常,闭目合掌诵经,待讲经结束、听众鱼贯退场后,随即绕过方丈室往后山匿藏。此时,日军追赶到方丈室盘问筏可大师。为掩护鲁风,即使日军以刀相逼及毒打他,他却始终镇定自如,没有透露鲁风的半点行踪。
1943年5月,大屿山中队中队长刘春祥带领6名班排骨干,乘坐帆船准备到大屿山对岸的龙鼓滩一带开展工作。在沙洲、龙鼓洲一带海域突然遭遇两艘日军炮艇伏击。经过激烈的战斗,木船被击沉,刘春祥等指战员和船家梁克一家五口壮烈牺牲。梁克一家动用全家赖以维生的木船冒险支持部队抗战的行动,是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体现。2020年,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将刘春祥等12名龙鼓洲牺牲英烈,列入第三批185名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羣体名录。
香港民众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香港虽为沦陷区但一直能够坚持抗战的「深厚根源」。香港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以深厚的爱国爱港情怀和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坚决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去,举家抵抗、不惧牺牲,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送上对香港抗战力量最深炽的尊敬和纪念!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5年4-6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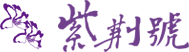





 今日热搜
今日热搜

 本周热搜
本周热搜

 本月热搜
本月热搜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