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荆论坛》专稿/转载请标明出处
作者:约瑟夫.格雷戈里.马奥尼 | 美国《中国政治学杂志》副主编、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译者:郑颖 |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现代性」这一概念不仅贯穿著中国历史的划分,亦在历任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思想中表现为不同的时代任务,其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逻辑和与政治合法性相关的叙事中占据了核心位置,最近被正式表述为「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和「现代性」在如今的中国可以被理解为「新中国」「民族复兴」等核心主题之一,通过理解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发展,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当今中国。
「现代中国」这一术语经常被中国和非中国学者用来描述某一特定时代的中国,包括当前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已将「现代化」作为其发展策略和全面治理的核心目标,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如今,很难低估「现代性」的各种表达方式在官方话语结构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实际上,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概念,「现代性」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逻辑和与政治合法性相关的叙事中占据了核心位置,最近被正式表述为「中国式现代化」。
作为历史分期的现代性
在西方,「现代」一词的拉丁词根的历史比许多人所理解的「现代」时期更为久远。在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研究中,西方的现代性在19世纪的巴黎达到了某种文化顶峰。但即便如此,现代性仍然必须被视为一种部分神话化的概念,它十分依赖于与过去的「激烈断裂」的观念,同时具备先锋性,常常自视为处于历史终结的边缘。哈维回顾道,巴黎的现代性在1848年达到了一个危机点——这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发表《共产党宣言》的年份,随之而来的是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兴亡。这些危机本身被认为是现代性的体现。换句话说,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哈维将现代性视为一个接连发生且经常愈演愈烈的危机时期。
这一观点值得注意,原因有二。首先,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主导中国现代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视角一致。其次,因为许多西方和中国学者将中国现代性的开端确定为19世纪中叶中国与西方艰难碰撞的时期,特别是两次鸦片战争。换句话说,中国几乎在欧洲列强自身进入现代的同时,也开始经历现代性危机。乔纳森.芬比(Jonathan Fenby)在《现代中国:一个大国的衰落与崛起,1850年至今》(Modern China: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 to the Present)以及埃德温.莫伊斯(Edwin Moise)在《现代中国》(Modern China)中都支持这种看法。
但是,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现代性的起点可以追溯到明末时期,中国在当时即将出现现代化发展,直到明朝灭亡,被清朝取代——这是中国与西方接触日益增多的时期。在《现代中国的崛起》(2000年)一书中,徐中约(Immanuel C.Y. Hsü)认同了这种观点,并指出其在说明清朝如何持续应对西方崛起方面的价值,以及为何这些努力最终尚显不足。
然而,徐中约曾恰当地指出,无论中国现代性是否倾向于从明末、清朝或更早的时期开始,中国现代性作为一种刻意发展的目标,实际上是在应对外来侵略时才真正开始,特别是清朝在1861至1895年间的追求现代化的努力,即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这场运动在1895年中日战争失败后宣告结束。可以说,中国在那场战争中的失败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当时大量的中国人开始倾向于结束封建王朝统治,开始接受进行民族革命的必要性。为此,有人将辛亥革命视为中国现代性的开端——这一革命导致了清帝的退位和中华民国的建立。
总的来说,西方叙事往往模糊地将中国现代性描述为一个推进中、间歇性的、尚未完成的项目,从鸦片战争开始,经历了若干关键时刻,这包括上述的各个事件,并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官方的历史和中国学者与西方的描述并无根本冲突,但在某些重要方面存在差异。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和西方一样,中国官方关于现代性的分期有两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是一般的历史方法,即前文所讨论的内容;第二种与文学和艺术运动相关。然而在中国,还有第三种方法,即官方的政治分期,这种分期方法也具有广泛的影响。区分这三种方法有助于避免某些混淆。
中国政治中的「现代性」
在政治分期中,中国的近代和现代之间出现了一个中间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时期的加入至少具有三个目的。首先,是为了强调「五四运动」的重要性,其标志著一场重要的文化和政治觉醒,这场觉醒开启了许多人认为对现代民族国家至关重要的新的大众政治。「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中国人民对《凡尔赛条约》的愤怒。该条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将德国占领的中国山东转交给日本,而未归还中国。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于1921年在上海成立,并得到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实际上,「五四运动」紧随1917年列宁的「十月革命」之后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也开始在中国迅速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中心位于北京大学,始于1920年并以李大钊为核心人物,包括毛泽东等人。有鉴于此,近代时期中出现这一特殊分期的第二个原因也就变得清晰了起来:一方面,「五四运动」被官方视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摇篮;另一方面,它也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先锋地位(因其列宁主义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方式),标志著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及其开始制定引领现代时期的新策略和新战术。
第三个将这一分期作为特殊时期的原因,是为了简明地表达一个原本混乱的过渡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包括了抗日战争,更广泛来说还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内战,以及各种形式的统一战线。同时,这一时期也囊括了中国共产党自身战略和战术的重大变化。
在1919年之前,在外国和中国国内的资本主义企业确实存在的同时,也存在著一个可以被描述为资产阶级和买办阶层的群体。这些元素在1919年之前的中华民国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甚至在清朝时就已存在。然而很难以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式断言中国经历了一个以资产阶级统治为主导的独立资本主义阶段。因此,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概念作为理论解决方案发挥了作用,适应了当时中国复杂的政治形势。这一概念有效地压缩了历史分期,使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交替重叠,随后逐步让位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尽管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7年)在毛泽东的文章中并未被直接引用,但其理论显然对毛泽东的观点有深刻影响。该著作阐述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如何导致不同的发展路径:核心国家遵循马克思熟悉的发展道路,而边缘国家则由于其自身独特的国情以及来自核心国家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被迫探索不同的发展道路。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扰乱使得殖民地国家甚至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边缘国家无法按照马克思所设想的路径发展。
综上所述,鉴于上述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了一座有用的桥梁,使得中国能够从近代向现代过渡,尤其是在1949年中国内战以共产党战胜国民党而告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最独特的地方在于毛泽东提出的工农联盟,这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式马克思主义,后者认为农民是落后阶级,无法充当先锋队。这一步骤对快速将中国群众动员到国家建设的政治项目中至关重要,也成为中国向现代技术社会转型的关键一步。
中国向现代国家和日益增长的技术社会的转型随即加速。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乎是立即参与了朝鲜战争。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苏联的支持下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但由于多种原因,包括自1921年成立以来时存在的复杂关系,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已经开始对莫斯科产生不信任,担心国家发展速度不够快,难以巩固国家主权,更无法跟上新的外国技术进步,而这些进步又可能对中国构成新的威胁。这一切导致了政策制定越来越激进,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三个世界」理论是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这一理论分析了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并在冷战时期指导了中国的外交政策。该理论不仅打破了外交和经济孤立的战略空间,还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邓小平于1975年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时提到「三个世界」理论。尽管该演讲未被收录在《邓小平选集》中,但他在该文集中其他部分四次提到「三个世界」理论,认为这是中国对抗霸权主义的战略思想基石,并将其与推动「四个现代化」明确联系在一起。
「四个现代化」(即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早在1963年由周恩来提出,并在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重申。邓小平同样重视「四个现代化」,他在1978年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首次明确提出这一目标。这表明,弥合技术差距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不论是在文革之前、文革期间还是之后,都是改革开放的核心目标。
虽然很难确切评估「三个世界」理论在多大程度上继续指导著中国的战略思维,但其核心价值观似乎与中国随后的发展高度一致。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该理论为中国外交和现代化路径提供了核心逻辑,并直接将其与「一带一路」倡议和「共赢」目标联系起来。这些学者认为,中国不仅成功地以自己的方式在反霸权的情况下实现崛起,还准备帮助其他国家也以类似方式崛起,推动多极化和多边世界体系的形成。
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不仅体现于中国在包括大幅缩小的技术差距方面的崛起上,也体现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这一观点在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变化看法中有所体现,也清晰地表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这与中国逐步从「规范接受者」转向「规范制定者」的趋势相一致,即在全球市场中寻求更强的地位(即便不完全是主导地位),尤其是在先进技术方面,并努力在竞争激烈的民族国家体系中强化自身的主权和地位。随著时间的推移,这一体系不仅没有放松,反而得到了加强。
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的现代化任务已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对自己的道路充满信心(即「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部分体现在2021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上,这是与「四个现代化」推进直接相关的一个关键发展节点。这一成就为中国接下来一个重大目标的规划提供了基础:到2050年将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中包括2035年的中期目标,并继续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前进。这一模式与其他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隶制、种族灭绝、战争等手段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形成鲜明对比。
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展与合法性中意识形态符号的「现代」和「现代化」
沿著这种思路来看,当今中国的「现代」和「现代性」可以被理解为「新中国」「民族复兴」「作为中国人」的意义,以及未来「作为中国人」将意味著什么的核心主题之一——根据「中国梦」以及习近平提出的到2050年实现全面现代化的目标,这意味著变得更为现代化。
进一步来看,可以观察到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样一个观点上:中国共产党为中国连续的现代性危机(外国侵略、重新确立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通过解决中国与强势外国势力之间出现的技术差距来强化主权,以及引领国家迈向更高的发展水平)创新了解决方案。在这里我们可以回顾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把共产党描述为「现代的君主」会更有益于理解。葛兰西将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在《君主论》中关于有效的政治权力和主权的关键见解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的先锋队理论相结合。葛兰西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共产党的力量源于推进现代化,并且这种物质形式的进步塑造了大众的意识,在意识形态上产生了共鸣,从而确认了进步的存在并赋予了政治上的合法性。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描述中国共产党。
作为「技术社会」的现代性
在前现代时期,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技术社会,以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为代表,而这一成就通过李约瑟(Joseph Needham)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得到了更具体的证实。然而,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孟德卫(D.E. Mungello)所描述的那样,16世纪欧洲人造访明朝时,对中国的技术和文化进步印象深刻,甚至有些人将中国人视为「白种人」。但到了清朝衰落、欧洲崛起时,东方主义则将中国人描绘为肤色偏黄且在科学上落后。
20世纪以来,学者们开始探讨所谓的「李约瑟之谜」:为什么中国在许多文化和科学成就上领先至少一个世纪,却未能在启蒙运动时期和工业革命期间像欧洲那样发展起来?
众多学者提出了各种理论来解释这一问题,包括文化、制度、地理和经济等差异,以及诸如小冰期带来的影响等其他可能的解释——竺可桢的开创性研究首次在近一个世纪前探讨了这一影响。然而,所有这些解释都未能区分「技术社会」和「技术性社会」的概念。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自1978年起,中国迅速从一个先进的技术社会转变为先进的技术性社会。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日益占据主导地位,而这种主导地位对国家独立和安全至关重要,同时也是推动全球技术文化的关键动力,这往往与传统价值观存在冲突。这种转型不仅体现在计算机、人工智能、绿色能源和太空探索等尖端技术的发展上,也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人所描述的那样,现代的自我意识本身是工业理性化的产物和表现。
这一转型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基于发展的合法性,并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先进的技术性社会。然而,这也引发了中国内部各种形式的「技术崇拜」,对中国社会及其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这一趋势在全球层面也产生了相似的影响,有些人热情拥抱中国的技术进步,而另一些人则推动「中国技术恐惧症」。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5年1-3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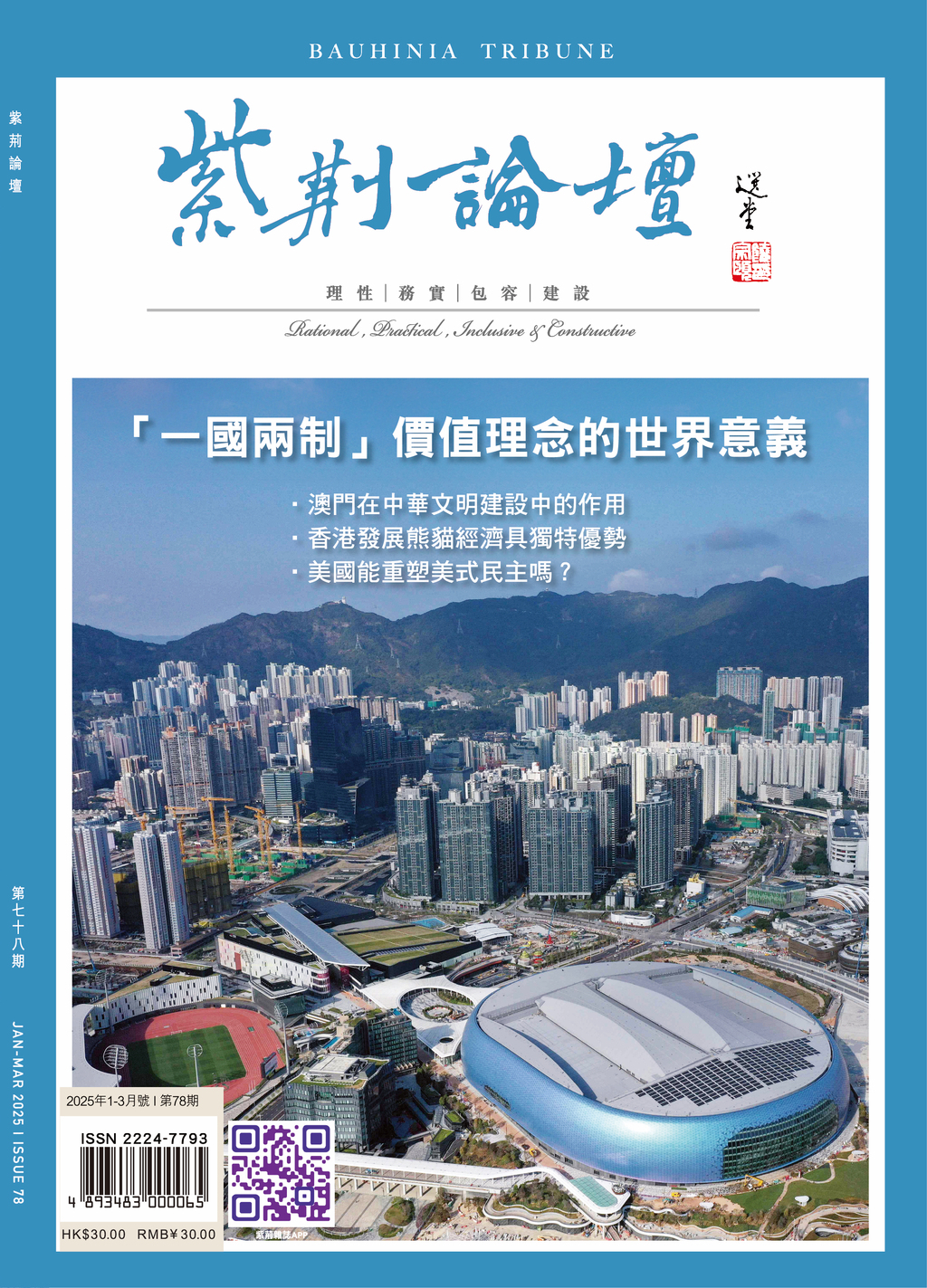







 今日热搜
今日热搜

 本周热搜
本周热搜

 本月热搜
本月热搜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