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荆论坛》专稿/转载请标明出处
叶文祺 | 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
梁跃昊 | 团结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
赵 恒 | 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员
2024年11月8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在深圳召开2024年香港工商界人士座谈会,讨论香港经济发展。会上夏宝龙主任重点提到,香港航运物流业非常重要,港口地位不应改变,「香港如果没有港口就不是香港」,并提出要建设好「陆丶海丶空三个『港』」。在外部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下,香港航运业不能仅靠「吃老本」,必须锐意改革谋求出路。
港口航运业「求变」时机已至
根据香港海运港口局公布的统计数据,2023年香港港口的货柜吞吐量为1,440万标准箱(TEU)。在此之前,香港货柜码头曾在2013年创下2,235万标准箱吞吐量的记录,然而其后经历了连年下跌,目前吞吐量只及当年高峰的六成。在2024年首9个月内,吞吐量则为1,017万标准箱,较2023年同期下跌近6%。尽管内地的经济活动及出口有所改善,然而仍未足以扭转香港港口吞吐量的下跌趋势。
总体而言,港口及航运业务除受制于周期性及结构性因素之外,也受到香港与内地经济增幅放缓、内部需求疲弱、中美贸易争拗等影响,这些均反映物流业处于周期低谷。随著时间推移,企业及消费者终会逐步恢复投资及消费意欲,届时周期性的影响或有所减退。相比之下,结构性的转变则较难以逆转,高昂的地租和劳动成本、欠缺支持物流业发展的基建及配套设施,以及区内其他港口的效率和竞争力大幅上升,均令香港港口的竞争力有减退的迹象。在此背景之下,「求变」已经是刻不容缓。

笔者认为,若要扭转劣势,香港特区政府及香港航运业界应思考香港港口的定位,并从三方面重塑竞争力:认清未来发展趋势,发展行业所需的基建及专注于更多具竞争力的范畴,以差异化竞争稳住传统港口及航运业的业务;拓展更多高增值服务范畴,实现业务重心转型;强化香港海运港口发展局的角色,统一管理港口相关政务,加强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协作,通过「港口同盟」实现协同发展。
第一变:价格取胜非可行之计,差异化竞争加强优势
航运及港口业务,可谓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根基」。港口业务不止为船公司和港口营运商带来商业活动,亦会为中流作业、仓储、陆运、贸易、金融业等行业创造商业机会,为数以万计的本地雇员提供就业岗位。无可否认,受到香港的先天条件所限,业界往往须面对较高的租金及劳动成本,因此以价格取胜并非可行之计。笔者认为,特区政府应专注于香港具有优势的范畴,如绿色港口及大宗商品,并就未来行业趋势作前瞻布局,以适当变革加强港口的独特竞争优势。
近年来,发展绿色港口及绿色航运已成为业界的最重要趋势之一。作为联合国负责制定全球航运标准的专门机构,国际海事组织(IMO)在2023年的减排战略中提出,要尽快使国际航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峰值,并在2050年前后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随著绿色大潮涌来,港口也要顺应需求变化,提供绿色能源以支持航运业实现绿色转型。全球船用燃料供需关系面临重新「洗牌」的时刻,为满足不同地区的环保要求,船公司在规划未来航线分布时,将优先考虑有充足绿色燃料补给的港口。
笔者喜见特区政府在近日发布《绿色船用燃料加注行动纲领》(以下简称「《纲领》」),勾画出香港未来推进船用绿色燃料的策略。然而,在芸芸众多的替代燃料之中,笔者认为特区政府应在改善生物柴油的生产及供应上有更多著墨,以满足未来不断增加的需求。不同于其他的绿色燃料,生物柴油在能量密度上与传统船用柴油较为接近,船舶无需作任何改装,便能转用生物柴油。而且,生物柴油具有较低含硫量,燃烧过程中将产生较少悬浮微粒,加上在燃料的生命周期内较传统柴油产生较低的碳排放,一直被视为代替传统燃料的最快捷可行方案,其需求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
有见于此,特区政府在《纲领》中提到将在2024年内开始鼓励业界使用生物柴油。然而笔者注意到,由于香港废弃食品油的回收量偏低,加上本地生物柴油产能有限,或将不利于推广生物柴油的使用。目前香港的食品油回收量只有约三万公吨,只能供两家生物柴油厂加工;而每年的本地船用柴油加注需求量则高达500万公吨。假若全部船舶转用由5%生物柴油混合95%柴油而成的B5柴油,那么单单是船用生物柴油的需求量,便将达到25万公吨,远超本地生产能力。可惜的是,由于缺乏推广,目前只有少数本地企业采用生物柴油;在本地需求不足的环境下,本地生产的生物柴油只能远销海外,不利于香港发展出完整的绿色燃料产业链,小批量的生产模式亦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笔者建议特区政府大力推行废弃食品油回收机制,巩固生物柴油的原材料供应,同时以具吸引力的税务优惠及政策措施鼓励企业转用本地生产的生物柴油,以达到创造需求和支持本地工业发展的目标,继而助力港口的绿色转型。
另一方面,特区政府可透过建立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强化香港的航运中心地位。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具有资本流通快速和金融体系发展成熟等优势,除了能提供大宗商品的现货、期货及衍生品交易平台,亦能提供货物仓储、运输、交割等服务,为航运、航空及物流业创造新商机。然而,由于香港各项大宗商品的业务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面对不少挑战,包括缺乏提供仓储交割的专业机构、实物交收体系未算成熟、仓储空间较为有限、各类商品期货的交易较为稀疏等,这些都不利于吸引企业及投资者透过香港进行交易。笔者认为,特区政府除了预留相应的土地供应用于发展基建之外,亦应加紧推动全产业链的招商引资工作,并为大宗商品市场引入更多大宗交易机构,收窄买卖差价,提高市场流动性,以构建成熟的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成熟的大宗商品交易圈除了带来更多货流外,亦能帮助香港发展成为绿色燃料交易中心,与绿色燃料加注业务相得益彰。概括而言,在传统航运领域,香港需不断变革,致力发掘新机遇,巩固航运中心角色。
第二变:善用高增值服务优势,构建完善航运产业链
除了巩固传统港口物流,特区政府亦应致力于开拓航运高增值服务,构建完善的航运产业链,以达到「回应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的愿景。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船东国,坐拥2.94亿吨吞吐量的船队,负责全球40%的海上货物运输。然而,由于伦敦一直是海事仲裁的首选地,不少中方船企在遇上法律争议时,仍需诉诸于伦敦。建基于香港优良的法律体系,香港应在海事仲裁上发挥更大作用。2020年,香港获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BIMCO)列为四个指定仲裁地之一,与伦敦、纽约和新加坡看齐。另外,2019年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容许以香港作为仲裁地,由指定仲裁机构管理的仲裁程序当事人向内地法院申请保全措施,处置当事人在内地的财产、证据及行为。该安排大大提高了香港仲裁服务在内地的适用性,这是新加坡、伦敦等地所不具备的。基于以上优势,香港可发展成为海事仲裁中心,为中外航运企业提供争议解决服务及法律支援。
值得鼓舞的是,早前内地落实「港资港法」,容许于深圳前海合作区注册的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选择香港法为合同适用法律,并实施「港资港仲裁」,即容许在深圳自由贸易试验区注册的港资企业之间,将商事争议提交香港仲裁,这些做法进一步向香港开放了内地的仲裁需求。笔者建议,特区政府继续与内地探讨,逐步将有关安排推广至内地的非外资企业,让内地的企业和个人也能够享受香港便捷、高效和保密的仲裁服务。
另外,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应在国际航运金融及保险领域发挥更大作用。目前内地航企仍十分依赖由西方金融机构所提供的资金、产品及服务,尚未能达到自给自足。特区政府亦自2020年起,推出不同税务优惠,包括为船舶租赁提供免税优惠,为船舶管理人、船舶代理及船舶经纪提供半税优惠,吸引更多海运企业落户香港。2023年发布的《海运及港口发展策略行动纲领》重点提到提升船舶融资、海事保险、海事仲裁和船舶管理等业务,让香港成为全球领先的高端航运服务市场,助力全球海运和港口业务向零碳排放转型。
即便上述措施对航运金融及保险有积极作用,特区政府仍需著手解决一系列障碍。目前香港的不少主要贸易伙伴,包括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澳大利亚、巴西,尚未与香港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的协定,令不少行内企业受到双重课税的影响。特区政府应与更多国家及地区签订有关协定,方便业界进一步享受香港的低税制便利。
在船舶融资上,香港银行承造船舶的按揭年期往往短于10年,远远低于船舶的平均寿命,不利于船东的现金流状况。笔者认为特区政府可提供信贷保险及担保,改善贷款的信贷评级,以协助船东获取更长年期和利率相宜的信贷。特区政府亦应继续促进资金的互联互通,同时整合在外地的业务推广资源,将航运服务产业链作总体推广及宣传。另外,在保险业务上,特区政府需继续吸引更多保险及再保险公司提供丰富的风险管理工具及方案,优化本地精算及风险管理人才库,以及鼓励行业提供更多创新的产品及服务。在传统法律和金融优势之上,香港需「识变、应变、求变」,在国家航运业发展中扮演更大角色。
第三变:打破狭隘「中环视角」,放眼大湾区发展机遇
长久以来,香港发展限于狭窄的「中环视角」,过于重视自身而忽略与周边城市的合作空间。随著大湾区融合不断深化,香港应打破狭隘的思维模式,以「湾区视角」放眼整个大湾区的发展与机遇。建议特区政府透过成立港口局,强化统筹角色,推进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合作。
纵观全球各大港口,均设有一个单一港口统筹机构管理港口发展。例如,迪拜的杰贝.阿里港及杰贝.阿里自贸区,均由国营公司开发土地、营运及管理,同时担当区内的政府角色;新加坡港则由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统筹。而香港的港口设施大多由私人企业拥有和营运,港口相关事务则分属运输及物流局和海事处管辖,没有单一政策局统筹。一直以来,香港业界均有声音呼吁政府将港口事务分拆,成立一个如同香港机场管理局般具备法定地位的机构,专注港口事务。参考机场管理局的制度,设想中的港口局,能独立统筹港口事务,制定行业发展策略和政策,进行市场推广,以及为行业提供所需的基建、物业和土地。
在2024年《施政报告》中,特区政府提出改革现时的「香港海运港口局」,升格为「香港海运港口发展局」。笔者喜见政府对港口及物流业展现出更大的关注,但同时认为政府有必要加强该局在咨询业界以外的角色,包括掌握发展港口业务所需的土地供应,具备招商引资、制定政策、提供支持措施等功能,以支持行业的长远发展。长远而言,特区政府可以机场管理局为蓝本,建立起一个具有统筹、领导和执行能力的专属部门,并将港口建设、营运及设施管理等功能整合在港口局的管辖之下,全力支持香港巩固其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地位的工作。
此外,笔者亦建议政府将多项港口相关基建,包括货柜码头的土地、启德邮轮码头,在相关的土地契约及专营权届满后注入港口局,通过统一规划及管理,实现港口及航运基建之间的协同发展。目前上述各项基建,其拥有权及经营权散落于多个私人财团和政府部门之间,不利于在港务上形成协同效应,提搞日程管理和营运的效率。整合后的港口局,能统一运营各项港口资产,并就整体港口策略作总体安排,以提前布局应对未来的航运格局。
大湾区拥有广州、深圳、香港三个世界级港口,产业群集聚程度位居世界前列。在外部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大湾区内的三大港口更应透过合作和优势互补,实现协同发展。近年航企并购活动不断深化,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联盟,取得了更大的议价权。因此,世界各国不少港口已经形成了不同规模、不同程度的港口同盟,例如美国塔科玛 —西雅图港组成西北海港联盟,以及中国浙江省的宁波—舟山港等。香港国际货柜码头、香港现代货箱、中远—国际货柜码头及亚洲货柜码头已于2019年组成香港海港联盟。在此基础之上,大湾区城市应充分参考世界各地的港口同盟建设经验,探索协同发展港口同盟的可能性,并展开更深入的合作,以巩固港口业务的定价权。笔者建议设想中的香港港口局与大湾区内其他港口形成「港口同盟」,在定价、招商、航线发展和服务上建立合作机制,构建出分工明确的港口群。
总而言之,随著全球航运业的变化,香港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方向,以保持竞争力。在激烈的外部竞争下,建设「陆、海、空三个『港』」并非易事,只有通过创新变革,才能突破现有瓶颈,实现长久繁荣的愿景。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4年10-12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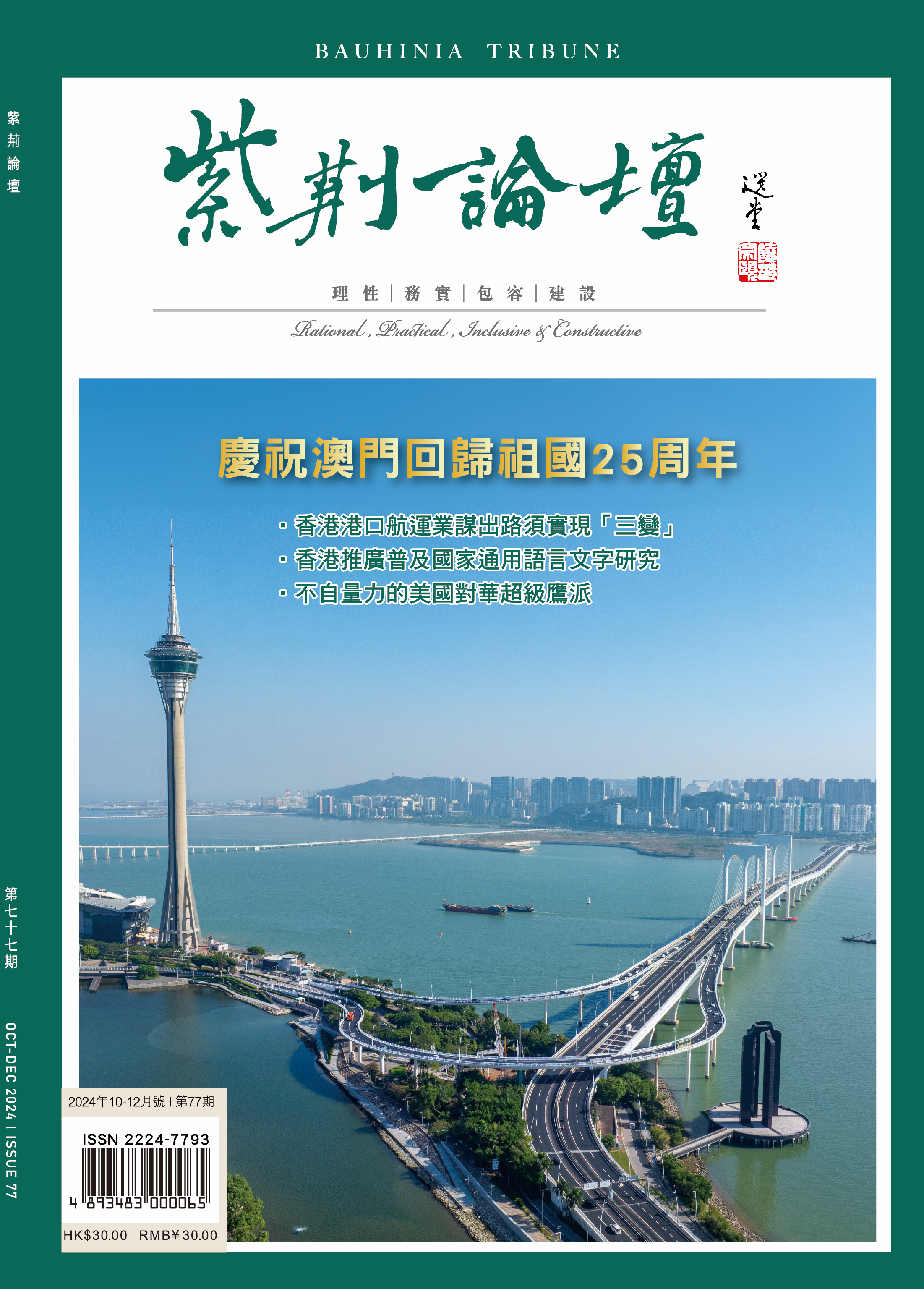







 今日热搜
今日热搜

 本周热搜
本周热搜

 本月热搜
本月热搜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