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承平
发生在2020年由香港反对派发起的“立法会35+初选”案,47人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2023年2月6日正式开审;2024年5月30日裁决。14名不认罪被告经审讯后被裁定“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刘伟聪及李予信被裁定罪名不成立。特区政府律政司代表当天就两名脱罪被告提上诉。
案件中辩方针对国安法第22条“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文提出争议,称所指的“非法手段”应限于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非法手段。然而,法庭颁下的判案书指出,第22条“显然是为防范及制止背后的祸害”;判案书又引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20年5月22日所做的说明解释,指出“鼓吹‘港独’和‘自决’、侮辱国旗国徽、煽动公众仇恨,以及瘫痪政府管治和立法会运作等非暴力行为,均可令国家安全在香港受到破坏”。故此,“非法手段”不限武力,涵盖“任何”非法手段。
“非法手段”不限武力
不明就里的人们可能会问:“为何仅仅是一场为立法会选举举行的模拟与预演却成了颠覆国家政权?”。让我们通过对该活动的真实意图,及其所想要达到的最终目的的揭露,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香港反对派初选案,为何不是模拟选举那么简单?关键是行动的谋划者、策动者的最终目的是透过预选,建立协调反对派内部的参选人、候选人的机制,在全港范围内进行配票,从而令反对派在该届立法会选举中得票最大化,达到占据立法会席位35席以上、即占据第六届立法会议席超过一半的目的。
有了超过一半议席的结果,若在立法会的重大审议议题上统一立场与行动,反对派就可轻易否决特区政府所提出的任何议案。如一年一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否决政府的财政预算,正如美国国会否决白宫的联邦财政赤字上限一样,将令政府关门、停摆。一旦特区政府预算遭否决,政府在新一年的任何开支都将被冻结,不仅涉及到政府部门的运作,还牵连到政府主导的建设项目、全社会的民生、福利的每一笔开支。该局面一旦出现,首先是当届的特区政府的执政合法性遭到市民乃至境外势力的质疑,行政长官及其团队立即面临下台的命运;否则,反对派在一些反动媒体的鼓动下,群众上街游行、示威将无日无之。
法庭延引此案的始作俑者戴耀廷、以及被告之一的控方证人区诺轩,在7月份的记者会,提到否决预算案、解散立法会等目标;以及在初选后的记者会和网络上的帖文中,戴耀廷重申参选人达成协议、承诺运用权力否决财政预算案。
“宪政危机”:反对派的目的
若果如此,香港就面临重大的“宪政危机”——被告之一控方证人区诺轩在陈述案发经过时,亲口道出此案的动机是导致“宪制危机”。那时,反对势力于2019年黑暴期间提出的所谓“五大诉求”( 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撤回“暴动”定性、撤回控罪、追究警队滥权、实现“双普选”)将成为香港必须面对与兑现的政治现实。在此种局势下,中央规划的香港政治改革循序渐进的路线图,将面临被迫直接过渡到一人一票普选特首、70名立法会议员全部直选的选择。不然的话,反对派将纠结外国势力煽动市民展开“罢工、罢市、罢课”等“三罢”运动;并以此作为筹码,要挟特区政府及中央政府。2019年夏天以来尚未平息的“港版颜色革命”将再被升级,情形将更加恶劣。
因此,反对派所谓的“立法会初选”,本质上是继2019年11月24日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之后的另一场夺取立法机构控制权的“夺权”活动。第6届香港区议会的选举要选出香港十八区区议会共452个民选议席,连同27个当然议员,合共479个议席。是次选举在黑暴运动尚未结束,全港社会仍处于所谓“五大诉求”的气氛之下,反对派阵营夺取全港86%的直选议席(389席);而建制派仅仅获得59席。反对派就是凭藉占据香港各区的议会平台,作为反中乱港的舞台,与特区政府及其各司局署的工作唱对台戏;而原本区议会的政策咨询、服务基层的功能被完全抛掷脑后。
该案的首被告戴耀廷在《苹果日报》发表的文章,标题即声称:“立会夺半 走向真普选重要一步”,就是再确凿不过的证据了。法庭也据此指出,“清楚看到”在2020年3和4月时,“35+”计划的“终极目的和用意已非常清晰”,就是“利用该谋划破坏、摧毁或推翻现行的政治制度,以及香港特区根据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方针所建立的体制”。
西方的“叫嚣”更像是“悲鸣”
香港高等法院依法判决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部分涉案人员之后,美英加拿大等国的政客及机构,“例牌式”地再次诋毁香港法治、民主、自由,甚至叫嚣制裁办理案件的法官和检察官。这,与其说是关注香港现状与前途的声音,不如说是西方为过去未能成功透过代理人达成“反中乱港”的目的,及今后更加难以通过“以港制华”而发出的阵阵悲鸣!
(作者系香港资深媒体人,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今日热搜
今日热搜

 本周热搜
本周热搜

 本月热搜
本月热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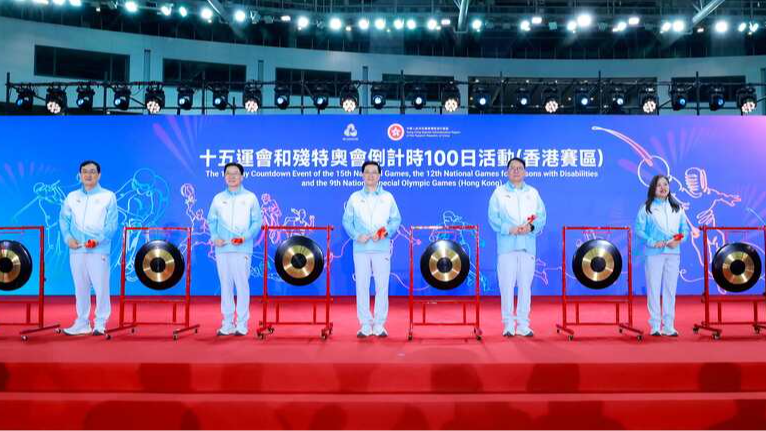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