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梦瑶
当东极岛的海浪第N次拍打著岸边的礁石,当香港维多利亚港的海浪第N次遥遥与之共鸣,一部名为《里斯本丸沉没》的电影,将深海之下沉睡的往事轻轻托起。这不是一场战争的复刻和解读,这是无数被命运揉碎的家庭,在时光里拼凑出的人性拼图。导演方励带著他的地球物理学专业知识和勘探仪器,以及一颗柔软善良的心,用八年时间完成了一场跨越世纪的打捞——打捞沉船,打捞记忆,更打捞那些在战争硝烟中从未熄灭的人性与温情。
这是“七七事变”八十八周年的前一天,南方影业在香港铜锣湾影艺戏院举办了隆重而简单的电影首映礼,我再次观看了《里斯本丸沉没》,并采访了导演方励。
座标之外:当科学家遇见未被标注的苦难
30°13'44.42 "N,122°45'31.14 "E。这组冰冷的数字是方励导演的执念。作为地球物理学家,他习惯了用精密仪器解读这个世界。但2014年那个偶然的午后,一组被历史遗忘的座标,将他引向了一处已被记录但又似乎是完全未知的勘探方向。“大家都没找到,我把它找到了。”方励说这话时,眼里没有征服的骄傲,反倒像个孩子捧著心心念念发掘到的贝壳,惊喜又珍贵。1942年,满载1816名英军战俘的里斯本丸在舟山海域被鱼雷击沉,日军的封锁令让这段历史在硝烟中褪色,只剩东极岛老人们口耳相传但逐渐模糊的记忆。
当方励的仪器第一次潜入30米深的海底,探照灯照亮的不仅是锈蚀和长满寄生生物的船板,更是八百多个年轻生命骤然凝固的瞬间。他的眼神仿佛透过浑浊的海水和清晰的时间轴,看到了过去:“我撤离海面的那一天,突然意识到脚下三十米的地方有八百多个生命被遗忘了。”那些被日军记录错误的座标,像一道数学题的错误答案——“日本的记录是错的,座标是错的,座标错的但它不是故意的,当年的技术是用航海的天象、用星座比对,所以这个误差太大了。”而他的专业知识,在多年之后的多年之前,成了打开时光密室的钥匙——不是为了证明技术的精准,而是为了帮那些在时光中沉默了许多许多年的人们,回答那些从未有机会被问出的问题:我的亲人在哪里?他们最后的时刻是怎样的?
方励导演至今记得撤离海面时那种深深的触动,“我第一次找到这个沉船完全是出于探索的好奇心,大家都说找不到这艘沉船,我就不相信了。所以,当我找到它的时候,我离开海面。然后我想到,光是听说有八百多个人在这,并不知道他们的故事,所以才开始寻找,调查这里面的人物。”也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情感,推动了他要完成这部电影,要记录这些故事。而Tony Banham博士宿命般走进了方励这部电影的制作。Tony Banham是英国历史学者,担任《里斯本丸沉没》的历史顾问,基于他25年的研究成果,其著作《里斯本丸沉没:英国被遗忘的战时悲剧》构成影片的史料基础,为影片提供许多关键资讯。看著两人在访问中不时对视一笑,就像看见子期伯牙的知音之谊。
当被问及为何总能敏锐捕捉到这些需要被铭记的瞬间,方励用具有审视感的第二人称来讲述自己的想法:“因为你从小经历了这个大的时代,你看到了很多苦难民生,看到大家的这个遭遇,所以你天生的就会产生怜悯之心,因为你是人。人是很善良的,所以你对穷苦的、遭遇了灾难的家庭,本能的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怜悯的同情心。”方励顿了顿,再次强调并续说:“这就是人的本能。就是所以你看金鸡奖我上台领奖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感谢中国给了我一颗怜悯的心。这算是我的一个‘诀窍’(This is my trick)吧。”
《里斯本丸沉没》在2024年底举办的第37届金鸡奖,获得了最佳纪录/科教片奖,是给方励导演和团队多年努力的重要肯定,更是对方励导演这种本能的善意的嘉奖。当一艘船沉没在海底,当科学家遇见未被标注的苦难,这就是答案。
大银幕上的家谱:两千个家庭的沉默与呐喊
在英国、美国、加拿大的某栋老房子里,当方励和团队扛著摄像机敲开这一扇扇门,老人们颤颤巍巍地摸著泛黄的照片和皱巴巴的信件,指认著里面穿著军装的年轻人,说起那些年幼时见过或者从未见过的亲人。这些老人伤心又感激:八十年来,第一次有人问我是否想说说他。这样的场景,应该在380多个家庭中重复了380次。
当我问起方励导演,怎么想到要做这部电影时,他说:“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想过做什么,只是因为听说这些老人都要没了,所以要去跟时间赛跑,去‘抢’人证。”大概是方励导演跟时间拼命抢人的倔强劲头感动了上天,他从三位在世的老人,逐渐发掘了更多的故事。“我第一次去英国群访的时候才发现有这么多故事可以说。这是我没想到的,所以我才决定去打广告。结果我这一打广告,找到380个家庭,还找到还在世的老兵!”最初只想抢救老兵记忆的方励,却在世界的不同角落,意外闯进了一座座被遗忘的情感博物馆。
“我不是来提问的,我是来听您说的。”他总对开门的人说这句话,像个虔诚的倾听者,捧著摄像机等待那些积压了半生的泪水与思念。方励导演说:“其实有很多人问过我,你有没有担心太突兀,有没有担心去触动人家的伤痛。我说,你们刚好讲反了,因为他们被这个世界遗忘了八十年没有人关心过。结果一帮中国人扛著机器就来敲他们的门,告诉他们,我替你们找到了你们爸爸失踪的地方。他们很惊讶,然后我再告诉他们,我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你们,你们想告诉世界什么,你们想说什么话,我替你记录。”方励导演补充道:“我是一个倾听者,就像一个树洞,然后我是个记录者。我告诉他们,我没有臺本,没有采访提纲,没有任何目的,就是来替你们传播给世界。因为你们的家庭受了这么多委屈,受了这么多伤痛,我有能力的时候,我想替你们转达给世界。”
从最初想做纪录片到最后以电影呈现,这种转变,在他看来不是形式的妥协,而是情感的必然选择:小萤幕是讲述,大萤幕是共情。“电影它更有更大的冲击力和时效性,也让更多人有机会看到。而且电影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大萤幕营造出的沉浸式,对于细节的品味、对于情感的浓度,对于营造情绪和氛围都是很丰富的,这是电影的魅力和能量。”
当被问及为何执著于将这些故事搬上银幕,方励的答案朴素而坚定:“情感,人的情感!人性的情感是这个电影的最核心的价值。因为对这些人,对这些家庭的情感,让我放不下来。”
跟方励导演对谈,会在他侃侃而谈的时候,感受到他身上的慈悲,慈悲的人会心怀众生。方励说:“我一辈子没有遇到这样一件事,是面对两千零七十一个家庭和他们的故事。我想要为这两千零七十一个家庭,把他们的先辈的遭遇记录下来。这两百五十五个东极岛救人村民的义举,一千八百一十六个盟军战士的家庭,在被所有人遗忘的时候,我有机会把他们记录下来,传播给全世界,我非常幸运,自己有这么个机遇,能为历史,能为世界,能为这么多家庭做一件事情,我是很有幸的。”付出了八年时间,投资了八千万,耗费的人力物力难计其数,大家都觉得方励亏了的时候,他说了好几次,自己是幸运的。
这些历史烟云里四散八方的碎片,最终被他细心用心地聚拢在一起,那些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在大银幕上重聚。当盟军战士的后代戴著老花镜读著寄回的家书,当光影将东极岛渔民划著小舢板冲向沉船的画面放大,观众看见的不再是历史事件,而是亲情与温暖。战争会改变生命的座标,却改不了思念的方向。
历史的接力棒:从东极岛到维多利亚港
香港首映会定在7月6日,“七七事变”纪念日的前一天。这个日期是特意选定的,像一个温柔的提醒:苦难需要铭记,但铭记的目的,是让维护和平的信念代代相传。“就像接力赛跑,Tony Banham博士传了第一棒,我传第二棒,你们传第三棒。方励导演在首映会后与观众对谈时说,满怀期许。
采访中,方励不时看向身旁Tony Banham博士,两人眼里是知己间的默契。Tony Banham博士考证出1816名战俘的姓名与军号——“1816个英军战俘,每一个人的军号,每一个人的部队都得准确”,方励转向Tony Banham博士,笑著补充,“I mentioned that every POW you verified. Everyone!”Tony Banham博士温和地笑笑,带著学者的儒雅和睿智。
方励则带著这些名字潜入人海,去打捞、去拼凑出他们的故事。这种传播的意念带著惊人的力量。2018年,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位老奶奶,通过报纸得知方励的拍摄,让孙子发来三封邮件:“她爸爸就在里斯本丸那里没能出来,她特别想倾诉。”方励当即带著团队飞越太平洋,“听她讲对她爸爸的怀念”。后来方励导演邀请了当年的盟军后代,在东极岛为他们的亲人举办安息仪式。方励特意替这位96岁高龄无法亲临的老人献了一个花环,“就是帮老人家还她的心愿”。
历史不是博物馆里的文物,是活著的记忆。这种记忆的传承,在东极岛渔民的讲述中尤为动人。他们的祖辈当年冒著生命危险救人,却从未将其视为功绩。“我们去访谈,采访他们的事,没有人觉得自己有多骄傲或者辉煌的。都是说,对呀,我们的先辈看到这么多的遇难的人,他们去救是很本能的呀。”方励理解这种朴素的善良:“渔村里的家庭跟其他地方的人是不一样的,家家户户大多有过这样的家族历史,都有出海遇到海难没回来的人。所以跑海的人就有这个传统,见到别人遇上海难,都会马上去救人,仿佛他们刻在基因里的。”
那些沉睡的往事正在大屏幕上醒来,正在影院之外传播,不是以仇恨的姿态,而是以“我们曾互相拯救”的温情。
做一次人:在利己的世界里种下利他的种子
“做一个人多难得啊!”方励在采访里感慨地说了几遍。“这种几率在数学上都不成立。你来看看,你是宇宙一百五十亿年的一百五十亿分之一,太阳系四十六亿年的四十六亿分之一,你再乘以第一个单细胞生物存在至今三十五亿年的三十五亿年分之一,加上绝迹了的恐龙距今6500万年,南方古猿距今600万年,直立猿人距今200万年,现代智人距今20万年,今天全世界80亿人,你是80亿分之一的存在,以上这些加乘在一起,是怎样微乎其微的存活概率?有我们吗?没有!所以,感谢你的爸爸妈妈,然后我们都好好做一次人吧。”方励导演张口便带著庖丁解牛般的精准与流畅,每个术语、每条原理都像刻在骨子里,字句如流水般自然倾泻,连同浓郁而深切的人文情怀。
这个曾在切白菜时为植物生命感动的导演,骨子里藏著对“人”这个身份的敬畏。他回忆起二十年前那个触动心灵的厨房瞬间:“我从冰箱里拿一颗大白菜,放在案板上,我一刀下去,切成两半,我突然就触动了。我想到,那白菜也是生命啊,虽然是植物,但被我一刀切两半了。我穿著拖鞋,站在厨房里,那一瞬间,那样的时间空间里,我莫名其妙就被触动了。”那一刻他深刻体会到:“做一个人多难得,我怎么那么精彩,做了人。人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兴趣爱好,有自己的理想和梦想,人会有感性的一面,才叫做‘人’啊。”
当被问及为何投入八千万,花费八年时间拍摄一部不知道是否回本更别提能否盈利的电影,他的回答带著理工人的直白:“如果知识只用来赚钱,那人和没进化的动物有什么区别?”在他看来,“人的最灿烂的地方在哪呢?在能够利他,能为他人做一些事。如果把我们的能力、才华用来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他人,你会觉得自己更有价值。”
这种信念贯穿了他的人生。从物理勘探到电影制作,跨界的背后是不变的逻辑:能力越大,利他的半径就该越大。“一个大写的‘人’,一定要让它一撇写‘善良’,一捺写‘利他’。”
电影里,那些东极岛渔民,明明自己吃不饱,却把仅有的乾粮分给战俘;那些英国家庭,明明被遗忘了八十年,却对著陌生的中国团队敞开心扉。这些瞬间让他确信,人性的底色从来不是精致的冷漠,而是互助的温暖。
方励常对年轻人说:“当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你能够利他,你能让别人快乐,你自己也会更快乐。”利己是活下去的基础,这是动物性的本能。“但是如果你能够为他人做更多的事情,让他人不受那么多苦难,让他人生活能够改善,你就变得更有价值。一个人能帮到他人,是幸运的”。八年时间,他用科学家的严谨考证历史,用电影人的敏感触摸情感,最终证明了一件事:比起炮弹的射程和爆发力,人性的善意辐射范围要宽阔得多。
深海作证:和平年代里的永恒功课
战争会摧毁物质,却摧毁不了一朵花的初心。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的今年,在世界仍有硝烟弥漫的角落,《里斯本丸沉没》讲述的从来不是过去,而是当下——我们该如何守护那些让人类文明延续的东西:善良,共情力,以及对陌生人的牵挂。
方励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观众明白:“和平有多不容易,自己健全的家庭有多珍贵。”他看著当下世界的纷争,“全球还有很多地方都有战争,有战争就会有妻离子散、悲欢离合。”因此更要学会更加珍惜自己的家庭和我们所处之处的和平。
“亲情或者人类的情感是一个共通的链接,所有人都能理解和共鸣的。”方励的打捞还在继续。不是在深海,而是在每个看过电影的人心里。他用八千万投资证明,有些成本永远值得付出。他用地球物理学知识提醒我们,最该精确定位的,是内心的良知。
就像他说的:“做人就是情绪感情用事的,你见别人有困难你会同情,你帮助人家,人家给你道了谢,你还被感动,这就是人的‘特权’。”
从方励导演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因上努力,果上随缘”的机缘感。随遇而安,而又冥冥注定。《里斯本丸沉没》这部电影好像是浩大的时光专门等他而来,又好像是他成就了这段历史。中国人禅宗讲三境界。第一境界“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芳迹”。第二境界“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第三境界“万古长空,一朝风月”。可见“禅”的最高境界是寂灭清净,清净圆明。方励导演开朗韧性带点活泼的性子里,隐隐潜藏著一种禅意的最高境界。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是方励导演的内心韧性和坚定,与外在松弛和善意的最好写照。
当香港的暮色逐渐漫过维多利亚港,首映会的掌声渐渐平息,那些走出影院的观众或许会明白:历史从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无数个“我”的故事。方励教会我们的,不仅是如何打捞过去,更是如何活在当下——带著善心待人,带著恒心成事,带著慈悲心对众生。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个需要我们守护的历史瞬间,会在哪个转角等待。而那时的我们,是否能像八十年前的东极岛渔民一样,像今天的方励一样,毫不犹豫地伸出手去。
这或许就是对和平最好的守护:让战争里的温情,成为和平年代的日常。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善良的传播者、历史的保存者,在利他的道路上,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正如方励所言,来到人间,就要“做一些前人还没做,我们也来得及做的事”,让人性的光辉,永远照亮历史的长河。
你一定要走进电影院,见见故事里这些素未谋面的人。







 今日热搜
今日热搜

 本周热搜
本周热搜

 本月热搜
本月热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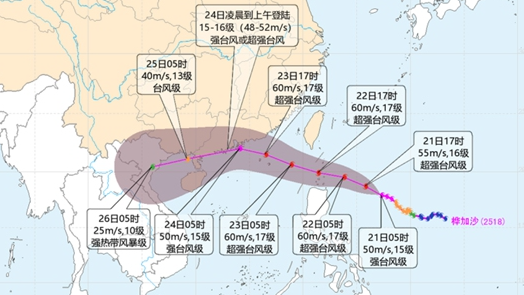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