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曦
坐在维园长椅上休憩,在这浓荫匝地,绿草茵茵的晚春晨光中,“布谷布谷,布谷布谷”鸟鸣声逶迤而来,如梦如幻,幻变为童年的听觉记忆。“布谷插禾,布谷插禾”,布谷鸟啼唤时,我依稀记得,秧田的禾苗可以拔出移栽于水田中了。
老公说,好不容易休息,中午要不出去午茶?我摇摇头,NO,我今天想做麸子肉。麸子肉即粉蒸肉,是老家的叫法。当然,做法也不尽相同,不是用米粉,而是用糯米,是春季农忙的必备餐食。
在老家,布谷鸟叫时正是插田的时候,女婿会和妻子一道去岳家,送“插田礼”——四个纸封(猫耳朵、麻丸粒之类的副食品),一刀猪肉(四斤),以答谢岳父岳母把女儿(也是一个劳动力)嫁给他。这天,夫妻俩留下来帮忙岳家扯秧插田。岳母则会用这一刀猪肉,和上糯米,蒸一大盆麸子肉,用以招待女婿。
我婚后在外地工作,老公是城里人,好似那时已无“插田礼”一说。春日里有时会买蒸肉米粉做粉蒸肉,很少会做传统的麸子肉。小时候姑父姑母回家帮忙插田,奶奶每年都会做麸子肉犒赏大家。我在灶下烧火,早已耳熟能详,复刻出来并不难。
去菜市场买了两斤五花肉,一小包红曲粉,一杯醪糟。五花肉切成半寸立方,加入盐、味、姜汁、醪糟水搅拌腌制。二斤糯米淘净泡发备用。半个小时后,把肉块、糯米、红曲粉、胡椒粉一起搅拌,让每块肉都均匀沾上米粒,用盆盛了,加少许水,放入电蒸锅,调高温蒸。
出锅撒上葱花,如盛放的桃花点缀绿叶。夹上一筷,桃红的糯米粘在肉块上,泛著晶莹油亮的光。送入口中,肥肉软烂如绵,瘦肉略有筋道。肉中醪糟的甜,姜与胡椒的辛,红曲中肉桂与小茴的香,葱香,丰富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我满足地吃著麸子肉,思绪从餐桌弹回童年。门前的桃花铺了满地,板栗树上挂满了长条的淡黄花序,奶奶踮著小脚在坪前晒菜苔。姑妈、伯母、母亲带领堂姐们在屋下的秧田弯腰扯秧,堂哥们各自担一担秧苗,摆胯摇臀,走上田埂,走上池塘堤岸,走向远处的六亩丘,田中的那几点黑,是弯腰插田父亲、伯父、姑爹。
灶膛里的火花在咆哮,灶上的蒸屉热气在跳舞,奶奶说,“再捂一灶火,麸子肉就熟了。”我从灶后蹦出来向外跑,跑向屋下秧田边,“吃饭啦!”又跑向池塘堤岸,双手做喇叭状,朝著六亩丘方向用力大声喊,“吃……饭……啦……”
母亲她们把八仙桌摆在了坪外,父亲他们在池塘码头清洗脚上的泥巴。菜一道一道上桌,桌中央是大盆红艳艳的麸子肉。人也一个一个围拢来,大人一桌,小孩一桌,言笑晏晏。在板栗花馥郁的香气中,布谷鸟还在声声慢,“布谷插禾……布谷播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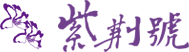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