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青子衿
我对于桃花的情绪是复杂的。
在家乡,父亲曾经栽种过两棵桃树,靠井边的桃树蓬蓬勃勃地长开来,一天比一天高,一年比一年大,桃树第二年开始开花。那应该是我第一次看到桃花,五六片粉红的叶片,黄色的芯,闲散地开在小桃树上。我忍不住掰了一截开著桃花的枝干,放在一个盛了水的酒瓶里,水里加了少量的盐。我期望桃花迟一些凋谢,慢一点落下。每日里,我在桃花清香的气息中醒来,又在桃花微微的笑意里睡去。夜里,无论有没有梦,都是欢欣快慰的。仿佛含了蜜一样。这枝桃花足足与我相伴了半个月,我看它时,它虽静然不语,却是笑意盈盈。它看我时,总是脉脉含情,温婉可人。
这株桃树在三年后,结出了桃子,毛茸茸的,小小的,与大一点的石子和土疙瘩差不多大,却尤其甜。因为口感好,离井沿太近,每一年还未等到桃子长大,泛红,树上的桃子就被东摘一个,西摘一个,所剩几个。一群孩子就风一样袭来,在桃树下叽叽喳喳,几双眼睛交错著像一张捕捉猎物的网,在桃树的叶子里梭巡。直到确认再也找不到一个桃子,才风一样刮走。
当然,这阵风也会提前刮过,那就是我和家人的出现,还没等到我们反应过来,就听“哗”,几个人影从桃树下一闪,呼啦啦转瞬间无有踪迹。只留下几声笑,如银铃般串在一起,前前后后,起起伏伏著。其实,我们对于桃子的去处倒不是太在意,父亲说,孩子们馋嘴而已。
那一年我大概八九岁,家里养的一条狗由我命名,我骄傲地唤牠作“霹雳”。我因此也把这只狗与我的喜怒哀乐牵系在一起,我与牠形影不离。至今我都能清晰地记得那种黏腻的情感是怎样开始,又是怎样结束的。那是个桃花盛开的日子,井旁的桃树开满了花,像一个庞大的花篮。午后,阳光灿烂。河岸边,我追逐著“霹雳”,并一次次用手抄起水泼洒在“霹雳”身上。牠不急不吼,只是摇头摆尾,上蹿下跳地沿河沿向前蹦跳著,偶尔还回头望我,呲牙咧嘴地笑……
不久,因为意外,“霹雳”永远离开了我。因为牠的消逝,多年里,我都不太敢养狗。“霹雳”的离去对我打击太大了。
虽然第二年,姐姐担任了喂养另一只狗的任务,我却总是离牠远远的。不知为甚么,那只狗并没有长大就夭折了,姐姐把牠埋在了桃树下。那时恰巧也是开满桃花的季节,我看见姐姐握著锹把,用力地向桃树根挖去,身体忽高忽低,两颊绯红,与盛开的桃花交相呼应。
有时我觉得,我的前世与桃花一定存著某种渊源。我们是如此相似,立在自己的枝头,不管枝头高矮,枝干粗细,只要温度适宜,在适合的季节,自然开放,自由生长,花自盛开水自流。
如此甚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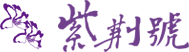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