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荆论坛》专稿/转载请标明出处
邓思颖 |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首先论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香港的中国语文教学的关系,提出以通用为纲,以差异为目。通过将词汇学习作为本文的讨论重点,建议词汇可划分为文言词、方言词、社区词、普通话词;以学习普通话词为核心,适当把文言词纳入教学当中,并系统比对方言词、社区词跟普通话词的异同。通过学习语言,进一步了解文化,以语言作为文化的传播载体,并以语言作为文化研究的对象,加深对文化的认识。学习的大方向,是以文化为本,以形式为末。通过语文学习,增进学习者的文化认同,建设现代文明。秉纲而目张,执本而末从,期望语文教学的问题能迎刃而解。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早于1982年写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推广国家通用语言,可谓宪法规定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下简称「《语言文字法》」)于2000年10月31日获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并在2001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法的制定,彰显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同时也是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制保障。
《语言文字法》第一条明确说明,「为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其健康发展,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这是我国以法律形式确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地位的表现。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健康发展」这几个关键词,可谓该法的精髓。《语言文字法》的制定,让语言文字的使用有了明确的方向,并有可依照准绳,无论对语言文字的研究亦或是应用等方面都非常重要。

至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定义及范围,《语言文字法》第二条作了清楚的界定:「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在第三条中,有关语言文字的工作也有清晰的说明:「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由此可见,这两条确定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为了行文方便,在不涉及文字讨论的语境里,本文也会采用「国家通用语言」一语。
至于「普通话」的定义,非常清晰。国务院在1956年2月6日所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有说明,普通话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至于「规范汉字」,即是以《通用规范汉字表》为准。该字表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制,整合了1955年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64/1986年的《简化字总表》、1988年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1988年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等文献,于2013年正式颁布。简而言之,规范汉字就是经过整理规范后的简化字。
顺带一提,按照教育部在2009年7月21日公布的英文新闻公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英语翻译为「the Standard Spoken and Written Chinese Language」。根据这个翻译,「通用」一词的理解,可以对应英语的「standard」。至于「普通话」,则用汉语拼音的拼写「Putonghua」用于英语的语境,并用英语作说明:「a common speech with pronunciation based on the Beijing dialect」。此外,教育部的英文新闻公报偶尔采用「Mandarin」「standard Mandarin」等来对应「普通话」。国务院的英文网页中,用「Mandarin」的场合比用「Putonghua」的场合多得多。至于香港地区的情况,在英语语境中把「普通话」一词翻译为「Putonghua」或「Mandarin」都有,但前者较为常见,往往用于香港特区政府的文件和公函。比如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在中小学普通话科的英文文件中,就是使用「Putonghua」一词。2020年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以推广普及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重点」作为指导思想之一,「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准进一步提高」等作为主要目标。这里所说的「规范化、标准化」,与《语言文字法》的精神可谓一脉相承。至于「信息化」一点,更好突显了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新任务,以适应时代的急速变迁。《意见》中与香港相关的部分,主要有两点:第十二点谈及「提高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提出「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的语言服务」,包括开展语言专项调查、开展语言生活状况监测、加强国家应急语言服务等方面;第十五点谈及「深化与港澳台地区语言文化交流合作」,提出「支持和服务港澳地区开展普通话教育,合作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提高港澳地区普通话应用水平。加大与港澳台地区青少年语言文化交流力度,组织开展中华经典诵读展演、语言文化研修等活动。加强与港澳台地区在科技术语、中文信息技术、语言文字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综合上述这两点,与香港相关的语言文字工作,主要涉及加强语言服务,善用研究和应用成果,提供符合社会需要的服务,更好地满足社会语言需求。加强内地和香港交流合作,包括普通话教育、普通话测试、文化活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
回归后香港中国语文教学的发展
自回归祖国以来,香港语文教育的主要工作对象,可用四个字概括:「两文三语」,即重视「两文」的中文、英文,还有「三语」的普通话、粤语、英语。以中国语文教育为例,正如课程发展议会在2017年编订的《中国语文教育:学习领域课程指引(小一至中六)》中所指出,「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掌握规范的书面语,能说流利的粤语和能以普通话沟通」就是主要任务之一。中国语文教学的基本理念,就是要「培养善用『两文三语』沟通的人才,以提高香港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同时促进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和联系。『文』指书面语,『语』指口语」。除了兼顾包括白话文和文言文的「书面语」和普通话和粤语的「口语」外,该指引页特别重视「运用规范书面语的能力,以避免学生的表达受口语或网络语言影响」。除了中国语文科以外,自1998年以来,普通话科被正式纳入香港小学至初中的核心科目,目的是确保所有中小学生都能够学好普通话。至于普通话科的课程理念,课程发展议会在2017年编订的《中国语文教育学习领域:普通话科课程指引(小一至中三)》中明确指出,「香港属于粤方言区,粤方言和普通话在语音、词汇、语法上有同有异,本港普通话科的学与教,应以广东人学习普通话的难点作为重点,以提高学与教效果」。
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2024年11月6日回复立法会议员提问时所作的书面答覆中,清楚阐释「教育局一直积极推动普通话教学,并采取多元策略,从课程、学与教支援、学生活动、教师专业发展等各方面,推动学生在课堂内外学好普通话」。《行政长官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拨款约4.7亿元强化英语、普通话和其他语言的学与教」。蔡若莲在上述书面答覆中,更具体说明「教育局在语文基金预留约两亿元,于2024/25学年向每所公营中小学发放一笔过津贴,以营造丰富的普通话语言环境,加强普通话学习氛围」。由此可见,特区政府在推动普通话教学、提升普通话水平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综上所述,香港的中国语文教学主要以「两文三语」中的「一文两语」作为教学宗旨。「文」方面,重点在于「规范的书面语」;「语」方面,就是训练普通话和粤语的沟通能力。教学的目标,离不开两大方向: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辨认地区差异。 换句话说,「文」就是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语」应平衡普通话和粤语,提升学生口语能力,加强学生对相关口语的语言知识。
语言是一个包含语音、音韵、词汇、语法、语义的系统;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拥有「形音义」的系统。无论是语文学习还是语言使用,都不能把这个系统割裂。以普通话为例,普通话就是一个包含「形音义」的完整系统。「音」,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所谓「形义」的词汇语法等,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只有把「形音义」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普通话。「规范的书面语」教学,不能只管词汇语法;普通话的教学,也不能只抓发音。目前香港语言教育的现状,往往存在「白话文与文言文混用现象」「用粤方言读出中文书面材料的现象」。 这些情况,肯定是不适合的。
我们要充分意识到语言是一个系统,一个整体。「文」和「语」的教学和使用,应该要一致,不能割裂。理想中的中国语文教学,应该要把「文」和「语」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就是以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纲,用一个统一的系统讲授语言的形音义,那就是结合北京音、北方话、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的普通话;以辨认差异为目,通过对粤语、普通话的对比,了解两者的异同,加深认识。把两套不同的形音义系统区分开来,不能相混,从而做到秉纲而目张,学好语文,提升水平。
建议在教学中将词汇分为四大类
词汇作为组成语言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在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工作中,尤其是香港的中国语文教学中,尤为重要。没有科学的分类,往往难以掌握好国家通用语言的词汇,也难以辨认出语言的地区差异。本文建议词汇可划分为以下几大类:文言词、方言词、社区词、普通话词。
文言词,又称「古语词」,即「书面保存下来的古代词,有文言色彩」,基本以先秦汉语为基础。国家通用语言即普通话,则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基础和规范。因此,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文言文与白话文有别,文言文与国家通用语言有别。文言文的词汇语法,不能全盘用于国家通用语言。例如,古汉语第一人称的「吾」「余」等,还有第二人称的「汝」「尔」等代词,虽然《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收录了,但明确标注为书面上的文言词语。《荀子.劝学》中有一句:「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当中的「水」,用作动词,这是古汉语的用法。上述的代词,还有用作动词的「水」,显然并非普通话词语,不属于国家通用语言。然而,不少文言词仍然活用于当代语言里,如形容说话的「侃侃」、表示独一无二的「绝伦」、形容山高的「崴嵬」等,都属于文言词,用在一定的场合,往往能产生庄重典雅之效,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能丰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方言词,在香港专指粤语词。香港的方言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有普通话的对译,可称为「可译方言词」,如名词「褛」(大衣)、动词「喊」(哭)、形容词「牙烟」(危险)、代词「佢」(他)、副词「正话」(刚刚)、句末助词「喇」(了)、「嗬」(吧,对吗)等。这些方言词,可以全转为普通话,用普通话已有的词汇来表达。关注可译方言词在普通话中的表达,可作为学习「粤普对应」的重要部分,力求避免把这一类方言词带入普通话里。
另一类方言词则不太容易找到普通话中的直接对译,可称为「特有方言词」,例如「肠粉」「烧味」「粉果」「鱼蛋」等生活词汇,尤其是饮食方面,很具地方特色。事实上,不少生活上的特有方言词,已被收录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如「河粉」「蛋挞」「埋单」等。这些特有方言词,反映了地域文化的特色,往往不能也不必翻译为普通话。在中国语文教学方面,特有方言词值得保留。通过特有方言词的教学,既可以让香港学生了解地域文化,认识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又可以增强学习动机,提高投入感。
此外,香港不少地名也保留了方言词。这些方言词的普通话发音值得好好整理,并向学生有系统地介绍,帮助其掌握正确的普通话发音,准确用普通话表达身边熟悉的生活环境,例如「禾輋」的「輋」(shē)、「鲗鱼涌」的「鲗」(zé)和「涌」(chōng)、「深水埗」的「埗」(bù)、「大埔滘」的「滘」(jiào)、「黄埔」「大埔」的「pǔ」和「bù」两种不同读法等。这些方言词的学习,不仅是普通话发音的问题,也可以从中了解地域的地理特点,加强学生对香港以及华南地区的认识。
社区词的产生,则是「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不同,以及不同社区人们使用语言的心理差异」。 有些社区词,「直接因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因素的不同而产生」,可称为「核心社区词」;有些则「跟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因素只有间接的关系,甚至没有什么关系,纯粹因地域差异而有区别」,可称为「边缘社区词」。「核心社区词」的例子,如「安老院」「八达通」「回乡证」「居屋」「专线小巴」等常见的生活用语,流通于香港社会,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过,一旦离开香港,在内地和其他华人地区,这些词就不使用了。
至于「边缘社区词」,往往跟社会制度的差异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以香港社会表示清点计算的「点算」为例, 那是香港社会继承了晚清民初的书面语,在香港的中文中保留下来的用法。严格来讲,既非文言词,又非方言词,但目前还没被普通话所接受。这种边缘社区词,值得广泛调查,并在中国语文教学中多加说明,让学生了解其独特性。如若放眼全球华人所使用的汉语,就会发现不少词汇的差异,这些差异同时也正好反映了地域上的差异。例如,中国内地所说的「出租车」,在不同的华人地区,会说成「计程车」「的士」「德士」。即使内地用「出租车」一词,加上动词「打」,还是普遍接受「打的」的说法,当中的「的」,就是「的士」。事实上,「打的」这个词,已被《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所收录,作为普通话的口语词。又如「自行车」「自由车」「脚踏车」「单车」「脚车」等,流通于不同的华人地区。又比如,「窝心」一词在不同的地区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种表示贬义的恶心,另一种则表示褒义的温暖。又如英语的「digital」,可以翻译作「数字」「数码」「数位」,也有著地域间的差异。通过了解全球华人用语(包括社区词)的异同,建构能通用于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这就是所谓「大华语」的构思。
普通话词以北方话为基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规范的词汇,也就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权威工具书中所收录的词汇,有一定的规范性。将其作为标准,组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核心部分。普通话词在不同的语境里,往往有不同的叫法,如「规范书面语」「标准中文」 「通用中文」等。
普通话词每年都会汇入新词语。例如,中国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等,每年都会公布口语、网络普遍接受的「汉语盘点」。以「汉语盘点2023」为例,「十大新词语」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全球文明倡议」「村超」「新质生产力」「全国生态日」「消费提振年」「特种兵式旅游」「显眼包」「百模大战」「墨子巡天」,而「十大网络用语」包括「爱达未来」「烟火气」「数智生活」「村BA」「特种兵式旅游」「显眼包」「主打一个XX」「多巴胺穿搭」「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新职人」。这些新词既反映了语言的生命力,又能让人们从中了解当代社会的最新发展。从规范化的角度来思考,加大广播影视、网络资讯等相关领域的「监督检查」,加强「监测研究和规范引导」,强化「规范和管理」是有必要的,务求做到新词的「规范」「标准」「健康发展」;从语文教学的角度来看,尤其是香港的中国语文科和普通话科,虽然课程发展议会于《中国语文教育:学习领域课程指引(小一至中六)》中曾指出「避免学生的表达受口语或网络语言影响」,但从普通话口语把新词适当引进到教学里看来,既可提升学习趣味,又可以让香港学生了解内地在新时代的新动态、新发展,吸收新资讯。如此,香港学生到内地学习旅游,遇到新词新事物,就不会觉得陌生。
综上所述,词汇学习可划分为文言词、方言词、社区词、普通话词学习。通过对文言词的学习,注意文言和白话之别,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写作中更显庄重典雅。通过辨认方言词,一方面作好粤语与普通话的对比(尤其是可译方言词),避免「方言入文」,另一方面通过特有方言词,了解地域文化特色,领略中华文化的丰富性。通过认识香港乃至全球华人的社区词,无论是核心社区词还是边缘社区词,可开拓学生视野,使其视野更开阔。
普通话词的学习是中国语文科和普通话科的基础,为掌握好现代汉语奠定扎实的根基,也是认识当代中国的重要工具。语文学习以通用为纲,加强普通话词的学习,并适当把文言词纳入教学当中,提升语文修养;以差异为目,系统了解方言词、社区词跟普通话词的异同,务求做到秉纲而目张。
语言作为文化传播载体
通过语言了解文化,由此把语言和文化联系在一起,建立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建基于两种情况:以语言作为文化传播载体,以语言作为文化研究对象。
以语言作为学习文化的工具,一直以来都是基础教育所重视的一环。正如课程发展议会于《中国语文教育学习领域:普通话科课程指引(小一至中三)》中所指出,香港的中国语文科,学习任务主要是要让学生「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培养语文学习的兴趣」,「透过文学的学习,可以引导学生感受语言文字和思想内容之美,培养善感的心灵,陶冶性情,发展个性,美化人格,促进全人发展」「鼓励学生熟读或背诵若干蕴含丰富文学、文化内涵的经典名篇,以积淀语感,提高语文素养」。无论研读现代篇章还是古代作品,都以语言作为形式。通过语言这个工具,欣赏文学,增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至于后者,即以语言作为文化研究的对象,属于以语言学的视角去考察语言,从而了解文化。所谓语言学的视角,我们可以通过语音、音韵、词汇、语法等形式,观察语言有趣的一面,加深对其背后文化的认识和认同。以词汇教学为例,从词汇的多样性,认识祖国的南北古今。例如,通过粤语方言词「颈」(脖子),我们可以认识古汉语的「颈」,学会《庄子.马蹄》「喜则交颈相靡」中「颈」的意思。再延伸到普通话的「脖子」,通过词汇的变化,还有加上「子」尾的要求,一并解说为什么普通话要加「子」尾,并由此产生出一系列加上「子」尾的名词,如「桌子」「椅子」「刀子」等。汉语名词从古到今,经历过从单音节到双音节的历时发展过程。以宏观的视野,体会语言的变与不变,从而加深我们对汉语及中华文化的认识,达到触类旁通、一叶知秋的效果。
又如「汉语盘点 2023」所选出来作为「十大网络用语」之一的「爱达未来」,原本来自2023年在杭州举办的亚运会的大会口号:「心心相融,@未来」,当中的「@」,读作「爱达」,即英语的「at」。为甚么「at」读作「爱达」呢?从语言学的角度,这个问题就很好说了。英语「at」的韵尾是个塞音「t」,但普通话音节结构中却不允许塞音做韵尾。因此,只能把「at」这个音节拆开为两个音节来读,即用「爱」来读「a」,用「达」来读「t」。这样拆开后,「爱达」表述更有意义,借此共迎美好的期许,寄托著面向未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良好愿望。 这样充满创意的语言事实,既突显汉语和英语音韵的差异,又可描绘出祖国在新时代的发展,让语文学习更具生动趣味。
从语言认识文化,学习的大方向,应以文化为本,以形式为末。香港的中国语文教学,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共通特点,彰显古今乃至地域差异所呈现出的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进而鼓励年轻人积极投入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中去。只有语言相通,才能心灵相通。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期望「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树立命运相通的共同体理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国家发展的大方向。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工作,在新时代有重要的使命,并非为做而做,而是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而进发。通过语文学习,增进文化认同,建设现代文明,可谓任重道远。只要明白这一点,就知道什么是语文学习的纲目本末:以通用为纲,以差异为目。以文化为本,以形式为末。秉纲而目张,执本而末从。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4年10-12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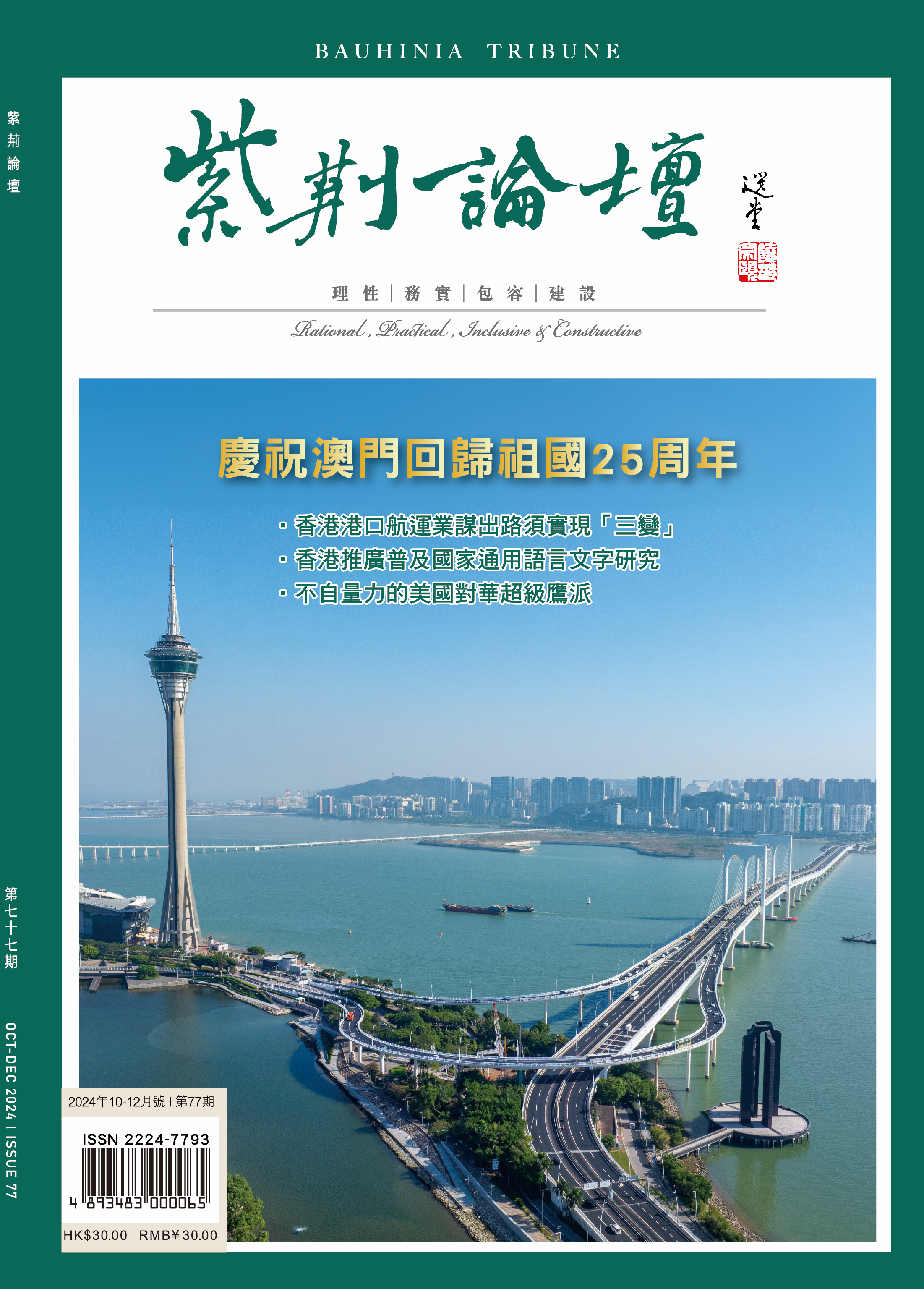







 今日热搜
今日热搜

 本周热搜
本周热搜

 本月热搜
本月热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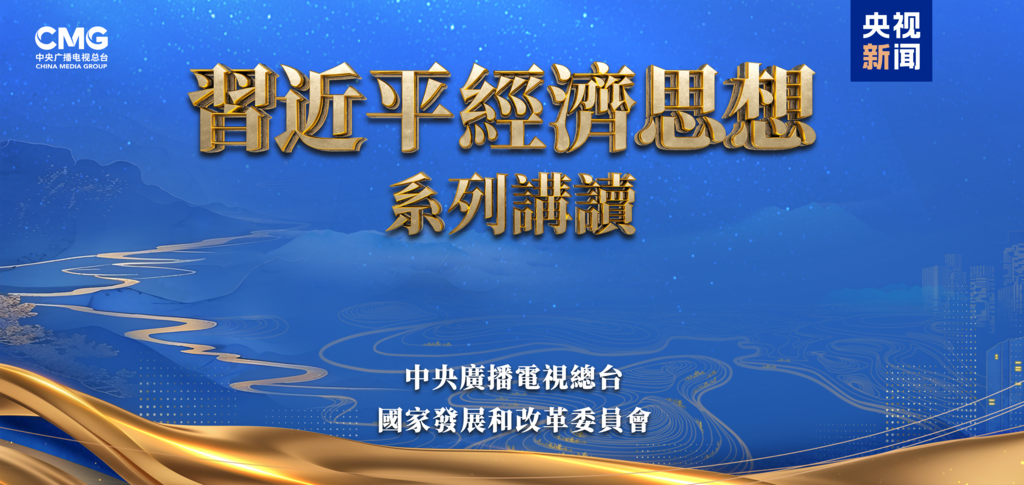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