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飞龙
2024年1月30日,香港特区政府启动23条立法公众咨询活动,为期一个月。从政府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来看,有关立法原则和框架基本清晰,公众立法咨询和参与获得有效的指引,可以针对性研究和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公众咨询是民主立法的一个重要环节,本身就体现了23条立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是香港居民享有的基本法上之民主权利的体现。在2020年引入《香港国安法》之后,何时并以何种方式完成23条立法一直是“一国两制”制度建设与香港法治发展的重要而敏感的议题。在选举制度改革、区议会制度改革及新的立法会、区议会产生之后,在香港“爱国者治港”获得政治正确性、法律权威性和社会文化领导力之后,特区政府决定启动23条立法,其立法时间点的判断和选择是精准的,也是合理的。
23条立法,从历史来看,是香港法治发展的最敏感议题之一。2003年的23条立法挫折,暴露出香港对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认同缺失和法律盲视。彼时的香港法律界及市民社会拥抱著一种与国家利益相对抗的自由民主观念,认定23条立法是自由之敌,是中央及其控制的特区政府干预香港自由民主的制度抓手。反对派当年发起的城市抗争大游行,不仅重创了立法进程,损及了特区政府权威和基本法权威,而且催生了香港城市民主运动的新范式,后来的非法占中和修例风波与之有前后承续关系。香港反对派与市民社会不信任国安立法,不认同国民教育,其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行动锚定于“双普选”。这就造成了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制度文化的价值撕裂:爱国与民主对立,安全与自由对立,一国与两制对立。在此类对立与对抗条件下,23条立法挫折是必然的,23条立法延宕至今也是必然的。然而,香港反对派终究缺乏政治美德、政治想像力、政治公心和政治妥协技艺,一味对立对抗乃至于颠覆,破了法律底线和“一国两制”制度安全底线,就必然引发国家自上而下的立法和治理改造:爱国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
这次重启23条立法,从中央到港府再到爱国者群体,是责任感强烈,制度共识凸显,自信心充沛。这是一次“补课式”立法,是在《香港国安法》基础上进一步弥补国安法律漏洞、全面应对国安制度风险及构筑完整国安法网的重大制度建设,具有显著的必要性与合法性。这次立法也不同于2003年立法,其制度环境与立法目标已有重要的变迁。《公众咨询档》对此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解释说明,对公众具有立法释明和参与引导的积极功能。
此次23条立法在“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与香港法治发展层面具有如下特点和制度进步意义:
第一,23条立法以更完整的制度基础为依托,全面回应新时代香港国安制度风险。此次23条立法是不局限于狭义的基本法第23条的“23条立法”,其立法的规范基础既包括狭义的第23条,也包括全国人大“5·28决定”和《香港国安法》,并且需要在法律体系与规制技术上与《香港国安法》进行衔接、相容和补充。这就决定了此次23条立法不是简单回到2003年国安条例草案的框架,而是需要提出立足新制度基础的全新框架。《公众咨询档》第10页提及了此次23条立法范围的解释方法,认为基本法第23条“根本要旨是要求香港特区自行立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一“根本要旨”指向的习近平主席在香港回归25周年纪念大会上论及的“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指向的是“一国两制”范畴国家利益的具体内涵与类别,指向的是国家安全的“总体性”的法权意涵。
第二,23条立法在国家安全基本概念上采行“总体国家安全观”,但在具体制度安排上体现“一国两制”特殊性。《公众咨询档》明确了此次立法的国家安全概念的唯一性,即统一于2015年《国家安全法》规定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是新时代国家安全观,也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叠加整合的安全观。这一安全观表达于《国家安全法》第2条,即“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香港国安法》立法时并未明确香港适用“总体国家安全观”,概念的模糊导致实施的偏差,此次23条立法予以明确化,是“一国两制”国安立法的法理自觉和自信的体现。国家安全概念的同一化显示了“一国”的概念与利益的确定性,但《公众咨询档》亦指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律的具体措施“根据香港特区的实际情况而定”,包括香港适用ICCPR和《人权法案条例》的特定法律环境,这就凸显了“两制”的差异性。“概念同一,措施有别”,这正是“一国两制”制度原理的精髓所在。国家概念只能来自“一国”,国家安全概念也只能来自“一国”,在“一国”的法理清晰化条件下具体考量和安排“两制”对应的国家安全制度的差异性,以便与各自的法律环境相适应并形成融贯的法律体系,这是完全符合“一国两制”制度原理与现代法治建设规律的。
第三,23条立法在具体内容和体系上需要与本地法例、基本法第23条及全国人大“5·28决定”以及《香港国安法》相衔接与融贯,从而承担起《香港国安法》法律体系的结构枢纽功能。面对香港修例风波和区议会“黑暴化”的颠覆性威胁,《香港国安法》属于应急性和典型性立法,未能覆盖香港国安制度风险的全部,也未能覆盖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七宗罪”,更不可能在具体制度安排与程式上尽善尽美。经过三年多实施,《香港国安法》与香港普通法的制度性磨合有所进展,但国安领域的新风险、外来干预的制裁性风险以及港独组织国际化的风险等不容忽视,《公众咨询文件》中有具体列举和分析。这些因素要求23条立法实现全面、综合性的制度回应,实现法律体系的上下贯通,特别是实现与《香港国安法》的衔接、相容和补充。从维护国安的实际需要及法律体系完备性出发界定23条立法的范围、内容与体系构成,这反映了此次立法的科学性与合目的性。
第四,23条立法具体罪名和制度框架安排上体现了综合性、针对性和制度衔接性,是公众咨询与法律草案拟订的关键点。在立法范围上,《公众咨询档》确立了两项基本指导原则,即全面综合性立法原则和重复专案不立法原则。全面综合性立法原则是指本次立法需要全面回应国安制度风险,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也要全面落实全国人大“5·28决定”和《香港国安法》规定的宪制责任和义务。重复项目不立法原则是指《香港国安法》已经规制的分裂国家罪和颠覆国家政权罪,本次立法不再重复规定。在立法针对性上,《公众咨询文件》提出了如下立法罪名范畴:(1)叛国及相关罪行;(2)叛乱、煽惑叛变及离叛,以及具煽动意图的行为;(3)窃取国家机密及间谍行为;(4)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等活动;(5)境外干预及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组织。这些罪名范畴涵盖了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有关罪名以及新出现的需予规制的罪名。这些罪名之订立及刑罚之具体配置,涉及多部本地法例如《刑事罪行条例》、《官方机密条例》、《社团条例》等的修改,也涉及部分的普通法罪行的成文化。这些具体的立法技术性问题,香港法律界可以有很大的意见参与空间。制度衔接性是重要课题,23条立法既要与本地法例横向衔接,又要与《香港国安法》纵向衔接,并确保自身订立的制度规范符合法治与人权保护的既有标准。
第五,23条立法具有域外效力,与《香港国安法》的保护管辖原则保持一致,增强立法的威慑性与执行力。从比较法角度而言,国家安全法的域外效力及其保护管辖规定是通行做法,因国家安全犯罪具有特殊危害性和行为模式的跨境倾向,法律需要订立与之相称的域外管辖机制。当然,这种域外管辖机制并非一种非法的长臂管辖,而是一种互惠机制,其具体执行需要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刑事司法互助协议加以实现。目前来看,《香港国安法》的域外管辖机制遭遇到美西方国家的政治阻却和制度干扰,导致诸多港独分子和组织逍遥法外,也放纵了外部干预势力的非法破坏行为,这是美西方国家“司法政治化”的体现,并不符合法治原则。但域外管辖机制仍是有意义的,可以对本土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的勾结破坏行为进行合理的延伸打击,并尽可能压缩其国际活动空间和具体行为的煽动效果。随著中国法治进步、国际地位提升与国际合作机制的完善,《香港国安法》与此次23条立法的域外管辖机制会逐步显示强大威力和精准惩罚性,故在本次立法中加以明确规定并规范执行,是合理与有远见的。
总体来看,《公众咨询档》提出了23条立法的背景、原则、框架和议题,是一种“纲要”式的立法计划书,也是公众可具体参与的立法框架稿。此次23条立法不是如同2003年那般宽松和缺乏明确框架,而是有著全国人大“5·28决定”和《香港国安法》的既定法制前提和基础,有著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列举范围,有著香港本地法例的关联性条款,还有著国安新风险的事实依据。《立法咨询档》将这些因素统筹归类,提出了面向公众和专业人士、甚至包括国际利益相关者的立法咨询框架,显示了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公开性。即便如此,此次立法仍然且必然持续遭受来自本土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的诋毁和指责,也会遭受来自市民群体的某种质疑和误解,这就更需要港府和爱国者阵营进行充分动员,展开充分咨询,提供充分解释说明,包括在香港本地及国际社会的一般性公众沟通和专业界别的定向沟通。当然,刻意的歪曲、唱衰和打压,是很难通过理性沟通加以消除的,这就进入了立法斗争的范畴。此次立法必然遭遇到持续和激烈的舆论战、法理战和资讯战,这对于经历过修例风波的港府及爱国者阵营恰恰是又一次重大的政治考验,是对“爱国者治港”之忠诚贤能水准的集中测试。同时,台湾地方选举中赖清德胜选,务实台独派得势,以及美国总统大选的“中国牌”效应凸显,美国盟友跟进行为加速抬头,23条立法及其相关联的“一国两制”话语权与中国国家发展确定性恐又将陷入纷争之中,香港经济与金融地位以及中国形象与法治规范性需要经历复杂的博弈、斗争和塑造才能重新确立自身的稳定性、规范性和可接受性,这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和“一国两制”长期坚持必须经历的阵痛和新生。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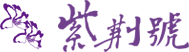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