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飞龙
2024年,《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通过,「23条立法」高质量、高效率完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与执行机制基本完备。2024年,香港迈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谱写「爱国者治港」的新篇章,「改革」话语在香港社会出现并逐步指向具体政策领域。
这些是以香港国安法为核心标志的「香港新秩序」的新风新貌,是民族复兴时代「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与融合发展的理性进程。决定这一进程的,是中国的文明复兴、现代化及其与世界关系的大转型,中国从现代化的「尾随者」及西方眼中的「东方落后国家」逐步自觉成长为基于自身文明和现代化经验的负责任大国,积极参与塑造人类和平发展新秩序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这一切重大变化集中发生于2012年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新政」及其与世界关系的结构性调整周期之中,更准确而言是2014年非法「占中」运动以来香港与国家及世界复杂互动的结果。
香港非法「占中」运动和反修例运动,在极度挑战「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底线、追求无视国家安全前提之「真普选」的激烈冲突中登场及落幕,刺激国家以垂直立法方式引入香港国安法及新选举法,缔造香港新秩序,推动「一国两制」之法理与制度重心由「两制」向「一国」作结构转型。
这一切冲击力之大,观念与制度转型之大,国家进场与西方制裁斗争之烈,以及香港民主法治与公民社会变化之急剧,大大超出了香港社会自有的政治成熟度与文化理解力。
十年之变,「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健全发展,国家安全与融合发展走上正轨,但香港社会自身的观念转型与制度适应,以及香港如何调校其与国家及世界的新型关系,构成香港新秩序的基本处境和挑战,同时也意味着新香港在21世纪的重大发展机遇。
一、十年:抗命歧途与国家安全
2014年,我有机会受邀赴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做高级访问学者,研究课题即为非法「占中」运动。
香港反对派为什么要非法「占中」?
公开的理由和目标是香港基本法承诺了「普选」,香港社会要国家兑现「普选」,且必须是「真普选」。「真普选」这个运动口号本身就标志着香港反对派对国家的严重不信任,唯恐国家最终给出的普选方案是「假的」。
2014年6月10日,国家发布香港回归以来首份治港白皮书,提出「全面管治权」概念,并对香港普选进行历史和法理层面的解释和引导,避免香港普选与国家安全相对立。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香港基本法政改程序作出著名的「八·三一决定」,从香港基本法的普选条款与国家安全大局的统筹考量角度给出了普选方案。香港反对派认定中央方案是「连落三闸」的假普选,遂发动为期79天的非法「占中」运动,并在2015年6月18日立法会政改方案投票时予以坚决否决,香港普选政改失败。
非法「占中」运动的理论依据是所谓的「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这是源自西方政治传统的一种社会运动理论,也有着实践个案与典型历史人物,对全球民主运动影响深远而复杂。
香港将这一套理论和做法搬过来,试图以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相要挟,逼迫中央作出重大让步。香港反对派的本钱和骄傲资本来自于对香港在西方体系中关键地位的想象性理解和高估,并严重低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及国家安全的根本重要性。
非法「占中」运动之发生,有着香港反对派长期民主动员、组织建设与路线凝聚的内在积累,也有着外部干预势力以「香港牌」渗透、影响及遏制中国的「准冷战」意图及战略指向性,二者勾结互动,造成国家安全的极大危害。非法「占中」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法治后果和社会后果:其一,破坏了香港社会的守法伦理和法治权威性;其二,误导青少年「违法达义」,为后续勇武暴力抗争埋下伏笔。
非法「占中」运动之后,香港社会的政治撕裂与对抗继续发展。中央的主导思路是以经济民生转移转化香港社会的「民主」焦虑和普选挫折感,但香港反对派并不买账,香港民主运动出现了民粹化、青年化、暴力化及外部干预深化的恶性发展趋势。
香港反修例运动就是这一恶性发展的结果。
这两场运动,极大消耗了香港的法治能力以及香港反对派与中央之间的脆弱信任,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完全对立起来。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香港反对派在文化与政治伦理上对最高原则严重失察,在运动动员上完全无视国家安全在政治与法治上的根本重要性及底线约束性,最终碰壁。
这暴露出香港回归以来因23条立法受挫和国民教育进程失利留下的巨大后遗症,香港民主运动在缺乏基本的国家安全前提和法治约束性的条件下发生,反对派与中央之间始终未能建立关于香港民主化的基础性信任与有效合作机制,香港反对派缺乏领导民主运动的理性妥协精神和必要的政治成熟度。
香港民主运动在缺乏国家安全制度保障与社会共识度条件下狂飙突进,误入歧途,付出了惨重的政治与社会代价,但客观上对香港社会有政治教育意义,并为国家进场引入新制度、缔造新秩序提供了历史契机和制度作用点。
二、新秩序:制度先行与社会转型
我对香港上述两场民主运动均有现场观察研究和学术专著,这是我的学术人生的重要经历和成果。非法「占中」运动之后,我出版了《香港政改观察》(香港商务印书馆,2015)。反修例运动之后,我出版了《抗命歧途》(香港新民主出版社,2020)。两场运动暴露了「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漏洞与短板,而这正是香港新秩序的契机和起点。
所谓香港新秩序,是对十八大以来中央治港的新理念、新制度、新政策及其实践成效的综合性概括。新秩序是制度先行的,最关键的制度标志是香港国安法和选举制度改革,而贯穿其中的核心法理是全面管治权。
香港国安法的引入,既是针对反修例运动之政治颠覆风险的应急管理,也是基于全面管治权的国家立法理性,决定性开启了香港由乱到治的制度建设大幕。客观而言,没有香港国安法的引入,香港现行的一切重要的制度改革和政策转型都无法展开。
香港国安法是香港新秩序的动力之源和最重要制度保障。香港国安法标志着国家执法权力在香港的个案化落实,标志着「一国两制」法理与实践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国家权力不再虚无飘渺,不再满足于高度节制和间接治理,而是在国家安全领域得以具体制度化展现。
美西方对香港制度之变的最根本焦虑和最重要的制裁理由就是香港国安法。只有这部法律让美西方对香港的控制权出现了根本性消解。象征意义上,香港国安法是「一国两制」香港平台上东升西降的一个绝佳缩影。
选举制度改革是香港国安法之后涉港制度建设的又一重大措施,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绝对保障香港的管治权安全及「爱国者治港」的名至实归。在新选举法下,爱国者治港,反中乱港势力出局,香港管治体系出现结构革新。
但中央主导的新制度建设及其新秩序,在香港社会与国际社会并未得到同步性的理解和认同,反而激发了美西方的制裁干预以及港独国际化的蔓延发展。
这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挤出-反弹」效应,是香港由乱到治必然经历的阶段和阵痛。打压香港,唱衰香港,根本原因在于本土势力和外部势力不再能够控制香港为其政治私利服务。新秩序下,香港社会结构与文化生态逐步发生重要转型,从以往过度西方化的「公民社会」转型为真正切合「一国两制」的「爱国者社会」,彻底破除香港社会政治文化中「爱国」与「民主」的长期二元对立,建设香港新的民主政治文化。
2021年12月,国家发布了第二份治港白皮书《「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对香港新秩序尤其是民主发展作出了权威性的历史梳理和制度解释,可以视为香港由乱到治之重大制度建设的一个官方总结。
新秩序在香港的「软着陆」及其社会和解与团结进程仍未结束,香港社会仍需要多元互动与理性协商,需要思想解放和社会大讨论,以便凝聚香港新阶段与新篇章的规范性共识。我在2021年出版《香港新秩序》(橙新闻出版社,2021)一书,对香港国安法与新选举法的法理、政治、政策、社会与文化多层面之脉络与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和阐释,我希望并渴望香港社会可以走出对抗国家、依赖西方的传统藩篱,真正培育出「一国两制」的国家视野及民族复兴的新时代责任伦理,对新秩序及其制度和发展内涵进行科学理解和本地转化。
三、新阶段:融合发展与新型全球化
香港这十年非常不易,其民主运动与社会斗争,背后折射的是香港在中西大变局中的精神迷惘、挣扎与新生,而香港新秩序给出的是香港与民族复兴的关键链接。
作为「一国两制」宪制秩序下的地方特别行政区,香港不可能在中西方体系性斗争中站在西方一边,香港需要一方面运用自身的国际缓冲带优势对中西方激烈斗争进行调解与缓和,为民族复兴争取最大时空条件,也对人类和平发展作出独特贡献,而另一方面则需要以融合发展为导向积极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带一路」建设及中国主导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协助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作出香港贡献。
「十四五规划」确定的「八大中心目标群」就是新香港的蓝图,也是香港新制度的规范性期许,更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纲目。「一国两制」绝不是权宜之计,更不只是简单的经济现代化,它是根植中华文明传统与世界体系演变规律的大战略,是国家对地方的高度自治授权与地方对国家的持续性贡献的理性结合,是中国治理文明与制度的「新边疆」并将之打造为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化最佳杠杆的新天下主义全球治理实验。
「一国两制」的功能序列是完整和深刻的,递进展现为和平统一、经济现代化、制度现代化与永久和平,以非冷战的和平发展方式超越西方冷战思维与冷战体系,尝试给出中国对人类道德自治与制度合作的样板方案。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
「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而香港始终是最佳的实验平台和信心来源,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及塑造新型全球化的重要战略与制度杠杆,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共生的实践动力。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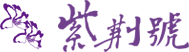








 查看更多
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