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荆论坛》专稿/转载请标明出处
刘兆佳 |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
当前,美国联合盟友不断打压遏制中国。但实际上,许多国家并不愿选边站队,既想利用美国为其提供的安全保证,又想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以此谋求自身发展。然而,随著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国内孤立主义盛行,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对其所作的安全承诺感到信心不足,而对中国可提供的经济发展机遇信心上升。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中美两国具有不同国际竞争优势
当前美中两国正处于激烈的遏制与反遏制斗争之中,双方都不遗余力争取盟友、伙伴和朋友来加强自己的实力。长期以来,美国自认为在这方面比中国拥有较明显的优势,并相信在建构盟友网络上中国将会永久处于下风。美国确与不少国家构建了军事同盟,包括北约、美日同盟等,以及「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日印澳安全对话」(QUAD)等准军事同盟,并为其提供武器和情报。美国与英国名义上虽非同盟国,但实质上胜似同盟国。此外,美国也向不少国家尤其是部分中东国家如巴林、卡塔尔提供安全保证。相反,在「结伴而不结盟」和「独立自主外交」的方针下,中国没有与任何国家构建军事同盟,但与少数国家比如俄罗斯、朝鲜和部分中亚国家维持密切的军事或安全上的合作。有趣的是,尽管中国基本上没有为任何国家的外部安全作出「正式」承诺,但不少国家主要是非西方国家在维护其内部安全上仍与中国有不同程度的合作,尤其在维持治安、反恐、反分离主义、反极端主义、反暴乱和粉碎「颜色革命」等方面。
经济领域情况则截然不同。目前中国是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的首要贸易伙伴,而以美国为首要贸易伙伴的则只有墨西哥、加拿大等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中国进行合作的国家远比与美国合作的国家多。在投资、对外援助和科技领域,中美之间的差距也正在日渐缩小。
不少西方和中国的战略学者倾向于认为在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上,美国的优势是能够为其盟友、伙伴提供安全保证,而中国的优势则在于能够为其伙伴带来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条件。这种论述无疑过于简单,但不无道理。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多年前曾经向我讲过这个观点。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客座教授希娜.C.格雷滕斯(Sheena Chestnut Greitens)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兼任教授艾萨克.卡登(Isaac Kardon)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的文章中语带挖苦地表示:「美国加强外部安全,在军事上保护其伙伴免受区域威胁。中国提供内部安全,为政府提供打击社会混乱和政治反对派的工具。」「美国的主要任务是区域安全:它保护盟友和伙伴免受邻国的威胁,提供广泛的核威慑,打击跨国恐怖组织,并让它们极度依赖美国在高端军事能力方面的优势。华盛顿透过共同防御条约和其他双边安全伙伴关系建立了一个盟友网络,以应对和平与稳定的挑战,包括中国和朝鲜在东亚,伊朗在中东以及俄罗斯在欧洲构成的威胁。」「中国为外国政府提供国内和政权安全。透过在数码监控、警察培训和防暴管理等执法和公共安全措施方面的合作,北京帮助其合作伙伴维持对国内的控制。」
为了遏制中国,美国不断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见顶论」「中国崩溃论」「中国产能过剩论」「大国角力论」「民主和威权决战论」「新冷战论」等,以及利用中国与个别东南亚国家在南海的领海争端和中印的边境纠纷,挑拨和破坏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不过,美国的如意算盘没有打响。绝大部分国家在争取美国安全保证的同时,希望与中国和美国均保持良好关系,特别是在经贸方面,它们不愿意选边站队。印太地区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在这方面的立场尤其明显。2023年5月,史汀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凯利.A.格里科(Kelly A. Grieco)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詹妮弗.卡瓦纳(Jennifer Kavanagh)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文章中说:「(印太)地区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某些行为表示日益担忧,特别是北京在南海的侵略行为和不尊重国际准则的行为。同时,许多国家既不认同美国对中国威胁的看法,也不认同拜登政府将世界分为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的简化愿景。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协助建立了基于互利合作的区域秩序,其成员国和太平洋岛国欢迎中国为经济成长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即使美国及其民主盟友设法兑现『人人享有可持续发展』的承诺,但无论拜登访问多少次、访问多久,它们也不太可能放弃深化与中国在该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在这种地缘政治背景下,美国的影响力比它想像的还要小。从泰国和韩国等条约盟友,到印度等日益密切的美国伙伴,再到越南等对美国交往持谨慎态度的国家,该地区国家正积极选择第三条道路。」「对他们来说,鉴于中国是它们的主要贸易伙伴和投资者,多边结盟是经济上的必然。但多方对齐也是它们在安全领域的首选。美国可能希望成为首选的安全伙伴,但该地区大多数国家不想要一个安全伙伴——它们选择了多个安全伙伴。」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保罗.斯坦尼兰(Paul Staniland)2024年5月在《外交事务》的文章中指出:「亚洲国家高度关注经济成长,它们将抓住机遇,在美中竞争中占据优势,例如与美国合作,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自己的市场。但这些努力可以与中国在其他经济议题上的合作同时进行。」不过,「过去十年来,一些亚洲国家——尤其是那些与中国存在陆地和海上争端的国家——一直在寻求与美国加强联系结盟。」「大多数亚洲国家都有很多需求。即使它们选择在一个领域与中国接触,美国及其合作伙伴也可以在其他领域推进其战略目标。」
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与中
保持紧密经济联系
展望将来,在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和认同上,中国的竞争优势将会逐渐超越美国,原因是对越来越多的国家来说,经济发展比安全保证重要得多,它们将会从中国获得越来越多且没有附带政治条件的经济发展机遇,尤其重要的是它们并不像美国般视中国为重大安全威胁。相反,美国所能给予其他国家的经济好处只会越来越少,特别是在投资和基础建设方面,然而美国仍然会要求那些受惠国家采纳西方的民主、人权、发展模式和开放市场来换取美国的支持。让不少受惠国家懊恼的是,美国要求它们支持和配合美国与中国为敌的立场。为了打击和抹黑中国,美国不断污蔑中国要在其他国家制造「债务陷阱」(debt trap)、宣扬威权主义价值观、破坏自然环境和进行政治渗透和控制。不过,美国这种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制造矛盾的伎俩没有得逞。更为重要的是,在提供安全保证上,美国的竞争优势正在不断下降。尽管当前世界并不太平,区域性冲突此起彼伏,但越来越多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保证的需求不断下降,认为美国的安全保证越来越不可靠, 甚至觉得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反而会给自己带来不安全。
在经济领域,中国的崛起和改革开放路线令中国在经济、贸易、科技和金融上与世界各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今天,绝大部分国家都把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视为第一要务,而这也是执政势力在政治上生死存亡的关键。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让很多国家得以从中国的发展中取得源源不绝的红利,因此参与的国家不断增加。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杰出研究员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2023 年 2 月在《外交事务》的文章中指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南半球,那里的大多数政府主要关心的是经济发展,不希望在北京和华盛顿的竞争中选边站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 2022 年 1 月生效,可能会在未来十年刺激经济成长更加显著地跳升。」「美国大力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但这场运动基本上失败了:所有十个东协国家都参与了各种『一带一路』项目,而且整个地区是最容易接受中国巨额基础设施投资的地区之一。」「美国根本没有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可行替代方案,因此不顾美国的反对而选择接受中国的倡议是很容易的。」「就像在东南亚一样,中国与非洲建立了更深层的经济关系。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警告非洲政府要警惕中国的剥削,但这种警告遭到了怀疑,尤其是西方有长期剥削非洲的痛苦记录。此外,经验证据表明,中国投资促进了经济成长,并在就业机会稀缺的非洲大陆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此外,由中国作为核心成员的金砖国家组织不断壮大,在全球经济所占比重媲美甚至超越G7(七国集团)。最近,泰国成为了第一个申请加入金砖国家组织的东南亚国家。身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也表示希望加入金砖国家组织。「一带一路」合作和金砖国家组织都让中国比美国在经济层面对世界各国更具有吸引力的竞争优势。
近年来,一个关键性的发展是,中东的产油国除了增加与中国的石油贸易外,也在中国进行规模越来越大的投资。据《中国日报》2024 年 2 月 23 日的报道:「中国曾经是中东的主要投资国,而美国一直是阿拉伯国家的主要投资目的地。然而,过去几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逐渐成为对这些国家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它们在中国的投资已经达到了与中国在中东的投资不相上下的水平。」「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动车、新能源、互联网、半导体、人工智能、智能基础设施、医药和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领域。」「阿拉伯国家投资的战略支点是摆脱对石油的依赖,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拥抱新兴国家和新兴市场。」
与此同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外主义、逆全球化和「美国优先」等思想令美国在经济上走向闭关自守,却同时对外采取经济自私自利的「掠夺」手段和霸凌主义,不断蚕食或牺牲他国包括盟友的利益。事实上,今天的美国对于与其他国家缔结多边贸易协定或参与国际经贸组织的兴趣越来越低。正如悉尼美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布莱克.赫辛格(Blake Herzinger)2023年5月在《外交政策》的文章中所言:「尽管美国作为一个自由贸易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现在它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当今定义该地区的大多数贸易协定之外。从美国没有参加《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本质上是除去美国的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来看,美国并不参与亚洲贸易规则的制定。」令人叹息的是,美国对其主力创建的世界贸易组织(WTO)采取蔑视态度,不但屡屡违反其规则,比如单方面向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肆意大加关税,而且恶意瘫痪其争议投诉机制,让WTO难以正常运作。美国战略学者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 2024年5月更在《外交事务》的文章中称, 如果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在经济上,『美国优先』策略将以保护主义和掠夺为特征。」「美国将对盟友和对手采取更强硬的胁迫措施。」诚然,美国总统拜登试图通过其倡议的「印太经济框架」来拉拢其他国家,但拒绝为它们开放美国市场,此举从而徒劳无功。
盟友对美国的安全承诺产生动摇
在提供安全保证上,越来越多国家对美国所能提供的安全承诺信心产生动摇。美国自己也知道不少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保证的信任度不高。三名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美国战略学者卡特琳.弗雷泽.卡茨 (Katrin Fraser Katz)、克里斯托弗.约翰斯通(Christopher Johnstone)和维克多.查(Victor Cha)2023 年2 月在《外交事务》的文章中指出:「美国会履行承诺,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美国全部能力来威慑并在必要时击败对其盟友领土和主权的外部攻击吗?」「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维持外部威慑承诺的可信度也是一个挑战。这样做需要让盟友相信,美国不仅有能力阻止和防御针对他们的潜在攻击,而且有意愿使用这些能力——即使这意味着将美国城市置于危险之中。这本质上是一项困难的努力,因此盟国对延伸威慑的怀疑是可以预见的,也是正常的。」「日本和韩国都担心俄罗斯对欧洲的侵略会分散美国对亚洲迅速演变的一系列安全挑战的注意力。」「亚洲盟友对美国自身的事态发展感到担忧。它们特别担心未来的美国政府可能会降低联盟的重要性,就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执政期间所做的那样。东京和首尔都关注美国政治中挥之不去的『美国优先』思想,并想知道华盛顿是否会继续致力于保护它们。」
与此同时,美国也深知自身国力相对于中国不断下降,因此越来越要求盟友和伙伴分担维护安全的费用,这更让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心存疑虑和抗拒。史汀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凯利.A.格里科 (Kelly A. Grieco)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詹妮弗.卡瓦纳(Jennifer Kavanagh) 2024年1月在《外交事务》的文章中表示:「当认识到维持美国在维持(印太)地区军事主导地位的代价在政治上和实际上都变得不可持续后,拜登团队寻求建立一个盟友和合作伙伴联盟来支付部分成本。」「该地区很少有国家愿意完全倒向美国主导的安全架构,而这种架构要求它们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坚称,它并不寻求建立一个地区安全集团,但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都抵制了华盛顿这样做的尝试。」
欧洲国家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但它们对美国的安全保证的信心也在动摇。西班牙前外交部长阿兰查.冈萨雷斯.拉亚 (Arancha González Laya)等人2024年2月在《外交事务》的文章中称:「欧洲领导人不能指望一个友好的美国。」「早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欧洲领导人就知道他们必须成长——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无论谁掌权(美国),欧洲都可能根本无法再依赖美国作为坚定的合作伙伴。美国已经在没有咨询欧洲的情况下就采取了外交政策举措,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英国的民调机构YouGov于2024年4月8日至15日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展开调查,发现只有6%的被访者认为美国未来10年在保障欧洲的安全上「非常可靠」,而持这个态度的美国被访者虽然较多,但仍只有24%。
如果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克兰的承诺越来越无法兑现,则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保证也会失去信心。以台湾为例,达米.恩凯夫(Damien Cave)和张健.艾米(Amy Chang Chien)2024年1月22日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中说:「当(台湾民众)看到华盛顿在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军事援助上陷入僵局,并试图想象美国在危机中实际上会为台湾做什么时,对美国的信心正在直线下降。一项台湾民调显示,只有 34%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值得信赖的国家,这一比例低于 2021 年的 45%。」
近年来,美国的「孤立主义」在共和与民主两党及美国社会都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要求美国推行「紧缩」政策(retrenchment policy), 即减少介入外国事务和对外国的承担呼声也在上升,这让美国盟友和伙伴对其提供的安全保证的信心进一步下坠。《外交政策》专栏作家麦可.赫什(Michael Hirsh)2023 年 11 月表示:「美国自建国以来其实一直是个孤立主义国家,特别是为了避免卷入外国战争。与它的整个历史相比,它的战后全球领导作用——近八年来伴随着我们成长的角色——实际上是一种反常现象,而不是常态。」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蒂芬.韦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2024年2月在《外交事务》的文章中提出忠告:「展望未来,(美国的)选择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可以选择性地紧缩开支并控制成本和风险,或者坚持全球主导地位并在危机中陷入困境。」「如果美国真的想根据自己的利益确定优先事项——换句话说,采取战略行动——除了从不那么重要的地方撤军之外,没有其他可行的选择。」「这意味着系统性地使美国与中东脱钩,将大部分欧洲防务负担转移给欧洲盟友,并努力与中国建立竞争性共存,以便在美国继续发展的同时,使两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稳定。」「美国不需要全球军事主导地位来实现繁荣。我们必须做的是拯救其自由民主,重建其政党政治,并恢复人民的信心。」哈尔.布兰兹也警告:「对美国全球主义关键方面的厌倦已成为两党共同的事情。世界可能会面临一个始终奉行『美国优先』的超级大国。」「华盛顿不会继续保卫遥远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生存对美国的安全显然并不重要,美国也不会继续提供主要被其他国家消费的公共产品。」「华盛顿至少不会将其联盟视为战略血誓,而是视为永远适合重新谈判的讨价还价。 ……或者华盛顿可能会简单地退出其联盟,将欧亚大陆留给欧亚人。」
国际社会期待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
与安全发挥更大作用
由于不少盟友和伙伴对美国的安全保证的信心越来越低,它们不得不积极寻找其他办法来维护自身的安全。在欧洲,法国和德国等国家增加了国防开支,并谋求建立北约以外的欧洲军事力量。这一趋势在战乱频仍的中东尤为明显,特别是在巴以冲突爆发后。阿拉伯国家虽然在安全上对美国仍有依赖,但它们已经明白,那个坚持容许以色列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暴行和坚持与伊朗为敌的美国并不具备在中东建构持久和平的资格。巴以冲突一方面令阿拉伯国家走向团结,另一方面缓和并改善了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的关系,同时还强化了伊斯兰世界国家在安全上的合作。在对美国和以色列失望和愤慨的同时,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正在一起积极探索达至中东永久和平的方案,当中尤其重要的一环是要让巴勒斯坦人民按照联合国的决议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质言之,中东国家已经不指望美国能够为自己带来和平,因此必须更多地依靠彼此的合作。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达莉亚.达萨.凯伊(Dalia Dassa Kaye)和查塔姆研究所研究员萨南.瓦基尔(Sanam Vakil) 在《外交事务》的文章中提出:「等待美国带头有效管理加沙并实现持久的中东和平就像等待戈多:当前的地区和全球动态使华盛顿很难发挥主导作用。」「任何对华盛顿能够达成最终结束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大协议的期望都脱离了当今中东的现实。最终,重大外交突破最有可能来自并取决于该地区本身。」「事实上,从 2019 年开始,该地区各国政府开始修复先前紧张的关系。」「尽管加沙战争将巴勒斯坦问题推回到国际议程的前沿,但它也凸显了整个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重要的新政治动态。一方面,美国的影响力似乎较小。但同时,区域大国包括那些先前存在分歧的国家,正在主动出击、参与调解,并协调各自的政策反应。」
除了越来越不能兑现对盟友和伙伴的安全保证外,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对外政策往往还为其盟友和伙伴带来不安全。美国罔顾俄罗斯的安危,并在部分欧洲大国有所保留的情况下悍然推动北约东扩,导致了俄乌冲突和欧洲国家的不安全。相反,近年来,随着国际影响力急速上升,中国积极承担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越来越多国家亦希望中国在维护世界与地区和平上发挥重要作用。国际上希望中国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和中东和平上扮演更主动和积极角色的呼声日益高涨。事实上,越来越多阿拉伯国家愿意与中国在安全事务上加强合作。可以说,在为其他国家提供外部安全保证上,美国虽然比中国仍较具优势,但中国的优势也正在持续增加。
总的来说,在争取世界各国的支持上,中国不但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的经济发展机遇,也能够为世界和地区和平作出更多贡献。美国不但不能够孤立中国,反而自己在国际上愈趋被孤立,尤其因为盲目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残酷杀戮而深陷道德危机并备受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4年5-6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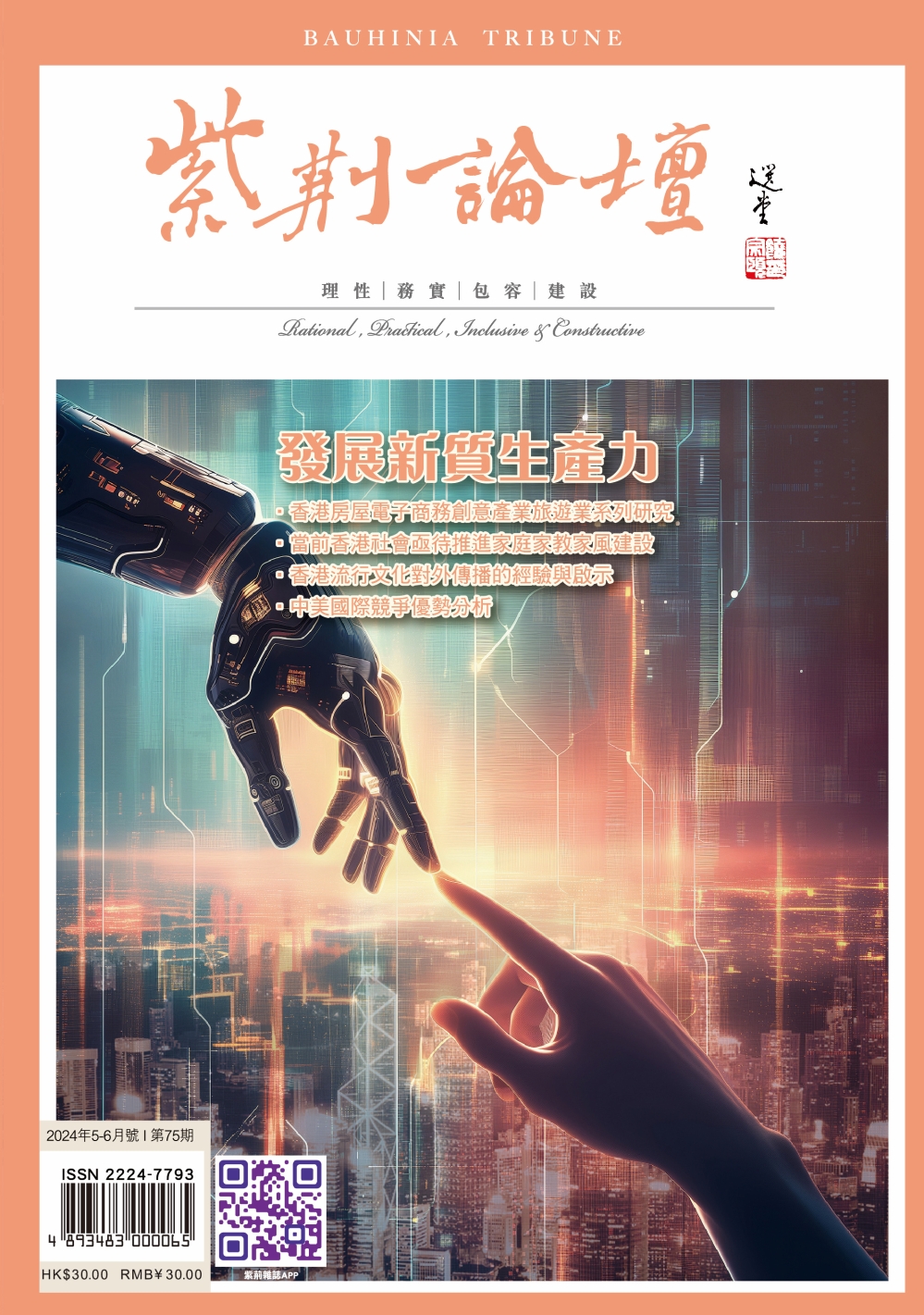











扫描二维码分享到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