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荆论坛》专稿/转载请标明出处
潘毅 |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教授
香港的青年发展问题近年备受关注,置业难、就业难、失业问题,乃至「躺平」等问题经常被捆绑讨论。然而,过于笼统的批评无助我们理解问题,我们需要分析社会文化背后的结构性成因,才可以提出适切的政策建议,增加青年的「获得感」,响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青年兴,则香港兴;青年发展,则香港发展;青年有未来,则香港有未来」的号召。因此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及发展中心之前就青年的贫穷和收入问题、工作状况等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并就相关政策提出倡议,本文将会分享当中一些重点。
被忽略的青年劳工身份
所谓青年,其背后综合了很多社会身份,包括学生、劳工、创业人士等。我们认为社会在讨论青年问题时,往往忽略青年作为劳工的身份。我们的研究所接触的年轻人,大多反映工时长以致过劳、工资低或追不上生活成本,加上他们大部分不在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内,也感受不到政府推出的青年政策对他们有什么帮助。
进一步说,我们在2023年下半年所接触的青年中,有大约四成的受访者自认贫穷。他们对于贫穷有多元化的理解:有青年认为三餐不继才算得上是贫穷,有些人觉得人工未达到港人月入中位数就算是贫穷,亦有人认为很多目标未能达成,导致「精神贫穷」。其余自觉不贫穷的青年部分归因于家庭支援,可以满足基本需求以外的消费,例如购物和旅游。
另外,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推算,受访青年要满足现时的生活开支水平,时薪应该要达到71.6港元。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青年的个人月均生活开支,在扣除教育开支后,约为14,894港元,按一个月工作26日,每日8小时计算出时薪水平为71.6港元,与目前最低工资水平相距很远。
工时方面,青年的不固定和长时间工作情况普遍。就问卷所得,受访青年的平均每周工时为43.11小时。近6成受访青年指雇主没有提供任何超时工作补贴,约3成指雇主会提供津贴或补假。而在36个深入访问中得知,受访青年平均每周工时为46.67小时。
从上述发现可见,青年的贫穷、低工资、长工时的问题并非空穴来风:他们的困境既是整体贫穷和劳工保障不足问题的一部分,亦有其特点。更宏观来说,据扶贫委员会最新的《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贫穷青年人口连升5年,三成介乎25-29岁的青年属在职贫穷,当中逾半拥专上学历。即使自新冠疫情退去,15-19岁及20-29岁的青年失业率逐步回落,然而与疫情前的水平尚有差距。换句话说,即使疫情过去,社会恢复平静,置业难、失业等问题依然存在。
总体而言,工资、工时政策的保障不足,与青年的疲劳和失望的状态有明显关系,然而政府和各方倡议的青年政策大多围绕教育、创业、置业等方向,忽略了青年作为劳工所需的保障和期望。
教育和就业问题需要一同审视 ——以影视业为例
特区政府已经意识到青年问题的重要性及复杂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所提出的青年发展蓝图便是以跨政策局的思维,试图在学业、就业、创业及置业这「四业」上为年轻人开拓出路。这四个范畴不是割裂的问题,而是紧密相连的,例如以我们研究的创意产业内的影视业为例,当中的高度零散化的工作模式,以及职业安全隐患,自然会影响青年在这个行业的发展,也会对有兴趣投身于此的大专和大学毕业生造成不良观感,留不住好的人才,会窒碍新产业的发展,加剧产业单一化的问题。
更深入一点说,以我们研究的影视业为例,文化及创意产业是近年香港政府重点发展的产业,锐意将香港打造成「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而根据「创意香港」办公室的数据,自2013/14学年至2019/20学年的七个学年期间,修读「广告」「电影及电视」课程的毕业生均超过2,000人,在整体创意产业课程范畴毕业生中稳占超过 30%,占全港总毕业生人数约4%。足见有稳定数量的年轻人有意投身影视创作,亦是创意产业未来的中坚力量。
然而影视业普遍的外判制度导致工作零散,容易延迟支付酬劳(即「拖粮」)。我们收集的问卷显示,有42.3%回复问卷的从业员表示在现时或上一份工作,开工前仅有口头或讯息协议,14.6%回复者则在开工前没有任何形式的协议。
同时,影视业从业员的劳动强度普遍较高,过劳和工伤均普遍,但甚少有适当处理。超过六成回复者表示「颇多」或「经常」连续两天工作12小时以上;76.4%回复者表示试过或目睹工伤,不过,只有11.7%的回复者表示有向劳工处呈报工伤。
每个行业的用工模式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就影视业来说,经历上世纪九十年代港产制作大幅萎缩的情况,投资商须紧缩制作成本预算,改以承包或自由工作方式聘用劳工,导致从业员缺乏正式雇佣关系和相关劳工保障。零散化的劳动模式亦造成普遍的不合理待遇,包括「拖粮」、欠缺清晰的工作协议内容和工时安排等。
不过有独特的劳动模式不等于可以忽略从业员的待遇和安全问题。从业员的公平待遇和获得感正是行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如何在行业需要和从业员保障间取得平衡,十分考验政府和行业领袖的魄力。就目前来看,政府透过半官方机构,例如电影发展局,专门管理行业的政策、发展策略、资助及人才培训等事宜,虽然对于香港本地电影发展有很大帮助,不同的资助计划近年更发掘了不少得奖人才和作品,不过对于行内,尤其是前线从业员、新毕业新人等的关注却并未足够。举例而言,我们透过对从业员的访谈发现,他们面对上述安全、「拖粮」或其他不合理待遇时,大多数情况只能不了了之,并对于缺乏一个可信赖的投诉或举报渠道的现状表示无奈。
另一方面,影视业的独特状况,例如非恒常的工作地点、高度细致和专业的分工模式,都使以往的监管方式难以「照板煮碗」,比如说主要创作岗位,即导演、编剧,与前线的机械操作人员、道具、化妆等专业人士,两者面对的问题和需要的保障都不同。加上普遍的外判制导致大量的小型独立制作公司出现,以少至数人的小团队方式承包了市场上大部分的短片、宣传片、广告的制作需求,层层的外判导致他们更难追讨待遇问题。以上种种具体状况都冲击著现时劳工法例对雇员、自雇人士的定义。
因此,除了访问从业员,我们也同一些行业领袖交流,提出「订立从业员基本待遇守则」「订立工业安全指引」等倡议,并持续完善这些构想。我们认为,在政策层面上,政府和行业领袖合力,订立合理的待遇和安全标准,并由政府带头规定受资助团体或个人以不亚于行业标准合约的待遇聘请制作人员,可以逐步影响至整个行业,实际解决问题。这个做法对于其他创意产业或牵涉大量自由工作者的行业,或许亦有一定参考意义。
结语
目前为止,我们的研究只能反映青年的一部分面貌,所以仍然需要深入研究不同行业,尤其是新兴产业的工作状况,和从业者不同的在职贫穷成因乃至他们的消费、文化等方面。可以说,社会目前所讲的「青年发展问题」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问题,一方面,旧的问题例如劳工保障不足,在新一代眼中依然存在,并以新的方式在新兴产业中重现;另一方面,青年对于非传统就业的向往、不断变化的劳动模式,亦产生新的问题。
要营造一个让青年可以自由发挥潜能的社会,我们始终要聆听青年的声音,提供更多机会予青年一代去发言及直接参与政策决策。政府、雇主、工会等各组织需要建立合适渠道,让青年劳工得以有意义地参与政策、职场和行业协定的商讨和决策过程。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4年1-2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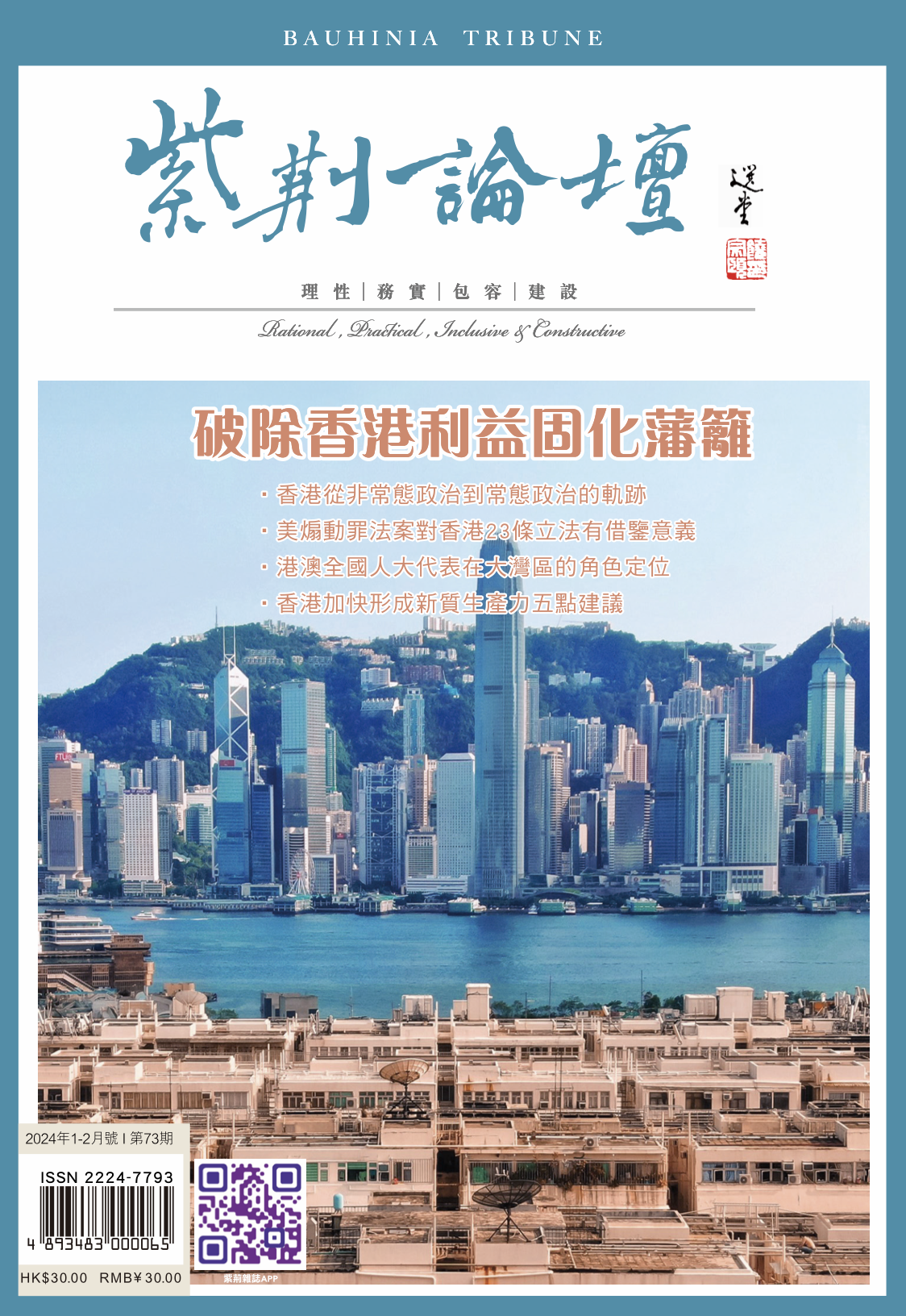
https://res.youuu.com/zjres/2023/11/28/zh4eP8EMTpqXAFC9ZeEog5YbsVmqMdkBhLX.png











扫描二维码分享到手机
![]()
+关注
《紫荆论坛》专稿/转载请标明出处
潘毅 |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教授
香港的青年发展问题近年备受关注,置业难、就业难、失业问题,乃至「躺平」等问题经常被捆绑讨论。然而,过于笼统的批评无助我们理解问题,我们需要分析社会文化背后的结构性成因,才可以提出适切的政策建议,增加青年的「获得感」,响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青年兴,则香港兴;青年发展,则香港发展;青年有未来,则香港有未来」的号召。因此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及发展中心之前就青年的贫穷和收入问题、工作状况等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并就相关政策提出倡议,本文将会分享当中一些重点。
被忽略的青年劳工身份
所谓青年,其背后综合了很多社会身份,包括学生、劳工、创业人士等。我们认为社会在讨论青年问题时,往往忽略青年作为劳工的身份。我们的研究所接触的年轻人,大多反映工时长以致过劳、工资低或追不上生活成本,加上他们大部分不在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内,也感受不到政府推出的青年政策对他们有什么帮助。
进一步说,我们在2023年下半年所接触的青年中,有大约四成的受访者自认贫穷。他们对于贫穷有多元化的理解:有青年认为三餐不继才算得上是贫穷,有些人觉得人工未达到港人月入中位数就算是贫穷,亦有人认为很多目标未能达成,导致「精神贫穷」。其余自觉不贫穷的青年部分归因于家庭支援,可以满足基本需求以外的消费,例如购物和旅游。
另外,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推算,受访青年要满足现时的生活开支水平,时薪应该要达到71.6港元。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青年的个人月均生活开支,在扣除教育开支后,约为14,894港元,按一个月工作26日,每日8小时计算出时薪水平为71.6港元,与目前最低工资水平相距很远。
工时方面,青年的不固定和长时间工作情况普遍。就问卷所得,受访青年的平均每周工时为43.11小时。近6成受访青年指雇主没有提供任何超时工作补贴,约3成指雇主会提供津贴或补假。而在36个深入访问中得知,受访青年平均每周工时为46.67小时。
从上述发现可见,青年的贫穷、低工资、长工时的问题并非空穴来风:他们的困境既是整体贫穷和劳工保障不足问题的一部分,亦有其特点。更宏观来说,据扶贫委员会最新的《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贫穷青年人口连升5年,三成介乎25-29岁的青年属在职贫穷,当中逾半拥专上学历。即使自新冠疫情退去,15-19岁及20-29岁的青年失业率逐步回落,然而与疫情前的水平尚有差距。换句话说,即使疫情过去,社会恢复平静,置业难、失业等问题依然存在。
总体而言,工资、工时政策的保障不足,与青年的疲劳和失望的状态有明显关系,然而政府和各方倡议的青年政策大多围绕教育、创业、置业等方向,忽略了青年作为劳工所需的保障和期望。
教育和就业问题需要一同审视 ——以影视业为例
特区政府已经意识到青年问题的重要性及复杂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所提出的青年发展蓝图便是以跨政策局的思维,试图在学业、就业、创业及置业这「四业」上为年轻人开拓出路。这四个范畴不是割裂的问题,而是紧密相连的,例如以我们研究的创意产业内的影视业为例,当中的高度零散化的工作模式,以及职业安全隐患,自然会影响青年在这个行业的发展,也会对有兴趣投身于此的大专和大学毕业生造成不良观感,留不住好的人才,会窒碍新产业的发展,加剧产业单一化的问题。
更深入一点说,以我们研究的影视业为例,文化及创意产业是近年香港政府重点发展的产业,锐意将香港打造成「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而根据「创意香港」办公室的数据,自2013/14学年至2019/20学年的七个学年期间,修读「广告」「电影及电视」课程的毕业生均超过2,000人,在整体创意产业课程范畴毕业生中稳占超过 30%,占全港总毕业生人数约4%。足见有稳定数量的年轻人有意投身影视创作,亦是创意产业未来的中坚力量。
然而影视业普遍的外判制度导致工作零散,容易延迟支付酬劳(即「拖粮」)。我们收集的问卷显示,有42.3%回复问卷的从业员表示在现时或上一份工作,开工前仅有口头或讯息协议,14.6%回复者则在开工前没有任何形式的协议。
同时,影视业从业员的劳动强度普遍较高,过劳和工伤均普遍,但甚少有适当处理。超过六成回复者表示「颇多」或「经常」连续两天工作12小时以上;76.4%回复者表示试过或目睹工伤,不过,只有11.7%的回复者表示有向劳工处呈报工伤。
每个行业的用工模式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就影视业来说,经历上世纪九十年代港产制作大幅萎缩的情况,投资商须紧缩制作成本预算,改以承包或自由工作方式聘用劳工,导致从业员缺乏正式雇佣关系和相关劳工保障。零散化的劳动模式亦造成普遍的不合理待遇,包括「拖粮」、欠缺清晰的工作协议内容和工时安排等。
不过有独特的劳动模式不等于可以忽略从业员的待遇和安全问题。从业员的公平待遇和获得感正是行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如何在行业需要和从业员保障间取得平衡,十分考验政府和行业领袖的魄力。就目前来看,政府透过半官方机构,例如电影发展局,专门管理行业的政策、发展策略、资助及人才培训等事宜,虽然对于香港本地电影发展有很大帮助,不同的资助计划近年更发掘了不少得奖人才和作品,不过对于行内,尤其是前线从业员、新毕业新人等的关注却并未足够。举例而言,我们透过对从业员的访谈发现,他们面对上述安全、「拖粮」或其他不合理待遇时,大多数情况只能不了了之,并对于缺乏一个可信赖的投诉或举报渠道的现状表示无奈。
另一方面,影视业的独特状况,例如非恒常的工作地点、高度细致和专业的分工模式,都使以往的监管方式难以「照板煮碗」,比如说主要创作岗位,即导演、编剧,与前线的机械操作人员、道具、化妆等专业人士,两者面对的问题和需要的保障都不同。加上普遍的外判制导致大量的小型独立制作公司出现,以少至数人的小团队方式承包了市场上大部分的短片、宣传片、广告的制作需求,层层的外判导致他们更难追讨待遇问题。以上种种具体状况都冲击著现时劳工法例对雇员、自雇人士的定义。
因此,除了访问从业员,我们也同一些行业领袖交流,提出「订立从业员基本待遇守则」「订立工业安全指引」等倡议,并持续完善这些构想。我们认为,在政策层面上,政府和行业领袖合力,订立合理的待遇和安全标准,并由政府带头规定受资助团体或个人以不亚于行业标准合约的待遇聘请制作人员,可以逐步影响至整个行业,实际解决问题。这个做法对于其他创意产业或牵涉大量自由工作者的行业,或许亦有一定参考意义。
结语
目前为止,我们的研究只能反映青年的一部分面貌,所以仍然需要深入研究不同行业,尤其是新兴产业的工作状况,和从业者不同的在职贫穷成因乃至他们的消费、文化等方面。可以说,社会目前所讲的「青年发展问题」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问题,一方面,旧的问题例如劳工保障不足,在新一代眼中依然存在,并以新的方式在新兴产业中重现;另一方面,青年对于非传统就业的向往、不断变化的劳动模式,亦产生新的问题。
要营造一个让青年可以自由发挥潜能的社会,我们始终要聆听青年的声音,提供更多机会予青年一代去发言及直接参与政策决策。政府、雇主、工会等各组织需要建立合适渠道,让青年劳工得以有意义地参与政策、职场和行业协定的商讨和决策过程。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4年1-2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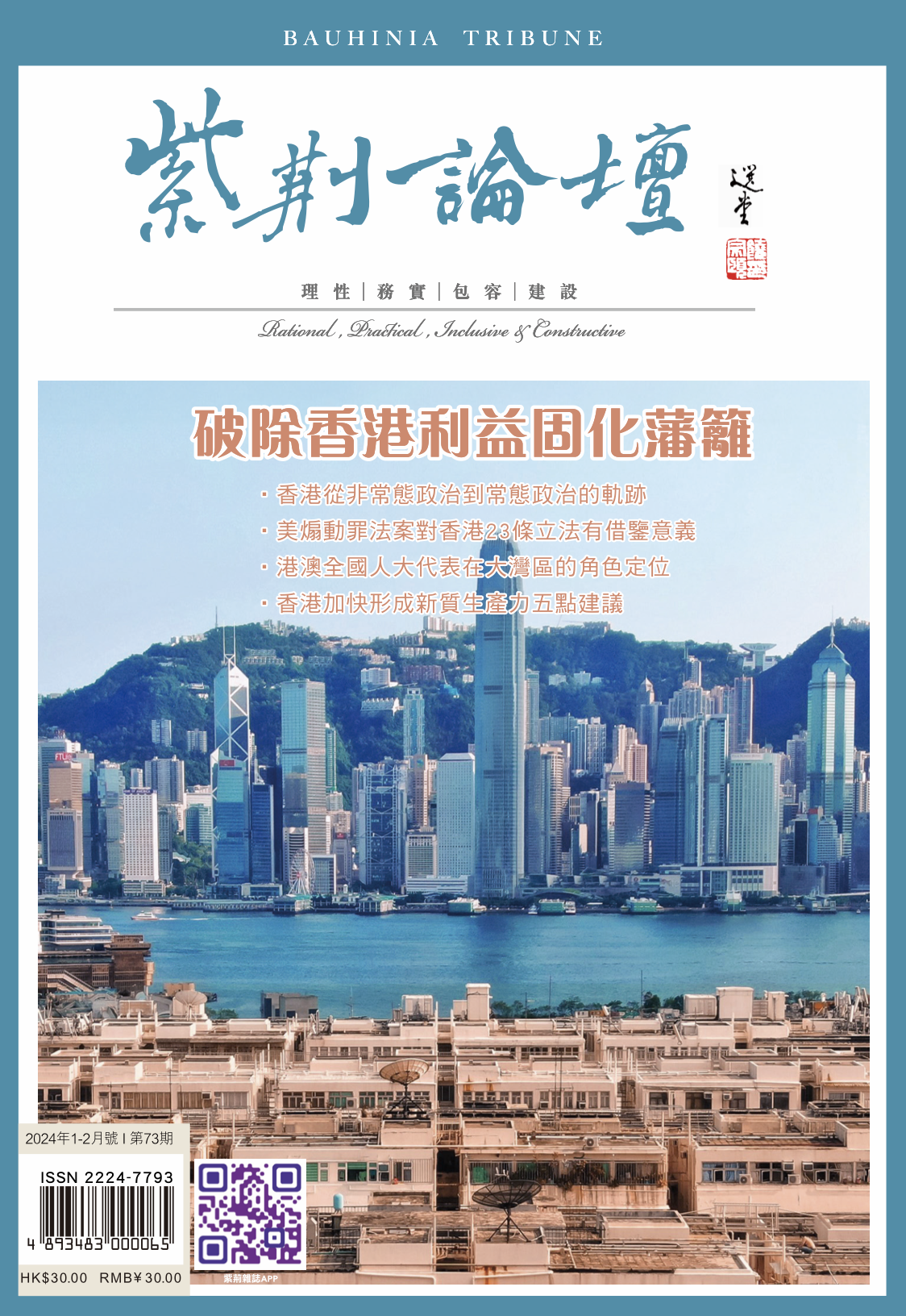
https://res.youuu.com/zjres/2023/11/28/zh4eP8EMTpqXAFC9ZeEog5YbsVmqMdkBhLX.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