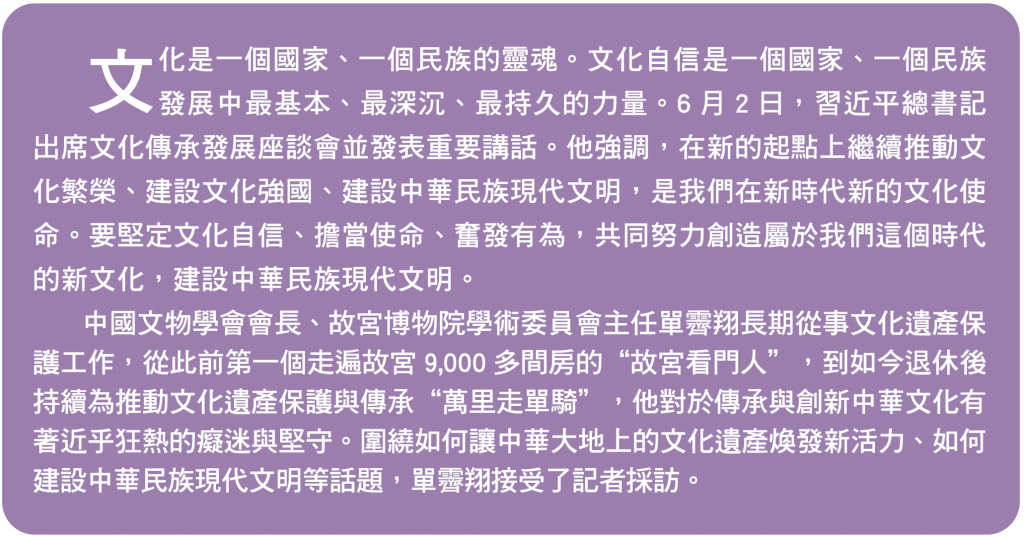
文| 本刊记者 冯琳

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
记者:您被大众熟知是因为曾掌管故宫博物院,实际上您对文化遗产有著广泛且深刻的研究。您如何评价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情况?
单霁翔:我是1994年开始在北京市文物局工作,后来又在国家文物局工作了10年,最后退休前到了故宫博物院。我长期在文化遗产保护行业中工作,深刻感受到,对于文化遗产来说,保护并不是目的,利用也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传承,传承的对象是当代和未来。
过去我们经常把文物保护看作专业的、部门的、行业的工作,保护对象多是古代的、静态的、单体的、物质的内容,但是今天慢慢我们把这个思路放开了,开始研究国土空间里五千年文明所传承下的内容。过去一直有人质疑,你们中国不就三千年文明吗?所谓五千年文明早期是否只是传说?事实上,十几年来中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者通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中华大地上,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同时从东北辽河流域到南方珠江流域,已经“满天星斗”般地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在一些领域推进到八千年、一万年。
我国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诞生13年以后,于1985年才加入公约。1987年我国有了第一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六项世界文化遗产,包括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秦始皇陵及兵马俑、故宫、敦煌莫高窟、泰山,开拓了文化遗产保护的视野。但是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在中国得到进一步普及,是2004年在中国苏州召开的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我们和文化遗产领域的国际组织有了更密切的沟通,也把过去局限于“文物保护”的理解,推进到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层面。例如这些年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包括澳门历史城区、殷墟、开平碉楼与村落、福建土楼、五台山、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元上都遗址、哈尼梯田、大运河、丝绸之路、土司遗址、花山岩画、良渚古城遗址等,都拓宽了我们文化遗产保护的眼界。
近十年来,人们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解和研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真正从“文物保护”走向了“文化遗产保护”。
记者:“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我们应怎样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单霁翔:当我们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我们的视野逐渐扩大,保护理念不断更新。例如过去文物保护重视单一文化要素,而文化遗产保护还要注重文化要素和自然要素共同生成的文化景观。过去文物保护的对象往往是静态的,比如古墓藏、石窟寺等,它们已经失去最初功能,今天只是被研究和观赏的对象,而文化遗产保护还要注意活态的、动态的内容,例如人们居住其中的历史街区、传统村落、民族村寨等。文物保护注重保护古代遗存,这当然是重要的内容,但是文化遗产保护还要注重保护近代的、当代的、20世纪的文化遗产,因为历史的链条不能断裂。过去文物保护的内容往往是单体的、小规模的内容,后来扩大到历史街区、历史文化名城,由点及面,但是文化遗产保护扩大到线形文化遗产、文化廊道,例如丝绸之路、大运河。过去文物保护注重保护宫殿建筑、寺庙建筑、纪念性建筑,现在还要注重保护那些普通民众生活的传统民居、乡土建筑、工业遗产、商业老字号。过去文物保护的对象是物质遗产,而文化遗产保护还要同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互为表里,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保护理念也发生了转变,特别强调世代传承性和公众参与性。
世代传承性,表明文物保护是一个历史过程,每一代人都有不可推脱的时代责任,任何世代都不能利用现实的优势随意处置文化遗产,因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也有保护、传承和享用的权利。
公众参与性,表明文化遗产保护不是政府的专利,更不是文物部门的专利,而是全民的事业,每个人都有保护文化遗产的权利,也都有保护文化遗产的义务。要更多地把文化遗产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赋予一般民众,这样文化遗产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尤其是今天那么多宏阔的文化遗产,像大运河、丝绸之路串联起众多区域、城市的文化遗产,仅依靠文物部门的力量肯定不够,必须要通过教育、宣传、展示,才能使更多民众热爱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才能得到真正地、更好地保护。

不同文明应开放互鉴共同发展
记者:中国如今已是拥有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在此背景下,您认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更好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单霁翔:我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时经常接待外国来宾,我经常会对他们讲“你瞧故宫的景色,红墙、黄瓦、蓝天,这是三原色,用这三种颜色可以谱画出世界任何的色彩”。我们的世界应该是绚丽多彩的,不能是单一色彩的,每个民族都有他们值得骄傲的历史,每个民族也都应该拥有他们向往的未来。
人类文化是多元的,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应该开放互鉴、共同发展。因此我们要增进相互了解,只有通过相互了解,才能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我们既要了解世界,也要让世界了解我们,所以要“走出去”,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还有一个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途径是申报世界遗产。世界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严格程序加以认定,每一项世界遗产都应该具有世界意义的“突出普遍价值”。这样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价值超越了民族和国家,成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在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委托遗产专家进行考察,还会在世界遗产大会上集体评议,通过后才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所以积极参与世界遗产事业,就能得到全世界的关注,就可以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博物馆应不断凝练强大的文化力量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您也一直倡导并努力实践让文物“活起来”,能分享一些经验和感受吗?
单霁翔:过去这些年,我们故宫博物院通过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践,获得了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什么才是好的文物保护状态?我认为不是把文物锁在库房里面,死看硬守就是好的文物保护状态,而是应该把这些文物藏品经过悉心地修复保养,让它保持健康的状态,让它们重新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在生活中感受到这些文物的魅力,才会精心地呵护这些文物,这些文物才有尊严,有尊严的文物,才能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才能惠及更广泛的人们的现实生活。
如何“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我们要继续思考,博物馆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更多的场所,把文物藏品更多地展示出来,讲好文物的故事。故宫博物院启动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使更多的古建筑经过修缮后合理利用,而不是锁起来束之高阁。我认为,一座古建筑修缮以后,将其锁起来,则糟朽得更快,而越将其开放合理利用,经常进行维护,就会使古建筑更加健康。
记者:作为城市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您认为怎样才是一座好的博物馆?您对于博物馆建设有什么建议?
单霁翔: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也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什么是好的博物馆?一座好的博物馆不是盖上高大的馆舍,搞华丽的装修,而是要不断深挖藏品的内涵,凝练它的力量,不断举办人们喜欢的好的展览和活动,这样才能在人民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面前,让人们感受到博物馆对于自身生活的意义,人们休闲的时候才愿意走进博物馆。走进博物馆,人们才会流连忘返,不愿离开;人们回去之后还能再来的博物馆,才是一座好的博物馆。我想,这就是今天人民群众衡量一座博物馆的优劣好坏的标准。
今天,我们博物馆的观众主体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旅游团体为主,到现在以家庭为单位,博物馆也要应对这种趋势,把观众对博物馆参观的愿望和热情激发出来。今天的博物馆依然要通过数字技术,通过互联网技术,把博物馆的声音不断放大,让人们能够听到、感受到。要创造文化遗产保护的良性循环,就要尽可能地开放更多的区域,举办更多丰富多彩的展览,使各个年龄段,尤其是知识欲望很强的年轻人喜欢上博物馆,这样的博物馆才有后劲儿。我希望每一座博物馆都要不断研究人们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根据自己的文化资源,来凝练出强大的文化力量。
香港文化建设必然蓬勃发展
记者:您与香港的缘分与交往颇深,去年还出版了新著《人居香港:活化历史建筑》,您对香港有什么印象?
单霁翔:香港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际都会,但是香港并非“文化沙漠”。香港虽然地域面积不大,但是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汇地,有8,000多栋历史建筑,它们见证了香港城市发展,也承载了集体记忆。
2002至2019年,我先后在国家文物局和故宫博物院工作。这一时期因为工作需要,我曾十余次访问香港,实地考察香港的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感受香港历史建筑保护理念和实践的迅速发展。
香港政府开拓创新,探索出一条更具适应性和操作性的模式来保护和利用历史建筑。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而传播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香港经验和香港故事正是我写作《人居香港:活化历史建筑》的初衷。
在这本书中,我还回顾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从设想到选址、筹备,再到规划、建设的过程。故宫博物院与香港虽然相隔千里,但是有著很深的文化渊源。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有包括《中秋帖》《伯远帖》等重要文物经香港回归故宫博物院。事实上,很多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藏品都有著香港的烙印。1999年,故宫博物院启动了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陈启宗先生创建的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为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提供了全额经费的捐款;许荣茂先生慷慨出资1.3亿元人民币,使《丝路山水地图》“回家”;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慷慨捐赠35亿港元,资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馆舍建设……
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筹建之前,故宫博物院几乎每年都有不同主题的文物展览在香港的各博物馆展出。从宫廷文化到皇家生活,从书法绘画到家具器物,从清宫服饰到外国文物,香港市民得以从不同角度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华传统文化,展览均获得强烈反响。
最使我难忘的是香港民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情,同时香港各界人士助力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文化情怀也让我印象深刻。我接触到的香港人士,无论是文化官员,还是文化学者、博物馆同仁、社会企业家,他们不但拥有国际视野,而且了解国情,善用中西兼容的文化优势,这是香港助力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积极力量。
记者: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已建成运营一周年,您对香港未来的文化事业发展有何期待?
单霁翔: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建设,无疑是香港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件大事,既可以使故宫博物院得以践行中华文化传承的长远承诺,也可以使香港博物馆界增加一份文化自信,更可以为香港吸引更多海内外博物馆爱好者,提升香港成为拥有国际重量级博物馆的文化之都。我们希望借助博物馆的平台,通过文物展览这一直观的方式,向更多香港民众展示中华传统文化,向更多国际友人宣传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未来,我祝福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成为一座有温度、令人震撼、不虚此行的博物馆。让中华传统文化更好地走进700多万香港同胞、7,000多万大湾区居民和世界各国民众的生活中,让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增添一条文化桥梁和纽带,使“东方之珠”更添魅力。
香港背靠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祖国,在文化资源的获取上可谓近水楼台,再加上各方面的强大合力与积极推进,我相信未来香港的文化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必然呈现蓬勃发展的景象。
https://res.youuu.com/zjres/2023/6/27/aAA1CzVZyqX39ZjlZ4G4BavbOdkkm7kGuC5.png
扫描二维码分享到手机
![]()
+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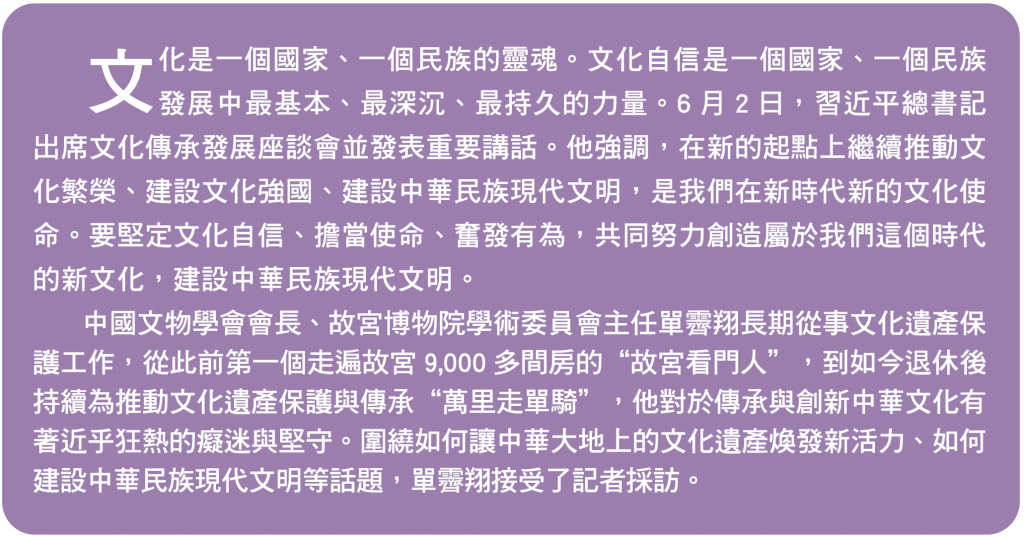
文| 本刊记者 冯琳

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
记者:您被大众熟知是因为曾掌管故宫博物院,实际上您对文化遗产有著广泛且深刻的研究。您如何评价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情况?
单霁翔:我是1994年开始在北京市文物局工作,后来又在国家文物局工作了10年,最后退休前到了故宫博物院。我长期在文化遗产保护行业中工作,深刻感受到,对于文化遗产来说,保护并不是目的,利用也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传承,传承的对象是当代和未来。
过去我们经常把文物保护看作专业的、部门的、行业的工作,保护对象多是古代的、静态的、单体的、物质的内容,但是今天慢慢我们把这个思路放开了,开始研究国土空间里五千年文明所传承下的内容。过去一直有人质疑,你们中国不就三千年文明吗?所谓五千年文明早期是否只是传说?事实上,十几年来中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者通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中华大地上,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同时从东北辽河流域到南方珠江流域,已经“满天星斗”般地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在一些领域推进到八千年、一万年。
我国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诞生13年以后,于1985年才加入公约。1987年我国有了第一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六项世界文化遗产,包括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秦始皇陵及兵马俑、故宫、敦煌莫高窟、泰山,开拓了文化遗产保护的视野。但是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在中国得到进一步普及,是2004年在中国苏州召开的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我们和文化遗产领域的国际组织有了更密切的沟通,也把过去局限于“文物保护”的理解,推进到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层面。例如这些年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包括澳门历史城区、殷墟、开平碉楼与村落、福建土楼、五台山、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元上都遗址、哈尼梯田、大运河、丝绸之路、土司遗址、花山岩画、良渚古城遗址等,都拓宽了我们文化遗产保护的眼界。
近十年来,人们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解和研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真正从“文物保护”走向了“文化遗产保护”。
记者:“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我们应怎样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单霁翔:当我们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我们的视野逐渐扩大,保护理念不断更新。例如过去文物保护重视单一文化要素,而文化遗产保护还要注重文化要素和自然要素共同生成的文化景观。过去文物保护的对象往往是静态的,比如古墓藏、石窟寺等,它们已经失去最初功能,今天只是被研究和观赏的对象,而文化遗产保护还要注意活态的、动态的内容,例如人们居住其中的历史街区、传统村落、民族村寨等。文物保护注重保护古代遗存,这当然是重要的内容,但是文化遗产保护还要注重保护近代的、当代的、20世纪的文化遗产,因为历史的链条不能断裂。过去文物保护的内容往往是单体的、小规模的内容,后来扩大到历史街区、历史文化名城,由点及面,但是文化遗产保护扩大到线形文化遗产、文化廊道,例如丝绸之路、大运河。过去文物保护注重保护宫殿建筑、寺庙建筑、纪念性建筑,现在还要注重保护那些普通民众生活的传统民居、乡土建筑、工业遗产、商业老字号。过去文物保护的对象是物质遗产,而文化遗产保护还要同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互为表里,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保护理念也发生了转变,特别强调世代传承性和公众参与性。
世代传承性,表明文物保护是一个历史过程,每一代人都有不可推脱的时代责任,任何世代都不能利用现实的优势随意处置文化遗产,因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也有保护、传承和享用的权利。
公众参与性,表明文化遗产保护不是政府的专利,更不是文物部门的专利,而是全民的事业,每个人都有保护文化遗产的权利,也都有保护文化遗产的义务。要更多地把文化遗产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赋予一般民众,这样文化遗产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尤其是今天那么多宏阔的文化遗产,像大运河、丝绸之路串联起众多区域、城市的文化遗产,仅依靠文物部门的力量肯定不够,必须要通过教育、宣传、展示,才能使更多民众热爱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才能得到真正地、更好地保护。

不同文明应开放互鉴共同发展
记者:中国如今已是拥有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在此背景下,您认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更好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单霁翔:我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时经常接待外国来宾,我经常会对他们讲“你瞧故宫的景色,红墙、黄瓦、蓝天,这是三原色,用这三种颜色可以谱画出世界任何的色彩”。我们的世界应该是绚丽多彩的,不能是单一色彩的,每个民族都有他们值得骄傲的历史,每个民族也都应该拥有他们向往的未来。
人类文化是多元的,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应该开放互鉴、共同发展。因此我们要增进相互了解,只有通过相互了解,才能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我们既要了解世界,也要让世界了解我们,所以要“走出去”,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还有一个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途径是申报世界遗产。世界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严格程序加以认定,每一项世界遗产都应该具有世界意义的“突出普遍价值”。这样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价值超越了民族和国家,成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在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委托遗产专家进行考察,还会在世界遗产大会上集体评议,通过后才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所以积极参与世界遗产事业,就能得到全世界的关注,就可以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博物馆应不断凝练强大的文化力量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您也一直倡导并努力实践让文物“活起来”,能分享一些经验和感受吗?
单霁翔:过去这些年,我们故宫博物院通过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践,获得了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什么才是好的文物保护状态?我认为不是把文物锁在库房里面,死看硬守就是好的文物保护状态,而是应该把这些文物藏品经过悉心地修复保养,让它保持健康的状态,让它们重新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在生活中感受到这些文物的魅力,才会精心地呵护这些文物,这些文物才有尊严,有尊严的文物,才能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才能惠及更广泛的人们的现实生活。
如何“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我们要继续思考,博物馆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更多的场所,把文物藏品更多地展示出来,讲好文物的故事。故宫博物院启动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使更多的古建筑经过修缮后合理利用,而不是锁起来束之高阁。我认为,一座古建筑修缮以后,将其锁起来,则糟朽得更快,而越将其开放合理利用,经常进行维护,就会使古建筑更加健康。
记者:作为城市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您认为怎样才是一座好的博物馆?您对于博物馆建设有什么建议?
单霁翔: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也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什么是好的博物馆?一座好的博物馆不是盖上高大的馆舍,搞华丽的装修,而是要不断深挖藏品的内涵,凝练它的力量,不断举办人们喜欢的好的展览和活动,这样才能在人民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面前,让人们感受到博物馆对于自身生活的意义,人们休闲的时候才愿意走进博物馆。走进博物馆,人们才会流连忘返,不愿离开;人们回去之后还能再来的博物馆,才是一座好的博物馆。我想,这就是今天人民群众衡量一座博物馆的优劣好坏的标准。
今天,我们博物馆的观众主体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旅游团体为主,到现在以家庭为单位,博物馆也要应对这种趋势,把观众对博物馆参观的愿望和热情激发出来。今天的博物馆依然要通过数字技术,通过互联网技术,把博物馆的声音不断放大,让人们能够听到、感受到。要创造文化遗产保护的良性循环,就要尽可能地开放更多的区域,举办更多丰富多彩的展览,使各个年龄段,尤其是知识欲望很强的年轻人喜欢上博物馆,这样的博物馆才有后劲儿。我希望每一座博物馆都要不断研究人们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根据自己的文化资源,来凝练出强大的文化力量。
香港文化建设必然蓬勃发展
记者:您与香港的缘分与交往颇深,去年还出版了新著《人居香港:活化历史建筑》,您对香港有什么印象?
单霁翔:香港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际都会,但是香港并非“文化沙漠”。香港虽然地域面积不大,但是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汇地,有8,000多栋历史建筑,它们见证了香港城市发展,也承载了集体记忆。
2002至2019年,我先后在国家文物局和故宫博物院工作。这一时期因为工作需要,我曾十余次访问香港,实地考察香港的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感受香港历史建筑保护理念和实践的迅速发展。
香港政府开拓创新,探索出一条更具适应性和操作性的模式来保护和利用历史建筑。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而传播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香港经验和香港故事正是我写作《人居香港:活化历史建筑》的初衷。
在这本书中,我还回顾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从设想到选址、筹备,再到规划、建设的过程。故宫博物院与香港虽然相隔千里,但是有著很深的文化渊源。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有包括《中秋帖》《伯远帖》等重要文物经香港回归故宫博物院。事实上,很多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藏品都有著香港的烙印。1999年,故宫博物院启动了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陈启宗先生创建的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为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提供了全额经费的捐款;许荣茂先生慷慨出资1.3亿元人民币,使《丝路山水地图》“回家”;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慷慨捐赠35亿港元,资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馆舍建设……
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筹建之前,故宫博物院几乎每年都有不同主题的文物展览在香港的各博物馆展出。从宫廷文化到皇家生活,从书法绘画到家具器物,从清宫服饰到外国文物,香港市民得以从不同角度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华传统文化,展览均获得强烈反响。
最使我难忘的是香港民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情,同时香港各界人士助力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文化情怀也让我印象深刻。我接触到的香港人士,无论是文化官员,还是文化学者、博物馆同仁、社会企业家,他们不但拥有国际视野,而且了解国情,善用中西兼容的文化优势,这是香港助力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积极力量。
记者: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已建成运营一周年,您对香港未来的文化事业发展有何期待?
单霁翔: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建设,无疑是香港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件大事,既可以使故宫博物院得以践行中华文化传承的长远承诺,也可以使香港博物馆界增加一份文化自信,更可以为香港吸引更多海内外博物馆爱好者,提升香港成为拥有国际重量级博物馆的文化之都。我们希望借助博物馆的平台,通过文物展览这一直观的方式,向更多香港民众展示中华传统文化,向更多国际友人宣传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未来,我祝福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成为一座有温度、令人震撼、不虚此行的博物馆。让中华传统文化更好地走进700多万香港同胞、7,000多万大湾区居民和世界各国民众的生活中,让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增添一条文化桥梁和纽带,使“东方之珠”更添魅力。
香港背靠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祖国,在文化资源的获取上可谓近水楼台,再加上各方面的强大合力与积极推进,我相信未来香港的文化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必然呈现蓬勃发展的景象。
https://res.youuu.com/zjres/2023/6/27/aAA1CzVZyqX39ZjlZ4G4BavbOdkkm7kGuC5.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