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022年10月26日,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以下简称“国际地科联”)在西班牙公布世界首批100个地质遗产地名录。当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地层古生物学家、南京大学教授沈树忠等地质科学领域专家学者,代表国际地科联在浙江长兴发布包括香港早白垩世酸性火成岩柱状节理等7个中国入选的地质遗产地。为了解世界地质遗产地的重要价值意义及中国地质遗产资源的保护情况,记者采访了沈树忠。
文|本刊记者 魏东升 冯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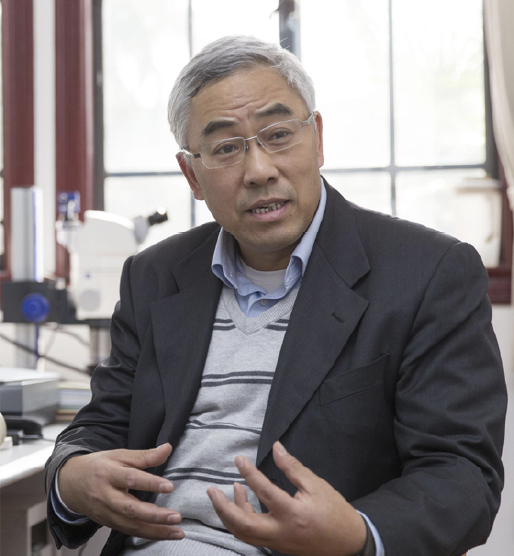
世界首批100个地质遗产地有著共同特征
记者:什么是地质遗产?研究和保护地质遗产有什么重要意义?
沈树忠:实事求是讲,地质遗产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我们通常认为,地质遗产是记录地球46亿年演化和地质过程的遗迹地。在地球演化的漫长历史时期,由于内外动力的地质作用,形成、发展并遗留下来许多珍贵、不可再生的地质现象。这其中的大多数,如今都是著名风景名胜区,具有很高观赏价值。还有一类地质遗产,看起来似乎与风景名胜无关,却记录著地球生命演化的历史,比如一些岩石或地质现象等等。
地质遗产地在科学意义上、在自然景观上以及理解地球演化历史等等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价值。地质遗产地不仅是地质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基地,而且还是广大公众了解地球奥秘、提升科学素养和环境保护意识的绝佳场所。这些遗产地一旦遭到破坏,我们可能没法再在地球上找到其它类似地方了,所以需要加强保护。
记者:国际地科联发布首批100个世界地质遗产地,遴选的程序和评判标准是什么?
沈树忠:国际地科联成立于1961年,是世界上最大、最活跃的地球科学团体,目前入会的国家和地区达121个,相当于地质界的“联合国”。此次100个遗产地由国际地科联通过公平公正的投票选举选出,是官方认可的、正式的地质遗产地名录。
2022年初,国际地科联地球遗产委员会向全球各会员和相关国际学术组织发布遴选通知。地质遗产地采取自由推荐方式,地质遗产地管理机构、科研机构、科学工作者等可按模板(格式)推荐全球任何地方自己认为符合条件的地质遗产地。与此同时,该委员会从21个国家和地区遴选34位地质遗产领域的专家组成评审和投票专家组。之后,地球遗产委员会按照 34 位评审和投票专家的专业特长,分配相应候选地的推荐材料,进行评估打分,打分标准分三个等级:完全达到标准(3分)、基本达到标准(2分)和没有达到标准(1分)。每个候选地的遴选至少有3位专家参与,并需给出打分依据和具体意见。初步遴选工作在 2022年6 月底基本完成。最后,地球遗产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要根据专家评估打分情况,依照候选地的科学价值、研究和保护程度,兼顾地球科学领域和全球地域相对均衡的原则,对候选地进行综合评定,最终确定首批100个地质遗产地名录,并报国际地科联核证批准。
从整体情况来看,本次国际地科联地质遗产地的遴选在国际社会引起了积极响应,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收到来自56个国家和地区181份合格的推荐提案,质量整体良好。尽管多数提案由所在国的专家推荐和提交,但也有不少提案人从全球的角度按其专业判断对其他国家的地质遗产地进行推荐,很好地显示了这一工作的科学性和全球性。最终入选名录的100个地质遗产地都有著共同特征:是该类地质遗产在全球最佳代表或在地球科学发展史上具有特别重要地位、科学研究达到国际水平、获得良好的保护。
国际地科联推出和推动这样一项工作,主要为了宣传宜居地球、保护地球和环境、地质科学研究等内容。一方面,能够入选地质遗产地,说明这些地方在地质方面研究的水平比较高,科学意义重要,另一方面,随著文明程度的提高,公众对自然现象、地球科学中的难题比较关注,发布名录也是希望公众对相关问题有更多了解。

中国地质遗产地保护状况受到国际社会肯定
记者:中国有7个地质遗产地成功入选,这些地质遗产地有什么价值?中国是本次入选遗产地最多的国家之一,这意味著什么?
沈树忠:中国本次入选的7个地质遗产地包括,长兴煤山二叠纪/三叠纪生物大灭绝和“金钉子”、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必鲁特高大沙山和湖泊、云南澄江寒武纪化石产地和化石库、香港早白垩世酸性火成岩柱状节理、云南石林喀斯特、藏南绒布峡谷滑脱构造体系、珠峰奥陶纪岩石(中国/尼泊尔)。它们涵盖了岩石学、构造地质学、地层古生物学、地理学、地貌学等领域,在地质上都有著特殊的意义。其科学价值和研究水准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一致认可,优良的保护状况也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肯定。
其中,珠穆朗玛峰山顶的4.6亿年前奥陶纪石灰岩,形成于温暖的浅海中。这些岩石中含有大量海洋动物化石,代表了地球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奥陶纪生物大辐射时期的热带海洋生物,它们现今大多已经灭绝。云南石林喀斯特保存并展示了世界上最好的剑状喀斯特(石林)地貌,它的形成经历了跨度2.5亿年的复杂地质演化过程,构成了一幅从地上到地下的喀斯特全景图。浙江省长兴县的煤山“金钉子”剖面,含有两颗经国际地科联和国际地层委员会正式批准的“金钉子”——二叠系-三叠系界线、长兴阶底界“金钉子”。该剖面完整记录了2.52亿年前地质历史时期发生的最大的一次生物灭绝事件,这次生物灭绝事件导致当时海洋和陆地中80%以上的生物物种在很短的时间内灭绝,为认识和保护当今地球的生物与环境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历史借鉴。
地质遗迹的保护和国家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文明程度。中国成为本次入选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一方面说明我国地大物博、地质现象和地质遗产丰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们对地质遗产地的保护进入了一个比较良性或是较高水平的循环。

记者:中国地质遗迹资源整体的发现和保护情况如何?您认为未来应如何加强对地质遗产的保护和研究?
沈树忠:我国地质遗迹资源丰富、分布地域广阔、种类齐全,是世界地质现象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底,全国调查出重要地质遗迹点6,322处。2019年—2021年,累计调查全国重要古生物化石产地2,176处。中国14处世界自然遗产、4处自然和文化双遗产都涉及地质遗产地,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福建、广东、江西等地;中国38处世界文化遗产也有10余处涉及地质遗迹。截至2022年6月底,中国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41处,总面积5万余平方公里;同时还拥有国家地质公园281处,都已成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从地质遗迹的整体发现和保护情况来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比如美国的黄石公园、科罗拉多大峡谷这些地质遗产地,无论是地质景观、科学意义还是其给全球普通游客的印象,都比我国的地质遗产地知名度和影响力要高很多。而且他们在管理和保护方面都非常规范,比如有统一的网络平台和委员会来审批人们在这些区域的活动,确保不会给遗产地造成破坏。
我们国家尤其是地方政府,对一些具有重要旅游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地质遗产地保护比较重视,但是对一些具有重要科普宣传意义却不能带来显著经济效益的地质遗产地的保护措施相对而言要差一些。另一个方面,保护这些地质资源的意义是什么、它到底有什么用,很多普通老百姓其实不太明白,而我们又缺乏一个比较系统的能够约束和执行地质遗产地保护的法律法规。在一些化石产地,常常会出现当地乡民四处采挖的情况。有时候科学家想要正常地实地考察研究,反而会受到当地有关部门和老百姓的阻挠。
所以我认为,我国在保护地质遗产地方面迫切需要加强一些相关法律法规的制订工作,同时还应当建立一套规范的管理模式,把国家公园、世界地质遗产地这些珍贵的地质资源纳入一个统一规范的平台进行管理和保护。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保障这些地质资源不被破坏,而且能够帮助科学家们更好地开展更多的科学研究。
保护并不意味著不能进行开发和利用。正相反,保护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科学研究,规范有序的开发、科学合理的利用。在我国东部省份,一些地质遗产地周边配套建设了博物馆、科技馆,帮助大家加深对地质遗产的理解,长兴煤山就建了两个博物馆;在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地质遗产多数建在地质公园、地质遗产保护区内,保护与发展更接近原生态、自然态,也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香港地质公园完好展示了极高的地质多样性
记者:香港早白垩世酸性火成岩柱状节理本次成功入选,不知您可到过香港实地考察?这一地质遗产地有什么特点和价值?
沈树忠:非常遗憾,我还没有到现场看过,不过我看了照片和介绍感到非常震撼。香港西贡火山岩园区的早白垩世流纹质火山岩柱群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地质遗迹。这些火山岩柱群源自约一亿四千万年前该地区的火山活动。当时剧烈的地壳活动导致香港东南面形成一座超级火山。经过前后长达300万年的猛烈喷发后,火山最终崩塌,形成直径约20公里的破火山口,大量火山物质在破火山口内堆积并冷却。由于冷却环境稳定及火山物质均匀一致,过程中火山物质能够随著冷却体积收缩,导致表面首先形成规整的六角网络状裂隙,并随著冷却方向下延伸,最终将庞大的火山物质分割成数百万条岩柱。
纵观世界各地的六角形岩柱大多属二氧化矽含量较低的深灰色基性玄武岩,惟香港地质公园的岩柱罕有地由富含二氧化矽的流纹质中性火山岩形成,分布在西贡粮船湾、滘西洲、吊钟洲、瓮缸群岛及果洲群岛等约100平方公里海陆区域。这些岩柱的直径平均为1.2米,最粗达3米,现存总厚度估计达400米,露出地表的高度达100米。加上这些岩柱大多分布在西贡地区绵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岛屿上,海岸侵蚀使得这些岩柱清晰敞露,并结合了丰富的海蚀地貌景观,构成全球罕见的地质奇观。
记者:近年来,您与香港方面有过哪些交流合作?您如何评价香港的地质资源情况?
沈树忠:香港是一个著名的国际大都会和金融中心,区域面积相对较小,人口十分密集。在高度发展的同时,香港拥有完善的自然保育政策,保护了大部分的自然景观、生态环境和地质遗产。在仅有的约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多达40%的土地被划作保护区,其中包括了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香港地质公园。香港地质公园虽是世界上面积最小的地质公园之一,却完好展示了极高的地质现象多样性。我相信香港特区政府机构和普通民众都对保护当地自然景观的重要意义比较了解,应该说在理解的程度上比内地要高一个层次。
我多次访问过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与香港高校的教授、院士就保护地球、保护生物多样性等话题开展学术研讨。但是与他们进行一些实质性的深入合作,目前还比较少。近期我参加了2022年香港“科创大讲堂”活动,很高兴被聘为香港学校科学教育荣誉讲师。
在地质研究领域,香港有许多优秀人才,在这方面其实已经比较超前了。不过香港毕竟地理范围小,地质资源的丰富性受限,所以我特别希望香港的科学家们能够多到内地开展研究。一来,他们可以见到很多香港见不到的地质现象,二是他们可以把香港的成熟经验带到内地来,也会对内地产生好的影响。
不懈探索人类和地球其他生命和谐共存
记者:作为世界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2019年,您荣获世界地层学国际最高金奖,也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亚洲科学家。对您而言,在地质科学不懈探索的理想和使命是什么?
沈树忠:当初我选择地质学研究,完全是一个偶然,一开始也不懂这到底是做什么的。但是在学习过程中,尤其在后来的工作当中,我越发觉得地质工作非常有趣。我们老说“胸怀全球,放眼世界”,地质学家可以走遍天涯海角。我们去世界各地勘探,采集各种各样的石头样品等等,回来后做室内的分析,再把它写成文章,写的过程中又会碰上新的问题,需要再去跑新的地方。
地球科学没有国界,因为我们要从地球的整体来理解这个星球上的演化过程。我所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地球生命的演化,比如火星上没有生命,而地球上的生命却能够发展到如此发达的程度,导致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地球上自生命出现以来共有近四十亿年的历史,这些生命是怎么起源的、怎么一步步进化过来的?又比如地球的生命系统有没有受到过强烈的灾难性事件,或者导致地球生命系统受到严重威胁的事件?总的来讲,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样的地球才是一个宜居的地球,我们怎么做才能够让地球可持续发展下去。
其实我们研究后发现,地球历史时期曾经发生过多次令整个生物圈受到严重威胁的事件。现在地球人口快速增长,人类居住区域占领的面积越来越大,对其他生物、对整个地球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些都跟地球生命的演化息息相关。我们需要特别加强宜居地球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我一直觉得,如果人类不能生存下去,那我们做所有其它的事情都没有意义。人类怎样能和地球的其他生命和谐共存,这是一个我们都需要去努力探索的科学问题。

https://res.bau.com.hk/url/1521/2023/1/3/XR0uUh5WmY5m9LaAFdQWpPGPq5OqXbkHkaO.png
扫描二维码分享到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