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现象。统治者独尊儒术,儒家圣人的著作成为经典,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相信经书上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发展到极致,必然要出现一些过分的情况。汉代经学就出现了繁琐注经、异化和内部分裂等三种不正常的现象。
独尊儒术以后才有经学,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现象。中国远古时代就尊崇上天,称为天命,认为天命主宰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天命的意思,只有圣人知道,圣人代表上天说话。圣人死后,思想就保存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的著作就是经。因此,这些经就是圣人的思想,上天的意思,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相信经书上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研究这些经,小可以修身,齐家,大可以治国、平天下。研究过程中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就是经学。
统治者独尊儒术,就要选精通儒家经典的人当官,这就自然产生明经取仕。公孙弘就由于研究《春秋》而从平民当上了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学习好经书,做官就非常容易,当时有一位经学教师对学生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汉书·夏侯胜传》大意是:读书就怕不理解经书中的思想,如果理解透彻了,那么,想当太尉御史大夫之类的大官,就像弯腰从地上拾取土芥那样容易。所以社会上流传这样的说法:“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留给子女黄金一筐,不如教子女学会一本经书。有一个学者叫桓荣,他由于通经,当了少傅,得到皇帝很多赏赐。他将皇帝赏赐的车马印绶陈列出来,请朋友与学生来参观。并且说:“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后汉书·桓荣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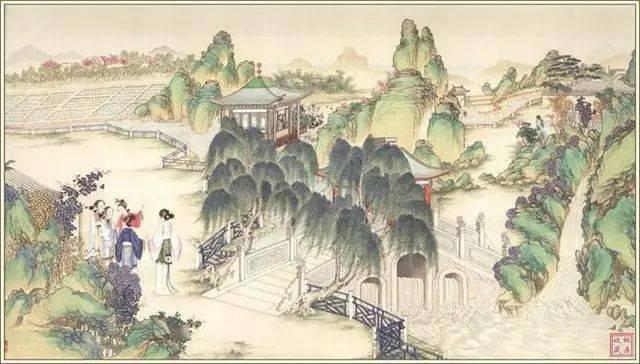
今天所得,都是靠读古代经典。朝廷官员,经常讨论政治问题,都要引经据典。只有精通经典,才能灵活运用,才有说服力。有时因为经学水平不同,还要经过争论来排座次。例如,有一次,东汉光武帝召集一次学术讨论会。古代规矩在宗族集会上,序齿排辈,按辈份和年龄来排座次,在朝廷上按官阶品级来排。那次学术会议,也是按官阶品级来排。当时有个叫戴凭的不肯入座,光武帝问他为什么站著不坐,戴凭说:“有些人解经水平不如我,却坐在我的前面,所以我不入席。”光武帝说:“你看谁不如你,你就找他辩论,他辩输了,你就夺他的座位。”光武帝也让别的官员都可以通过辩论夺他人的座位。许多人提出经书中的问题,戴凭都能解说。他提的问题却难倒了许多人。那一天,戴凭共夺了五十多个座位。这个学术会议按学术水平排座次,是别开生面的。总之,儒家经书成了汉代社会的灵魂。经学成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朱买臣也是很穷的书生,由于刻苦读书,精通经书,后来当上大官。读儒家经典而当上官的人很多,特别是元帝以后,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皮锡瑞《经学历史》)。
一个学派成为权威以后,必然要出现一些过分的情况。儒家独尊以后,也出现几种不正常的现象:
一是繁琐注经。汉代立几本经书,天下之大,学者之多,都集中研究几本经书,一章一句的解说,所谓“章句之学”。一个教师有一种说法,这叫“师法”。教师的说法能够成一家之言,又叫“家法”。学生首先要学会师法,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理解,来注释经书,代代相传,经书的注,越来越多,越注越复杂。夏侯建是研究《尚书》的,宣帝时立于学官。夏侯建解说《尚书》,内容可能不太多,他传授给张长宾,张长宾又传给秦延君。秦延君注解《尚书》“增师法至百万言”(《汉书·儒林传》。桓谭说,秦近(延)君解说《尚书》中《尧典》篇目两个字,就注了十余万言,只注“曰若稽古”四个字,也用了三万言。(《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引桓谭《新论》)这类现象相当普遍,“说五字之文,至二三万言”(《汉书·艺文志》)。而且这种趋势日益严重。一个人从幼童入学,只学一本经书,到头发白了,才能解说,所谓“皓首穷经”。“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此学者之大患也(《汉书·艺文志》)。
二是异化。儒学独尊以后,几部儒家经典具有极高权威,任何言行都要以儒家经典上说的为最高标准。思想成为如此权威以后,就会产生异化。真精神被掩盖了,书中的文字变成教条。一种情况是,创新思想受到严重挤压。但是创新思想是压不住的,要用其他各种方式,甚至借用经书,展示出来。今文经学家采用“六经注我”的方式,以阐明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为借口,阐发自己的思想。例如在《春秋经》开头一句:“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的解释是:隐公即位第一年,按周历的第一个月。董仲舒从此引出许多说法:“王”是君王,“春”是天,天在王上。天之上还有“元”,“元”存在于天之前。“正”是政,也就是统治人民的意思。从此引出,王者必须上顺天意,下教人民。“元”在天地之前,是开始。称第一年为“元年”,就表示重视开始,重视根本。从此引出大一统说法,认为《春秋》强调大一统,大一统是宇宙间最普遍的法则。董仲舒这些思想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如果说是他的想法,没有人相信,他要与《春秋》相联系,并且说成是天意,这样才具有权威性,别人才会相信,特别是像汉武帝那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才会认真考虑这种意见。另一种情况是出现纬书。纬书,采取经纬这个说法,将自己的思想与经书相联系,称为纬书。有的说是注解经书,有的根本看不出与经书有什么联系。对每一种经,都编撰一批纬书,例如与《周易》经相对应的有《易纬》,其中包括《易乾坤凿度》《易乾凿度》《易稽览图》等十多种。与《春秋》经相对应的有《春秋演孔图》《春秋元命苞》《春秋文耀钩》等十三种。权威过度,就必然产生迷信,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而纬书却有很多“怪力乱神”的内容。
三是内部分裂。诸子争鸣,儒家与其他家矛盾很大。儒家独尊以后,诸子无力与其抗争。诸子有合理性的思想,都被儒家所吸取。结果在儒家内部形成不同的派别,展开斗争。由外部矛盾变成了内部矛盾。汉代儒家有许多派别,可以说每一种经都有不同的“传”。“传”就是指阐释发挥经书的思想,相当于现代的注释,例如《春秋》经,就有《公羊传》、《谷梁传》、《左传》,都是解释《春秋》经的书,成为三个派别,它们的说法有同有异。从大的方面分,可以分成两大派: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是政治家,认为“六经”是指导政治的学说,所以重视“微言大义”,经常结合现实讨论经学,主张天人感应说。缺点是臆解经文,以合己意,曲解附会。古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是史学家,“六经”是孔子整理古代史料的书,所谓“六经皆史”。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著重于考证,希望恢复古史的真面目。缺点是繁琐。前者是哲学家,“六经注我”;后者是史学家,“我注六经”。今文经学以《公羊传》为经典,专家以董仲舒和何休为代表;古文经学大家以《左传》为经典,专家以刘歆、贾逵为代表。今文经学盛行于西汉,古文经学盛行于东汉。东汉后期,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开始融合,郑玄融会两家说法,取长补短,遍注群经,自创一家之言,成为两汉注经的集大成者。

(来源:周桂钿. 中国儒学讲稿[M]. 北京:中华书局,2008:49-52.)
https://res.bau.com.hk/url/1521/2022/2/19/zOAOeDIgmbDwP9l0boPbuu405R6m4aogIh7.jpg
https://res.bau.com.hk/url/1521/2022/2/19/jfb0cSPGK4p1kzYDb1VsxsO0wUHVN6isqik.jpg











扫描二维码分享到手机
![]()
+关注
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现象。统治者独尊儒术,儒家圣人的著作成为经典,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相信经书上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发展到极致,必然要出现一些过分的情况。汉代经学就出现了繁琐注经、异化和内部分裂等三种不正常的现象。
独尊儒术以后才有经学,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现象。中国远古时代就尊崇上天,称为天命,认为天命主宰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天命的意思,只有圣人知道,圣人代表上天说话。圣人死后,思想就保存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的著作就是经。因此,这些经就是圣人的思想,上天的意思,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相信经书上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研究这些经,小可以修身,齐家,大可以治国、平天下。研究过程中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就是经学。
统治者独尊儒术,就要选精通儒家经典的人当官,这就自然产生明经取仕。公孙弘就由于研究《春秋》而从平民当上了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学习好经书,做官就非常容易,当时有一位经学教师对学生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汉书·夏侯胜传》大意是:读书就怕不理解经书中的思想,如果理解透彻了,那么,想当太尉御史大夫之类的大官,就像弯腰从地上拾取土芥那样容易。所以社会上流传这样的说法:“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留给子女黄金一筐,不如教子女学会一本经书。有一个学者叫桓荣,他由于通经,当了少傅,得到皇帝很多赏赐。他将皇帝赏赐的车马印绶陈列出来,请朋友与学生来参观。并且说:“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后汉书·桓荣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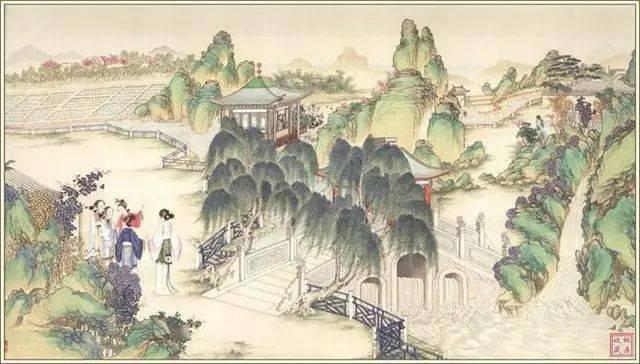
今天所得,都是靠读古代经典。朝廷官员,经常讨论政治问题,都要引经据典。只有精通经典,才能灵活运用,才有说服力。有时因为经学水平不同,还要经过争论来排座次。例如,有一次,东汉光武帝召集一次学术讨论会。古代规矩在宗族集会上,序齿排辈,按辈份和年龄来排座次,在朝廷上按官阶品级来排。那次学术会议,也是按官阶品级来排。当时有个叫戴凭的不肯入座,光武帝问他为什么站著不坐,戴凭说:“有些人解经水平不如我,却坐在我的前面,所以我不入席。”光武帝说:“你看谁不如你,你就找他辩论,他辩输了,你就夺他的座位。”光武帝也让别的官员都可以通过辩论夺他人的座位。许多人提出经书中的问题,戴凭都能解说。他提的问题却难倒了许多人。那一天,戴凭共夺了五十多个座位。这个学术会议按学术水平排座次,是别开生面的。总之,儒家经书成了汉代社会的灵魂。经学成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朱买臣也是很穷的书生,由于刻苦读书,精通经书,后来当上大官。读儒家经典而当上官的人很多,特别是元帝以后,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皮锡瑞《经学历史》)。
一个学派成为权威以后,必然要出现一些过分的情况。儒家独尊以后,也出现几种不正常的现象:
一是繁琐注经。汉代立几本经书,天下之大,学者之多,都集中研究几本经书,一章一句的解说,所谓“章句之学”。一个教师有一种说法,这叫“师法”。教师的说法能够成一家之言,又叫“家法”。学生首先要学会师法,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理解,来注释经书,代代相传,经书的注,越来越多,越注越复杂。夏侯建是研究《尚书》的,宣帝时立于学官。夏侯建解说《尚书》,内容可能不太多,他传授给张长宾,张长宾又传给秦延君。秦延君注解《尚书》“增师法至百万言”(《汉书·儒林传》。桓谭说,秦近(延)君解说《尚书》中《尧典》篇目两个字,就注了十余万言,只注“曰若稽古”四个字,也用了三万言。(《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引桓谭《新论》)这类现象相当普遍,“说五字之文,至二三万言”(《汉书·艺文志》)。而且这种趋势日益严重。一个人从幼童入学,只学一本经书,到头发白了,才能解说,所谓“皓首穷经”。“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此学者之大患也(《汉书·艺文志》)。
二是异化。儒学独尊以后,几部儒家经典具有极高权威,任何言行都要以儒家经典上说的为最高标准。思想成为如此权威以后,就会产生异化。真精神被掩盖了,书中的文字变成教条。一种情况是,创新思想受到严重挤压。但是创新思想是压不住的,要用其他各种方式,甚至借用经书,展示出来。今文经学家采用“六经注我”的方式,以阐明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为借口,阐发自己的思想。例如在《春秋经》开头一句:“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的解释是:隐公即位第一年,按周历的第一个月。董仲舒从此引出许多说法:“王”是君王,“春”是天,天在王上。天之上还有“元”,“元”存在于天之前。“正”是政,也就是统治人民的意思。从此引出,王者必须上顺天意,下教人民。“元”在天地之前,是开始。称第一年为“元年”,就表示重视开始,重视根本。从此引出大一统说法,认为《春秋》强调大一统,大一统是宇宙间最普遍的法则。董仲舒这些思想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如果说是他的想法,没有人相信,他要与《春秋》相联系,并且说成是天意,这样才具有权威性,别人才会相信,特别是像汉武帝那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才会认真考虑这种意见。另一种情况是出现纬书。纬书,采取经纬这个说法,将自己的思想与经书相联系,称为纬书。有的说是注解经书,有的根本看不出与经书有什么联系。对每一种经,都编撰一批纬书,例如与《周易》经相对应的有《易纬》,其中包括《易乾坤凿度》《易乾凿度》《易稽览图》等十多种。与《春秋》经相对应的有《春秋演孔图》《春秋元命苞》《春秋文耀钩》等十三种。权威过度,就必然产生迷信,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而纬书却有很多“怪力乱神”的内容。
三是内部分裂。诸子争鸣,儒家与其他家矛盾很大。儒家独尊以后,诸子无力与其抗争。诸子有合理性的思想,都被儒家所吸取。结果在儒家内部形成不同的派别,展开斗争。由外部矛盾变成了内部矛盾。汉代儒家有许多派别,可以说每一种经都有不同的“传”。“传”就是指阐释发挥经书的思想,相当于现代的注释,例如《春秋》经,就有《公羊传》、《谷梁传》、《左传》,都是解释《春秋》经的书,成为三个派别,它们的说法有同有异。从大的方面分,可以分成两大派: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是政治家,认为“六经”是指导政治的学说,所以重视“微言大义”,经常结合现实讨论经学,主张天人感应说。缺点是臆解经文,以合己意,曲解附会。古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是史学家,“六经”是孔子整理古代史料的书,所谓“六经皆史”。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著重于考证,希望恢复古史的真面目。缺点是繁琐。前者是哲学家,“六经注我”;后者是史学家,“我注六经”。今文经学以《公羊传》为经典,专家以董仲舒和何休为代表;古文经学大家以《左传》为经典,专家以刘歆、贾逵为代表。今文经学盛行于西汉,古文经学盛行于东汉。东汉后期,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开始融合,郑玄融会两家说法,取长补短,遍注群经,自创一家之言,成为两汉注经的集大成者。

(来源:周桂钿. 中国儒学讲稿[M]. 北京:中华书局,2008:49-52.)
https://res.bau.com.hk/url/1521/2022/2/19/zOAOeDIgmbDwP9l0boPbuu405R6m4aogIh7.jpg
https://res.bau.com.hk/url/1521/2022/2/19/jfb0cSPGK4p1kzYDb1VsxsO0wUHVN6isqik.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