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荆论坛》专稿/转载请标明出处
邱 逸 I 香港都会大学助理教授
中华文明是世上唯一未中断的广土巨族式古文明。如果地球是一个舞台,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群雄竞逐,此起彼落,但无论情况如何改变,中国都是其中一个主要的「雄」,曾经的对手不少如匈奴、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满洲等都或亡或弱,唯独中国是盛衰不息,唯独中国从未离开过舞台。更何况中国是文明早、地盘大、人口多、历史长,全世界独此一家,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中华文明,就是「历史悠久的『大一统』的非一神教思维的中央集权超大体系」。鸦片战争是中国人「未有之变局」,往后一百年,中国不仅有差一点被踢出舞台之患,更有灭国灭族之虞,但经过一百多年的变革和自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那个曾经是亚洲秩序主宰的中华文明正在复兴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甚至将传统「大一统」制度推向现代化的高峰。中国能历史悠久、能「大一统」、并能在没有一神教思维下建设人多又杂、地大而广的中央集权帝国,背后就是中国独有的「大一统」思维,从而生出丰富的生存、辩证、应对和整合的知识。
一、「大一统」初立
中国的「大一统」概念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后经董仲舒把王权和儒家结合,使「大一统」成为一种思想理念和政治型态。
仅从文字上看,「大一统」以正朔(历法)、服色(官制)和礼乐(尊卑等级)为「一统于天下」的标志,凝聚了儒家思想中关于王权正当性的理念:它将周代追思为理想社会,王权受命于「天」,确立统一权威的至上性。而在制度创新和建设上,秦汉都作了非凡的贡献。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中国正式走向「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这套制度比之前的西周封建制度要先进和复杂得多,现据考古所得,特别是里耶、睡虎地等秦简的出土,我们就会发现秦始皇的功绩,不仅是扫平六国、建郡县、封三公、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还有更多涉及现代公务管理的工作,如建立了复杂的文书制度、档案存放制度、文官培训制度、地方管治制度、官员的请示汇报制度等,秦简上的记载近乎巨细无遗,甚至涉及特殊案件、特殊人物的记录和在案。
秦亡汉立,汉代初年要休养生息,直到汉武帝继位,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深化并完善了秦制,特别是在经济层面上,例如货币政策有货币官铸、产业政策是盐铁国营、财政政策有均输和平准。
在往后千多年,「大一统」思想在政治上维护了政权的统一,强调政治统一、思想统一,有助于避免长期处于分裂之中。「大一统」的思想适应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统一了思想,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安定了社会,改善了国家的治理,也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著名经济史学者安格斯 ,麦迪森(Angus Maddison)在其不世巨著中写到:「(中国) 一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实体…(领先地位) 一直延续至十五世纪。在技术水平上,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以及在对辽阔疆域的管理能力上,中国都超过了欧洲。在此后的三个世纪中,欧洲才在人均收入、技术和科学能力上逐渐超过了中国。」
二、变局和冲击
鸦片战争之后,「大一统」开始遭到西方势力的强大而持续的冲击。1860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观于今日,夷患不已」,西方侵略是「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 他们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在观念上并未能跳出「大一统」的「天下观」和「华夷观」。在鸦片战争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清代政治和思想精英试图通过「严夷夏之防」来挽救「天下秩序」。其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期望通过在器物层面学习西方,实现国家富强,李鸿章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上说的「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原话的「奇局」是指,中国的大患由北方变为东南方,大敌则从陆地转为海洋而来,而对手从单一民族变成许多国家联群结队击打中国。到甲午战争战败之时,朝贡体系土崩瓦解,「大一统」也走向分裂,越来越多的政治和思想精英认识到,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国,而且是其中羸弱的一国。康有为和梁启超率先提出学习西法,「以夷变夏」,使中国从世界的一国,变成世界的强国。
但晚清的政治和思想精英还未能看到大变局的真义,大清是一个人口多、文盲多、技术弱、组织差、制度乱的农业国,在军事、财政、教育、卫生等各方面都远远落后同期已进入工业社会的西方列强,在往后的70年到1949年,中国走上艰难痛苦的变革之路,从洋务、维新、立宪、国民党革命到共产党革命,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逐渐走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三、「大一统」的现代转化
如果我们用上帝视野看这段历史,会发现中共建党一百年是近代史的大转折,是中国由衰转盛的转捩点,从「最危险的时候」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经济总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600多亿元人民币到2020年突破100万亿元大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加到77岁,教育水平从文盲率超过80%到大学毛入学率超过50%,去年全国贫困人口全面脱贫,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首次,这不仅是中国人的奇妙之旅,也是人类发展的新奇迹。
在这种峰回路转的发展里,新中国的「大一统」是如何在传统封建王朝「大一统」上作理念的改革和创新呢?
新中国「大一统」理念作了三个方面的改变,形成当代中国的核心政治共识。
(1)人民性
新中国为传统封建王朝的「大一统」注入新的时代精神——人民性。传统封建王朝「大一统」植根于皇权体系,以天子为政治象征;新中国「大一统」植根于人民民主,以人民为主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一章 ,总纲 ,第二条〉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新中国最响亮的政治诉求就是「为人民服务」,在国家与人民个体之间建立了更为直接的关系,具有更强的动员能力。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政权的民主认同是人民整体作为主权者行使主权的结果,是维护我国统一大局的基础,也是地方自主发展不能超出的界限。新中国的「人民」不是虚构的想像,而是经由血与火的考验塑造出来的,是通过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所组成的,历经统一战线、独立建国、土地改革、劳资协调、男女平等、城乡互助等社会革命而塑造出来的。人民就是以共和国形式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人民就是共和国的根基,没有人民就没有共和国的成立和发展壮大。
(2)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传统封建王朝的「大一统」有其局限性,最明显的缺憾就是因组织力的欠缺和技术的落后,体现出来的就是「皇权不下乡」,中央统治权力无法延伸到乡下,而是借助士绅来间接统治乡下的组织形式,有学者总结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即使辛亥革命成功了,传统封建王朝告别历史舞台,没有皇帝的「大一统」,制度如何设定,也经过艰难的探索,孙中山曾叹说:「中国虽四万万之众,实等于一盘散沙」,这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常态,内忧外患、四分五裂、军阀割据、战争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
1943年,中共根据地面对日军、国民党和自然灾害等三重压迫,境况凶险,毛泽东发动「组织起来」的运动:「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通过党组织把命令下达到每一个大型机构、企业,甚至街道上的每一家一户,一改秦汉制度以来的皇命不下乡的情况,大大深化了集权的内容和工具。如果以战场表现为准则,就会惊讶地发现同样是中国士兵,在抗日战争时被日军打到落花流水,却在十多年后的朝鲜战争中,面对著比日军装备更精良、后勤更完善、战力更充沛,而且刚在大平洋战争中迫使日本无修件投降的美军时,却在朝鲜战场和美军互有胜负,最后要在三八线上妥协。
以政治权威保障中央政权的统一。中共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以及各种社会团体中实施组织建设,通过贯彻党的方针,统一组织纪律,保障了中央政权统一领导的实现。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超大型组织,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个组织的核心,一层层广及社会各个领域。新中国的「大一统」是政权权威体系中的一元核心:中共作为政治权威领导核心,中央作为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力核心,二者通过中共的政治、思想、组织领导结合成为全国统一发展的核心权力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新中国的「大一统」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大优势,这一制度优势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的综合优势。为防控疫情,中共中央采取系列措施都充分演示了新中国的「大一统」特色和能力: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建立联防联控机制;通过封城切断传染源;综合多学科力量进行科研攻关;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在加强防控的前提下,采取差异化策略,分割分级、分类分时地复工复产。在全国动员防役战中,让我们更能看到这个组织的运作,无论是横向的医护、军队、大学、企业、市民、基层党组织等,或纵向的省市支援,都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声令下井井有条地投入防疫战中,其组织细密、周详、完备、复杂和一致,都令人叹为观止。可以说,党把组织能力和动员优势转化成为疫情防控优势。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的「大一统」中建立了完备的组织体系,各级党组织担负不同职能,发挥不同作用,全党服从中共中央统一领导,党的方针政策能够落地执行,借助完备的组织体系,做到了真真正正地全国一盘棋。
所以,习近平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说:「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这是历史实情,也有深刻道理。
(3)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
中央为地方多元发展需求提供了开放结构,将多种政治制度和多种区域形态整合到统一发展轨道中,以中央统一领导,引导地方自主发展朝著巩固统一和深化共识的方向发展,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共同发展。全国人大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中统一行使主权者权力,以此为基础产生的中央政权是全国唯一的主权性单位,这是新中国采取单一制的根本标志。以此为出发点,新中国在政权配置体系中都贯彻了统一原则:首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对下一级权力机关行使立法监督权,保证了立法权体系的统一。其次,国务院作为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全国行政权体系。最后,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终审权,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全国检察院实行法律监督,共同保障了全国法治运行的统一。
在地方制度层面,新中国则实行因地制宜原则。除省行政区划外,新中国还设置了直辖市、民族自治区、经济特区和行政特区等不同形态的地方单位。为促进地方发展,中央对特定区域分别进行特别授权,有的授权甚至不惜突破现有基本制度框架:如港澳的「一国两制」中,中央除了保留主权,在包括基本政治制度在内的广泛领域内,都允许行政特区实行自治。
这种制度设计平衡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中央负责外交、国防、人口控制等领域,省则负责主要经济事务、地方建设,许多政策由中央制定,地方执行。中央在制定政策时,经常会咨询地方政府的意见。学者郑永年称此一制度为「行为联邦制」,并指:「这一制度的中心特征,促成了中国层出不穷的地方创新和高速的经济发展。同时,单一制的集权政治架构,又确保中央对地方拥有相当的控制权,能够推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结语
著名的史家唐德刚曾提出「历史三峡论」:中国历史第一段是先秦的封建社会,第二段是皇权农业帝国,第三段是民权开放的工商社会。第一至第二段的转型,从战国到秦帝国,大约三百年。第二到第三阶段,从1842年鸦片战争打开天朝大门开始,约需二百年时间,即到二十一世纪四、五十年代,才能完成中华帝国到一个真正现代共和国的转型。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100年,在这100年中,不但解决了百年朝代更替的问题,如政权转易、军阀割据、海上侵略、殖民势力、资本入侵、政治代言等,也一并解决了千年以上的民族蜕变问题,如农业转工业人口、政制落后、文盲遍地、各式的地方主义(乡绅治乡、宗族械斗、拥兵割据)和男女不平等。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治理下完成了从中华帝国到一个真正现代共和国的转型,党对中华民族在制度上的最大贡献,是在70年的探索、试错和实践中,完成了中央集权的现代化,并使中国复兴有一可靠的载体。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1年11-12月号第45-4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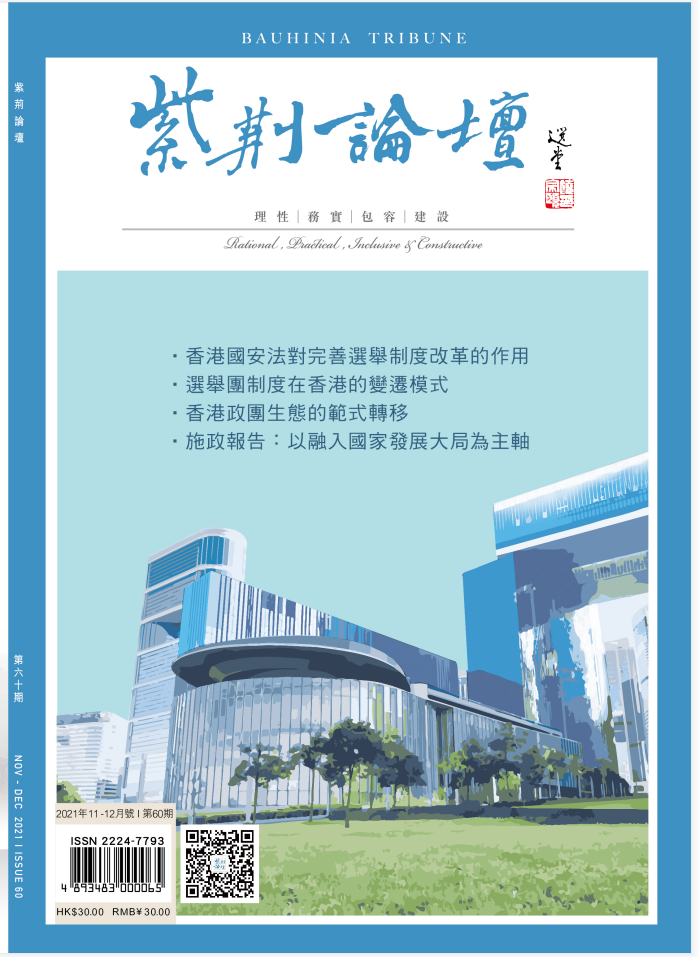
扫描二维码分享到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