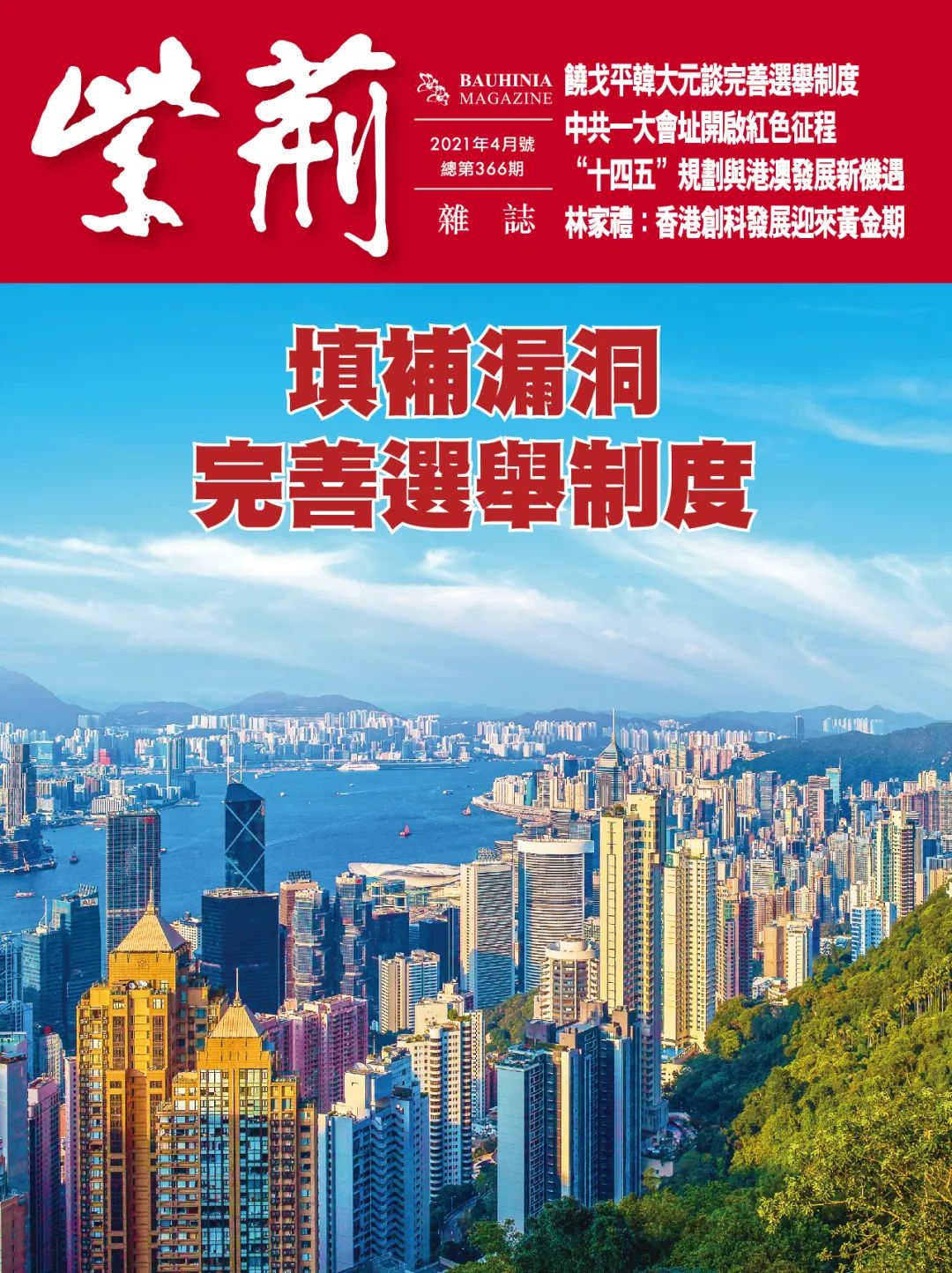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以高票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继制定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后,国家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和政治体制的又一重大举措。法治是在完善选举制度中凝聚共识的根本基础,也是对香港社会普遍关切的合理回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在关于《决定》草案的说明中提出了完善选举制度的五项重要原则,其中第三项原则是“坚持依法治港”,指出“维护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在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轨道上完善有关选举制度和相关机制,严格依照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决定和香港本地法律组织有关选举活动,提高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本文结合《决定》以及《决定》草案的说明,谈谈如何在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过程中坚持法治原则的问题。

3月15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到街站签名联署,支持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左图:林郑月娥在位于港铁坚尼地城站的街站展示签名;右图:林郑月娥的签名(图:新华社)
全国人大作出《决定》
具有充分法律依据
《决定》指出,为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发展适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根据宪法第31条和第62条第2项、第14项、第16项的规定,以及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决定》。全国人大作出《决定》的首要依据是宪法。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作为授权条款,宪法第31条明确授权全国人大设立特别行政区,并以法律规定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这为特别行政区所有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奠定了宪法基础。选举制度作为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自然是由全国人大依据宪法第31条建立,并根据实践的需要由全国人大不断完善。同时,宪法第62条第14项规定,全国人大有权“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这一规定在宪法第31条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的权力主体,即只有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有权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体现主权机关的主权意志。因此,由全国人大对香港选举制度完善作出《决定》具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宪法第62条第2项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赋予全国人大宪法监督的职权。宪法是主权的最高体现,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维护国家主权,首先要维护宪法权威与尊严。长期以来,对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最高法律效力,香港社会存在认识偏差,缺乏高度的共识,由此出现了将宪法和基本法对立、相互隔离甚至以基本法替代宪法等现象。基于宪法监督机关的地位,全国人大有宪制权力,也有宪制义务监督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包括基本法规定的选举制度运行是否符合宪法。同时,全国人大行使宪法第62条第16项规定“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以应对国家生活的变化,始终保持全国人大对国家重大问题的决定权。《决定》还指出以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作为依据。基本法是全国人大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律,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化,全国人大有权依据基本法对完善选举制度作出决定。香港国安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制定的法律,通过一系列“根本性条款”的规范再造,构建了香港基本法与香港国安法之间的特殊规范逻辑链条,体现了香港国安法的特殊性质与功能。因为基本法第1条和第12条是有关国家主权和特别行政区法律地位的核心规范,构成基本法规范体系的基础。选举制度完善关系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关系香港的繁荣稳定,这种核心利益体现在香港国安法之中,有必要成为《决定》的依据之一。总之,全国人大作出《决定》的宪法和法律依据是明确的,由此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
中央享有并行使
完善特区选举制度的主导权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中央有宪制责任推动特区政治体制向著有效运作和渐进民主的目标发展,从而保证“一国两制”实践和香港基本法的正确实施。选举制度是香港特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宪法和基本法推动香港选举制度改革,是对特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是行使国家主权的具体体现。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在本质上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特殊性在于,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授权享有高度自治权。香港基本法在第二章“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中明确划分了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各自负责管理或享有的职权,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体现为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香港基本法在第四章“政治体制”第45条和第68条分别规定了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的方式、原则、目标,具体办法则由附件一和附件二分别作出具体的程序和制度设计。因此,香港政治体制所据以产生的香港选举制度属于中央管理的事务,而不属于香港高度自治范围的事务。香港选举制度的完善由中央(全国人大)根据宪法和基本法并按照香港的实际情况决定启动。中央主导香港选举制度改革是中央行使对香港全面管治权的具体体现。全国人大决定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方式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通过香港基本法作出规定。其直接依据是香港基本法序言第三段和第11条第1款。基本法序言第三段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以保障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第11条第1款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有关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政策,均以本法的规定为依据。由此可知,特别行政区制度必须以香港基本法为依据,而不得违背基本法。二是通过符合基本法的其他法律或决定对基本法确立的特别行政区制度作出发展和完善。这种方式的特点在于,并不依据基本法第159条启动对基本法的修改程序,而是通过全国人大的有关决定实现对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完善与发展。例如,香港回归以前,全国人大通过《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对特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的产生机制和原则作出了规定。2020年5月28日,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对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进行了原则规定和制度设计。
当务之急是在法治的轨道上修改完善选举制度,填补选举制度漏洞,筑牢选举制度屏障,确保“爱国者治港”。图为香港小朋友挥舞国旗和区旗
完善选举制度应体现社会整体利益和
维护行政主导制
《决定》在完善选举制度方面设计的重要制度机制是“设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的选举委员会”,由选举委员会负责选举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部分议员,以及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等事宜。 选举委员会选举立法会议员,并不是新建立的机制,实质上是根据新情况,恢复其曾经承担的职能,是一种新型的选举委员会。按照新的选举委员会设计,立法会的部分议员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这有助于在立法会形成稳定的力量,消除“政治碎片化”,维护基本法确定的行政长官主导制。回归以来,香港社会一直存在所谓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之争,但包括立法会议员在内的各方都在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内活动。然而近年来,香港政治局势日趋复杂,社会撕裂不断加重,“政治碎片化”现象愈发明显。主要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分歧不断增加,在立法会内部的分歧愈发严重;不同势力之间立场对立加深,反对派在立法会多次恶意“拉布”,立法会的正常议事时常遭到破坏,政府高效施政受到阻扰。基本法起草过程中,曾有人主张香港效仿英国实行议会内阁制,有人主张采用美国“三权分立”体制,也有人认为香港可采用内地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基本法起草者经过反复权衡和研究,根据“一国两制”方针和中英联合声明,考虑香港的现实情况,设计出了现行香港特区政治体制,即行政主导制。在此体制下,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同时司法独立。这是“一国两制”下适合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方政权形式。从行政主导表现看,行政长官在政治体制架构设置及运行中处于主导和核心位置,行政长官是整个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享有超出行政机关首长的广泛权力。
从基本法条文看,行政主导制有坚实的法律依据。基本法不仅从整体上确立了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同时以20多个条文具体规定了行政主导制的原则与架构。比如,基本法第四章“政治体制”共六节,分别涉及行政长官、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区域组织与公务人员。其中,第一节是行政长官,第二节是行政机关。从法律文本对不同机关顺序的安排以及条文内容看,行政长官与行政机关在政治体制中居于特殊地位。从具体条文规定看,如基本法第43条和第60条明确规定,行政长官不仅是特区政府的首长,也是特区的首长,行政长官代表特区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一代表”、“双首长”和“双负责”,集中体现了行政长官在特区政治体制中的核心地位和特殊重要性。
确保“爱国者治港”是
完善选举制度的必然要求
“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前提和基础。邓小平作为“一国两制”的设计者,他从政治家的眼光反复强调爱国者治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只有爱国者治港,才能确保国家主权,保证政权的安全性。如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管治权落到反中乱港分子,或者是外国的代理人手中,香港市民无法安居乐业,甚至会危及到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2021年1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听取林郑月娥述职时指出,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这是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事关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这为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爱国者治港”既是对作为治港者的政治伦理要求,也是宪法、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明确要求。如宪法第5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宪法第5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基本法第104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在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拥护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特别行政区。2016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104条作出解释,进一步明确宣誓效忠是参选或者出任公职的法定要求和条件。香港国安法第6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参选或者就任公职时应当依法签署文件确认或者宣誓拥护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特别行政区。2020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因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寻求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干预特别行政区事务,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不符合拥护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一经依法认定,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这些规范实际上构成判断爱国者的法律标准,使“爱国者治港”成为清晰可辨的法律要求。“爱国者治港”作为治港者的政治伦理与法律要求,理应成为特别行政区公职人员的自觉行为准则。爱国者“起码都有民族自豪感”,具有基本的国家认同与国家意识。习近平主席曾指出,“一个人不爱国,甚至欺骗祖国、背叛祖国,那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丢脸的,也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充满民族自豪感和具有国家认同的人,必然诚心诚意地拥护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维护国家统一、主权与安全,同破坏国家统一与安全的行为作斗争。代议机关中存在不同政治立场和意见分歧是正常的,也是现代代议政治的重要特征,但每个立法会议员都必须在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内活动,不能滥用议员职权扰乱立法会的有效运作和破坏基本法确定的政治体制的有效运行,更不得利用议员职权从事对抗中央政府和支持“港独”等非法活动。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是基本法的核心要义,是作为爱国者的所有公职人员的基本要求。近年来,“一国两制”实践中出现了种种政治乱象,暴露出香港民主政制,特别是选举制度运行存在漏洞和短板,集中体现在有些人模糊、冲击或者抹煞“爱国者治港”这一根本原则。一些反中乱港分子企图通过组织策划或参与实施所谓“35+”“真揽炒十步”等政治阴谋,利用现行选举制度漏洞,取得立法会的控制权,进而瘫痪特区政府并最终夺取香港管治权。一些立法会议员利用议员身份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寻求外国或者境外反华势力干预香港特区事务。还有一些区议会议员利用区议会平台煽动暴力、宣扬“港独”,谋取政治私利,严重扭曲了区议会的非政权性区域组织的性质以及增进地区公共利益和市民福祉的功能。这些在民主政制发展中出现的各种乱象直接危及“爱国者治港”这个根本原则,冲击破坏特区以行政长官为主导的政治体制,对抗中央政府管治权威,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从根本上威胁著国家主权和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因此,我们需要从完善选举制度入手,使选举制度回归到基本法所确定的原则和轨道上来,为“爱国者治港”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事实告诉我们,选举制度设计是否科学,运用是否得当,直接影响著什么样的人进入治港行列、掌握政权的问题。选举是实现政治利益的一种手段,而谁掌握政权是目的。从这种意义上讲,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当务之急,是在法治的轨道上修改完善选举制度,填补选举制度漏洞,筑牢选举制度屏障,确保“爱国者治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