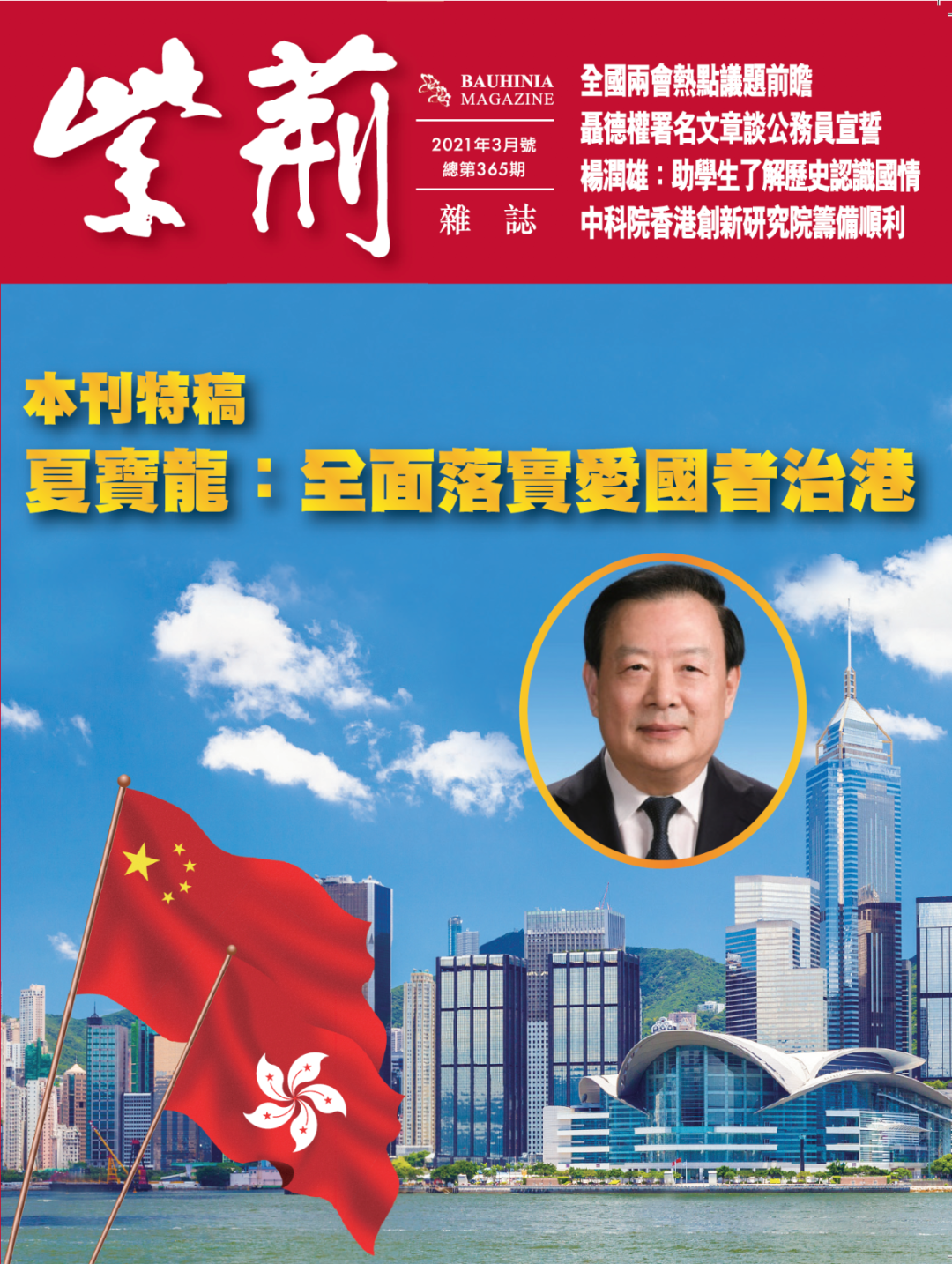任何社会必须根据自身实际不断变革、积极探索,从而找到切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才能因应历史变化、应对时代挑战稳健地前行。香港也不例外。鉴于香港现时深层次矛盾不断加深的局面,我们应该对深刻影响香港的“无形之手”等新自由主义学说进行反思,同时“祭出”我们开拓创新、积极有为的“有形之手”,并努力将“有形之手”以及“无形之手”有机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创造性地探索出一个合乎香港实际的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模式。
文|香港 谭耀宗

谭耀宗
变革香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长期以来,香港社会的确积累了很多深层次问题。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香港的宏观经济结构过分单一,资本资源过度集中,物价水平高居不下,产业活力不足,导致部分市民始终无法共同受惠于经济繁荣。从公平角度来看,香港的一次分配机制严重僵化,社会上流动力不足,贫富之间差距较大,社会矛盾日增,导致市民大众普遍缺乏自身向上的发展机会。
面对着来自现实生活的巨大压力,不少香港市民难免陷入无助、悲观和抱怨的负面情绪之中。我们认为社会管治者应当充分注意市民的实际需要并始终致力从根本上解决香港的种种深层次问题,只有民生得到改善,香港才能长治久安,“一国两制”才能行稳致远。
当然,香港的深层次问题是多因多果、相互联系的,我们不能把问题看得过分简单化。经济正义以及公平效率是我们提出变革香港所要追求的主要目的之一;透过经济多元发展、变革税制、设计有效的二次分配机制等多种实际方式,我们希望逐步缓解深层次矛盾,让每一个市民达成美好家庭生活的良好愿望,让每一个青年追逐那片属于自己的人生理想。

1月31日,香港民建联举行记者会,倡议“变革香港”(图:香港民建联官网)
应该探索建立香港特色资本主义
提到资本主义,大家马上就会想起亚当斯密提及的“无形之手”。可能是由于香港人长期以来深受“无形之手”等新自由主义学说的影响,每当有人提出政府应当在宏观经济调控上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时,都必然会在社会上引起很多不同的意见。事实上,香港社会对于“无形之手”的理解还是较为片面的,亚当斯密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一再强调必须要守护公平和促进公正,并认为只有在公平和公正的前提底下,“无形之手”才能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香港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路上却是忽略了公平公正的重要性,片面强调自由的结果是反而造成了寡头资本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等深层次矛盾不断加深的局面。
我们国家在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同样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但中央从一开始就明确强调要兼顾效率和保障公平,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从国家的发展中分享到果实。所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始终是内地政府不断向前发展的施政目标。未来香港的资本主义发展也必须要朝著公平公正这个大方向继续深化前进,而变革香港的大方向可以考虑借鉴内地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整体思维。
内地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央始终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判断我们国家的发展阶段,重点围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来制定政策。国家宪法序言中准确指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为国家解决一系列经济、民生问题提供了指导性方向。我们国家不断实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正正是当代中国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长期以来,香港社会只片面强调基本法第五条所列明的“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却没有以阶段划分来考虑现在香港究竟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什么发展阶段?也没有思考过到底什么样的资本主义模式才最适合香港。“资本主义”是一个较大的概念,而具体的实现形式在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是根据自身发展状况来决定的,如欧洲出现了福利国家的模式、新加坡出现了“威权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等。
鉴于香港现时深层次矛盾不断加深的局面,我们应该将“有形之手”以及“无形之手”有机结合起来,取长补短,综合地探索出一个合乎香港实际的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模式。
可推行“公有私营”方式
“积极不干预”“小政府大市场”“自由放任”等管理哲学无疑曾经是充分调动起香港发展的积极性,和确实曾经是基本支撑着香港辉煌的栋梁柱。然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就已经向世人证明了市场失灵的后果,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从此一蹶不振,都开始转移目光并注重政府在调控经济中的作用。我们认为,在一些涉及重大民生以及关乎社会发展的主要生活必需品上,政府不应该采取全盘“私有私营化”的政策,反而可以研究进行“公有私营”的变革,并探讨在市场经济模式中如何适度提升主要生活必需品“公有私营”的市场占比。我们提出“公有”是强调行政主导下政府具有最终决策的绝对话语权,提出“私营”则是保持企业经营效率所需的一贯高水平。
提升“公有私营”的市场占比还有一个额外好处,当政府向市民提供更多收费产品或服务的时候,该收费产品或服务将来便可以作为一个调节经济周期起伏的有效手段,简单来说,经济上行时多收,经济下行时少收,这对属于完全外向型的香港经济来说,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无疑便能够得到多一个调节的有效手段。假如政府在港铁等机构中有更大的话语权和最终的决策权,在行政主导下,交通费直接减价而不是以现行各种复杂的折扣模式,政府便能精准地向市民提供普及而平等的实惠。如能这样,在经济危机突然来袭时,政府便能快捷地帮市民缓解生活重担之所急了。我们认为其他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以及公共屋邨的商场街市管理和楼宇屋苑管理等似乎也可以做类似的考虑。
可通过改善二次分配促进公平
关于二次分配,除了字面上的一般含义之外,我们更想强调的是香港社会需要改变过往对社会福利的陈旧思维,和需要适度包容以拓宽税基来支持福利变革的具体建议。
香港社会一直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加上社会文化一直认同“有手有脚唔需要靠政府”的思维,因此香港的社会福利至今只是提供最基层的保障,属于“残补式”的福利模式。香港缺乏类似养老保险、退休保险、失业保险等基本的社会保险模式,市民反而需要依靠家庭或者从市场购买取得这些福利;所以我们认为,特区政府需要研究以政府、市民共同供款的社会保险模式,为市民提供更广泛的基本保障。
社会上对于税制变革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其实税制最重要的作用是进行调节。税制对社会总体供求、居民收入、居民消费以及产业结构都有不可或缺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在调节居民收入的环节中,税制一方面以发挥二次分配的调节作用来促进社会的公平,另一方面亦能够为福利变革提供财政的基础。
进一步来说,税制变革还有产业结构的重要调节作用,比较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香港宏观经济结构过分单一、资本资源过度集中和产业活力不足等深层次问题。特区政府按产业政策的实际需要,采取税务政策和财务政策双管齐下方式,可以引导市场发展方向,促进产业结构总体的协调发展。
我们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税制和福利变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香港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产业结构总体的协调发展;税制和福利变革最终受益者将会是全体香港市民。我们希望特区政府在研究税制和福利变革的时候,能够平衡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关系,始终保持香港社会整体不断向前发展的无限活力!
(作者系香港民建联会务顾问)
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1年3月号
监制:左娅、连振海
编辑:哈元源、莫洁莹
校对:李博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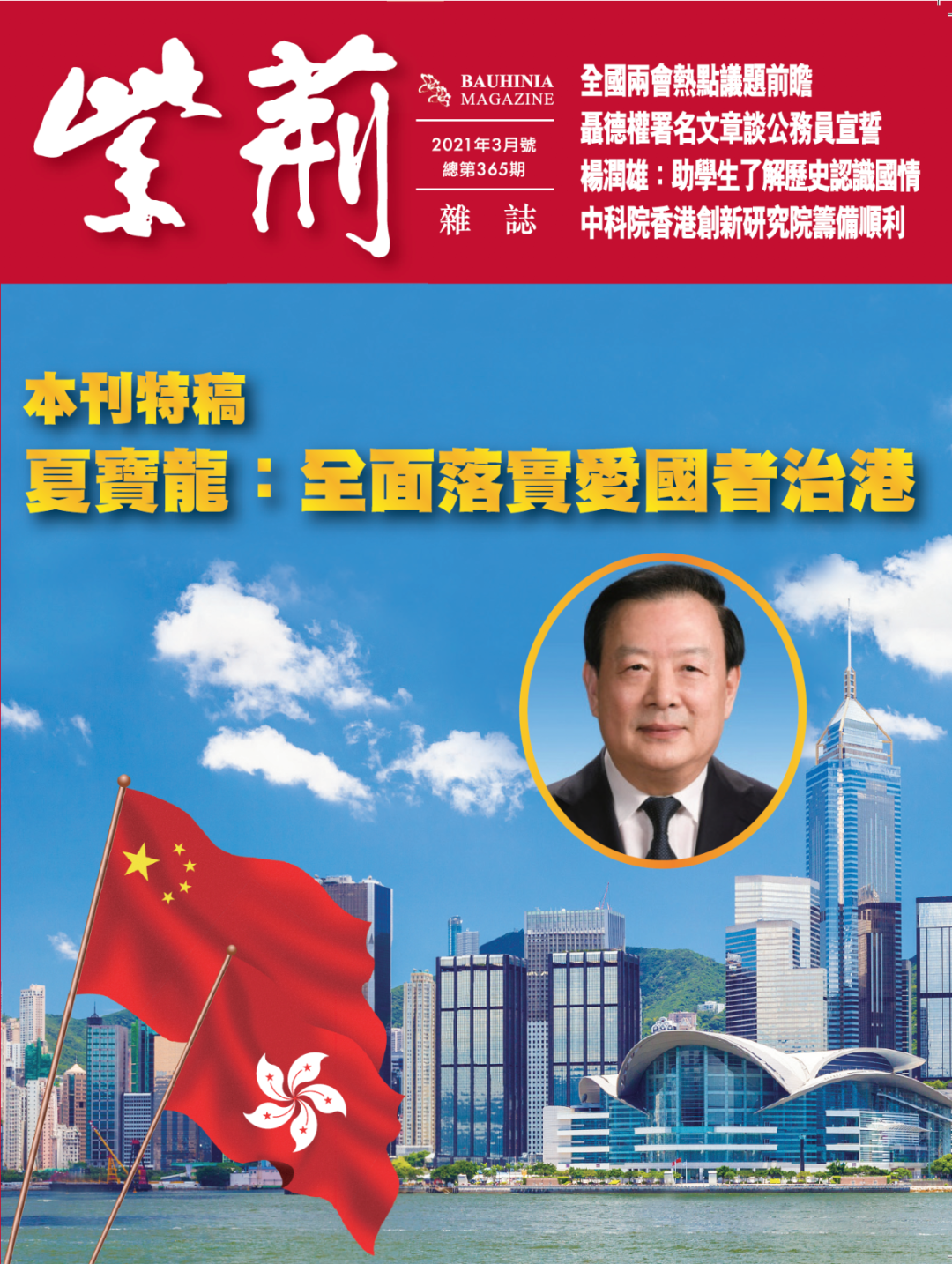
扫描二维码分享到手机
![]()
+关注

任何社会必须根据自身实际不断变革、积极探索,从而找到切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才能因应历史变化、应对时代挑战稳健地前行。香港也不例外。鉴于香港现时深层次矛盾不断加深的局面,我们应该对深刻影响香港的“无形之手”等新自由主义学说进行反思,同时“祭出”我们开拓创新、积极有为的“有形之手”,并努力将“有形之手”以及“无形之手”有机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创造性地探索出一个合乎香港实际的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模式。
文|香港 谭耀宗

谭耀宗
变革香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长期以来,香港社会的确积累了很多深层次问题。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香港的宏观经济结构过分单一,资本资源过度集中,物价水平高居不下,产业活力不足,导致部分市民始终无法共同受惠于经济繁荣。从公平角度来看,香港的一次分配机制严重僵化,社会上流动力不足,贫富之间差距较大,社会矛盾日增,导致市民大众普遍缺乏自身向上的发展机会。
面对着来自现实生活的巨大压力,不少香港市民难免陷入无助、悲观和抱怨的负面情绪之中。我们认为社会管治者应当充分注意市民的实际需要并始终致力从根本上解决香港的种种深层次问题,只有民生得到改善,香港才能长治久安,“一国两制”才能行稳致远。
当然,香港的深层次问题是多因多果、相互联系的,我们不能把问题看得过分简单化。经济正义以及公平效率是我们提出变革香港所要追求的主要目的之一;透过经济多元发展、变革税制、设计有效的二次分配机制等多种实际方式,我们希望逐步缓解深层次矛盾,让每一个市民达成美好家庭生活的良好愿望,让每一个青年追逐那片属于自己的人生理想。

1月31日,香港民建联举行记者会,倡议“变革香港”(图:香港民建联官网)
应该探索建立香港特色资本主义
提到资本主义,大家马上就会想起亚当斯密提及的“无形之手”。可能是由于香港人长期以来深受“无形之手”等新自由主义学说的影响,每当有人提出政府应当在宏观经济调控上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时,都必然会在社会上引起很多不同的意见。事实上,香港社会对于“无形之手”的理解还是较为片面的,亚当斯密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一再强调必须要守护公平和促进公正,并认为只有在公平和公正的前提底下,“无形之手”才能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香港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路上却是忽略了公平公正的重要性,片面强调自由的结果是反而造成了寡头资本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等深层次矛盾不断加深的局面。
我们国家在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同样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但中央从一开始就明确强调要兼顾效率和保障公平,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从国家的发展中分享到果实。所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始终是内地政府不断向前发展的施政目标。未来香港的资本主义发展也必须要朝著公平公正这个大方向继续深化前进,而变革香港的大方向可以考虑借鉴内地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整体思维。
内地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央始终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判断我们国家的发展阶段,重点围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来制定政策。国家宪法序言中准确指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为国家解决一系列经济、民生问题提供了指导性方向。我们国家不断实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正正是当代中国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长期以来,香港社会只片面强调基本法第五条所列明的“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却没有以阶段划分来考虑现在香港究竟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什么发展阶段?也没有思考过到底什么样的资本主义模式才最适合香港。“资本主义”是一个较大的概念,而具体的实现形式在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是根据自身发展状况来决定的,如欧洲出现了福利国家的模式、新加坡出现了“威权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等。
鉴于香港现时深层次矛盾不断加深的局面,我们应该将“有形之手”以及“无形之手”有机结合起来,取长补短,综合地探索出一个合乎香港实际的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模式。
可推行“公有私营”方式
“积极不干预”“小政府大市场”“自由放任”等管理哲学无疑曾经是充分调动起香港发展的积极性,和确实曾经是基本支撑着香港辉煌的栋梁柱。然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就已经向世人证明了市场失灵的后果,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从此一蹶不振,都开始转移目光并注重政府在调控经济中的作用。我们认为,在一些涉及重大民生以及关乎社会发展的主要生活必需品上,政府不应该采取全盘“私有私营化”的政策,反而可以研究进行“公有私营”的变革,并探讨在市场经济模式中如何适度提升主要生活必需品“公有私营”的市场占比。我们提出“公有”是强调行政主导下政府具有最终决策的绝对话语权,提出“私营”则是保持企业经营效率所需的一贯高水平。
提升“公有私营”的市场占比还有一个额外好处,当政府向市民提供更多收费产品或服务的时候,该收费产品或服务将来便可以作为一个调节经济周期起伏的有效手段,简单来说,经济上行时多收,经济下行时少收,这对属于完全外向型的香港经济来说,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无疑便能够得到多一个调节的有效手段。假如政府在港铁等机构中有更大的话语权和最终的决策权,在行政主导下,交通费直接减价而不是以现行各种复杂的折扣模式,政府便能精准地向市民提供普及而平等的实惠。如能这样,在经济危机突然来袭时,政府便能快捷地帮市民缓解生活重担之所急了。我们认为其他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以及公共屋邨的商场街市管理和楼宇屋苑管理等似乎也可以做类似的考虑。
可通过改善二次分配促进公平
关于二次分配,除了字面上的一般含义之外,我们更想强调的是香港社会需要改变过往对社会福利的陈旧思维,和需要适度包容以拓宽税基来支持福利变革的具体建议。
香港社会一直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加上社会文化一直认同“有手有脚唔需要靠政府”的思维,因此香港的社会福利至今只是提供最基层的保障,属于“残补式”的福利模式。香港缺乏类似养老保险、退休保险、失业保险等基本的社会保险模式,市民反而需要依靠家庭或者从市场购买取得这些福利;所以我们认为,特区政府需要研究以政府、市民共同供款的社会保险模式,为市民提供更广泛的基本保障。
社会上对于税制变革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其实税制最重要的作用是进行调节。税制对社会总体供求、居民收入、居民消费以及产业结构都有不可或缺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在调节居民收入的环节中,税制一方面以发挥二次分配的调节作用来促进社会的公平,另一方面亦能够为福利变革提供财政的基础。
进一步来说,税制变革还有产业结构的重要调节作用,比较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香港宏观经济结构过分单一、资本资源过度集中和产业活力不足等深层次问题。特区政府按产业政策的实际需要,采取税务政策和财务政策双管齐下方式,可以引导市场发展方向,促进产业结构总体的协调发展。
我们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税制和福利变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香港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产业结构总体的协调发展;税制和福利变革最终受益者将会是全体香港市民。我们希望特区政府在研究税制和福利变革的时候,能够平衡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关系,始终保持香港社会整体不断向前发展的无限活力!
(作者系香港民建联会务顾问)
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1年3月号
监制:左娅、连振海
编辑:哈元源、莫洁莹
校对:李博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