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晓宇 I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生
《紫荆论坛》专稿/转载请标明出处

2020年内地肖战事件中粉丝群与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中反修例人士,其发动网络攻击的手段,显示了两种在网络上组织并行动的方式。本文将试图分析这两种网络组织方式的特点及其表现形式,并讨论其对政治形势的可能影响。
一、肖战事件中的「线球」现象
内地知名男演员肖战的粉丝们在事件中展示了粉丝集团的能量。因为不满以肖战作为角色的一篇文章,肖战的粉丝群集体举报了登出这一篇文章的网站,并成功使其被屏蔽。之后,数位微博博主在表露对肖战及其粉丝不满后,遭到了大量辱骂和人肉威胁,最终退出微博。在现在的网络上,这种「一群人,在无利可图的环境下,抱成了一个集团,去共同行动」已经成为了一种网络现象。如果将互联网比作一张四通八达的巨网,那么网络上的这些集团,便是巨网上的一个个线球。在明星粉丝中,这种「线球」出现得尤其频繁。「线球」由两个特点构成,一是其成员思想的趋同性,二是其成员对排异的热衷性。趋同性带来了共同行动的土壤,对排异的热衷带来了行动的原因。
(一)「线球」的趋同性
趋同性首要的一个成因便是回音室效应。回音室效应是讨论网络媒体时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汇。它的大意是,人会更多关注和自己意见相近的声音,而在网络环境中,和自己意见相近的声音更容易被发现并获得关注,导致人们最终耳朵里充斥的都是类似的声音,而与自己相左的意见则不会出现。这些近似的声音使人们对自己之前的意见更加确信,从而失去了与其他不同的意见交流的机会。这就好比一个人在一个回音室中发声,回音室传来的都是他本人的回音,但他却不知道,并以为这些回音就是所有外界的意见,而外界则都和他一样。
现在,许多网站的算法都加剧了这一效应。通过分析用户之前的搜索偏好,网站会自动向用户推送他可能会喜欢的内容,从而更多的将用户的注意吸引到和他相近的意见上。肖战事件主要的舞台——微博,不仅有算法推荐,还有超话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超话就是人工制造的巨大回音室。只有关注了超话的人才能在超话中发表言论,而超话的管理员「主持人」则有权力任意地屏蔽他超话中的帖子和用户。因此,不符合主持人要求的声音无法在超话中出现,超话成为了主持人和与他相近的人的回音室。
除了个人和算法对信息的筛选之外,语言也帮助塑造了回音室。以明星粉丝为例,很多粉丝群体都对他们的明星有独特的称呼,比如肖战就被叫做「兔兔」,而粉丝称呼自己为「小飞侠」。除了粉丝以外,很多亚文化群体都有他们独有的名词和梗,如果不是对这个群体深入了解的人,可能看这个群体内的人对话,只能是半懂不懂,更别提互相交流了。如果说算法和个人偏好构成了回音室的四壁,那么语言就构成了回音室的屋顶。在其中,人们能听到的不同声音极为有限。
语言的另外一个效应在于趋近人们的想法。人的思考以语言为载体,依托于词汇,使用语言相近的人思考方式不会偏差巨大。语言中出现频率较低的词汇,它的所指在思考中也不会高频出现;而语言中高频出现的词汇,它的所指则会被优先使用。因此,使用语言相近的人,思考方式很可能比使用语言偏差巨大的人更加接近,从而进一步放大回音室效应。
(二)「线球」的排异性
排异性则来自对自己身份认同的需要。马歇尔.麦克卢汉在采访中曾说,我们在被电子媒体部落化后,都将如同小母鸡潘妮一样疯狂的四处打转,寻找我们过去的身份,并在这个过程中释放巨量的暴力。身份认同是「线球」形成的重要原因。现代社会原子化的人,在寻求身份的过程中,发现了成为「线球」的一部分这条捷径。还有什么比加入网络上的一个「线球」成本更低的事呢?与低廉的加入成本相比,进入「线球」后一个人所能得到的认同,对自己身份的肯定,可以说高到不成比例。
身份的认定需要边界。假设全世界所有人都成为了中国人,那中国人这个身份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每一个「线球」,在不断扩张并吸取新成员时,也在不断的排异。肖战事件其实起源于肖战粉丝内部的矛盾。一名肖战粉丝以肖战为角色写了一篇小说,而这篇小说中名为肖战的角色遭到了其他粉丝的反对,导致小说发表的整个平台被举报屏蔽。这个小说作者就是被排出的「异」,他就是举报他的那一部分肖战粉丝所组成的「线球」的边界。 因此,「线球」是在不断排异中的。在吸收与排出的过程中,「线球」成员的认同必然越来越强烈,思想越来越趋同,而排异行动本身带来的攻击性,也成为了「线球」的一部分。
拥有了强烈的认同和相近的思想后,「线球」变得有组织起来,拥有了比其他无组织的网民强大许多的力量。在意识到自己拥有力量后,「线球」的攻击性便不仅针对它体内的异,也针对它体外的异。在这个阶段中,「线球」就成为了一个具有社会影响的组织。通过集体评论、谩骂以及人肉等手法,一个「线球」轻则可以逼迫他人道歉,重则可能影响他人现实生活。
(三)「线球」的表现形式
互联网对交流的加速,除了方便用户找到「同」之外,也方便自以为思想相近的人们找到他们之间的「异」。在交流不充分的情况下,两个思想相近的人可以很快发觉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而忽略他们的不同。因此,一个有系统思想的人找到一个类似的人,是有可能的。但是在交流非常方便的网络上,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观点上的不同。在最好的情况下,拥有不同观点的人可以求同存异;在最坏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认同其他人,随之而来的是极端的原子化,所有个人都是网络上的孤岛。总体而言,思想越成系统的人,越难以在网络时代认同别人,因为在大量的交流下,他会发现别人的观点总会在某个地方违背自己的原则。因此,即使有大量反对「线球」的个人,由于无法互相认同,难以形成组织,即使反对者数量庞大,也往往不是对手。因此,一个「线球」几乎在网上无往而不利,通常只有另一个「线球」才可以与其抗争。
「线球」是否仅仅存在于追星粉丝群体当中呢?也未必如此。形成「线球」的,如上所述,是一个具有相近思考方式、拥有强烈排异愿望的群体。实际上,很多互联网亚文化社群,或者某些网站/论坛的用户,都可能形成「线球」。这些集体拥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规矩和语言,他们的领导者,比如论坛的管理员,正如微博超话的主持人一样,极其愿意执行他们的规定。不能遵守规定的,都被排出了集体。而不能掌握这些集体语言的,根本无法进入集体。互联网本身的回音室效应,配合独特的规定和语言,制造了思考方式接近的人。而对自己集体的认同,和管理员对异端的删除,带来了强烈的排异愿望。以上只是一个追星粉丝群体的例子,实际上,可能形成「线球」的网络群体,并不止这些。
二、「修例风波」中的「虫群」现象
在「线球」之外,还有一种组织方式,就是香港「修例风波」中反修例人士使用的,依靠著一个共识发动的,去中心化抗争策略。「线球」是一个只有单一声音的,高组织度的集体,就如同肖战的粉丝一样,可以说令行禁止。在粉头的带领下,他们可以对一个人进行网络暴力,也可以对人表示支持。甚至可以在进行网络暴力之后,发现不对,立刻采取一个集体急刹车,反过来对这个人表示支持。沈逸教授在前一段时间和肖战粉丝在评论区进行了论辩,开始时,他的评论区充满了人身攻击和质疑。后来,在得知他是研究网络安全的专家后,肖战的粉丝马上刹车,而且利用微博的搜索机制,迅速地把沈逸教授和粉丝的论辩转化成立一个误会。由于肖战粉丝对搜索机制的利用,一个不了解微博搜索机制的人,在搜索「肖战 沈逸」时,都不会看到粉丝和沈逸之间发生过的具体论辩,而只会看到肖战粉丝想让他们看到的。这一切发生得很快很整齐,很有组织。
反修例人士则不是这样。他们理论上也有一个中心,「民间人权阵线」。而反修例暴乱的主要组织方式,是由随机的愿意行动的人,在LIHKG( 连登)和Telegram上发布意见。因时间、内容等缘故,受到点赞、讨论的意见,会被讨论进一步放大,进入更多人眼里,从而引发更多讨论,受到更多点赞。在这条意见的受众滚雪球一般扩大后,就形成了一个「共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个共识,并不是所有人对这个「共识」的理解都一样。但是,只要有足够多的看到这条共识的人,愿意依照他们对这条共识的理解去行动,那么一次攻击就发生了。这个攻击往往不像「线球」的攻击一样,那么整齐划一,所有人都做相近的动作。在香港「修例风波」所引发的暴乱中,有非暴力主义者,有暴力分子,有准备各种武器的破坏分子。所有人都为了共识而行动,而没有人有权力去指导、约束另一个人,这包括共识的创造者。在发表共识后,他的权力就与其他人等同了,他没有对共识的解释权。

2019 年 11 月 17 日,在香港理工大学外,暴徒纵火、打砸并和警方对峙(图:新华社)
如果说肖战的粉丝像一个滚来滚去的线团,那么反修例人士则像是科幻小说中的虫群。一个探路虫发现了目标,释放了信号。这个信号,被足够的其他虫族单位捕捉到后,便被不断放大,最终找来虫群的主力对目标进行攻击。这种去中心化、无组织的行动,难以被阻止。能被大量人看到的共识,一定很简单,并且有大量的理解空间,就如同约法三章一样。一个事无巨细的长贴,在无数讨论类似内容的帖子掩盖中,从一开始就不会有足够的人有耐心读下去,也就不会被众人的视线捕捉为共识。试图阻止「虫群」行动的人,面对的是众多方法不可捉摸的个人。任何极端的可能性,都会在无数没有约束的个人之中出现。反修例人士冲击香港机场,就是一个例子。在共识形成的讨论中,很多人出于各种理由,最后没有同意冲击机场,但这并不影响什么。在同意冲击的人足够多了之后,冲击便开始了。
内部分裂,和无法谈判,是「虫群」模式的问题。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对共识产生同样的理解,当分歧达到一定程度时,内部分裂成多个只同意某种对共识的理解派系便成为可能。而由于没有代表,和「虫群」谈判就意味著和每一个人单独谈判,因此谈判也并不可能。在肖战事件中,内地网络还出现一个反肖战运动,是在肖战粉丝发动举报后的2月27日开始的,因此也叫227。参加227的人,便可以说是一个「虫群」。他们没有组织,唯一的共识就是反肖战。众多个人,没有组织的以各种方式抵制肖战的商业行为。尽管肖战的粉丝是一个「线球」,大部分时候在互联网上无往而不利,227还是成功的对肖战的商业活动造成了一定打击。
三、「线球」与「虫群」现象带来的政治影响
是否「线球」和「虫群」,就如同肖战粉丝和227一般水火不容?是否「线球」只是一个娱乐圈内的粉丝行为,与政治无关呢?并非如此。这两种组织方式,有时候可以组合起来,造成政治影响。
在美国达拉斯警局推出了一款app供用户举报抗议游行者后,韩国歌手粉丝向该app里上传了大量韩国歌手演唱视频,导致该app陷入崩溃状态。部分白人使用White Lives Matter(白人生命重要)标签发twitter,来反对近期的黑人运动。很快,这些人的twitter评论区也被韩国歌手视频占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俄克拉荷马举行了集会,但是大量韩国歌手粉丝预定了集会门票,却没有参加集会,据他们宣称,这导致实际参加集会的人数低于预期。韩国歌手粉丝的这些行为,证明了他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影响政治。
在以上事件中,参与这些活动的不止有韩国偶像的粉丝们。但是,首先发起活动,并使活动具有规模的,无疑是粉丝群体。个体在网络上的力量是微小的,一个人在手机app中刷无关视频,很容易被屏蔽,或者直接无视。但形成规模后,就可以吸引到群体以外的人注意,并形成一种潮流。也就是说,「线球」靠著自己强大的组织力,迅速吸引了足够的目光,形成了共识,以此将一次「线球」活动转变为了「虫群」活动。
本文无意对这两种网络组织方式作出道德判断,而只是希望指出这些现象。当今网络中,由于各种原因,布满了无数「线球」。由于「线球」思考方式趋同,一定程度上他们的行动是可预测的。同时,由于拥有组织性和攻击性,他们可以被用来对可能的对手发起攻击,攻击方式可能包括现在的人肉、谩骂、刷屏,也可能有更加先进的方式。单一的思考方式,导致「线球」面对某一种外界刺激,大概率会总是做出同一种反应,比如肖战的粉丝在见到不合他们心意的小说之后,集体举报了刊登小说的网站。而「虫群」的组织方式,也值得更深一步的思考。共识是怎么形成的?什么样的意见更容易形成共识?如果在将来的政治活动中,有人可以预测「线球」和「虫群」的反应,并给予相应的刺激,那么他们便在网络空间获得了相当的力量——足以让一部分人的声音被淹没的力量,正如韩国偶像的粉丝们与后来跟进的人淹没达拉斯警局的app一样。可以想见,在将来的舆论战和网络战中,对这两种现象的利用,可能是胜利的关键所在。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1年1-2月号第98-10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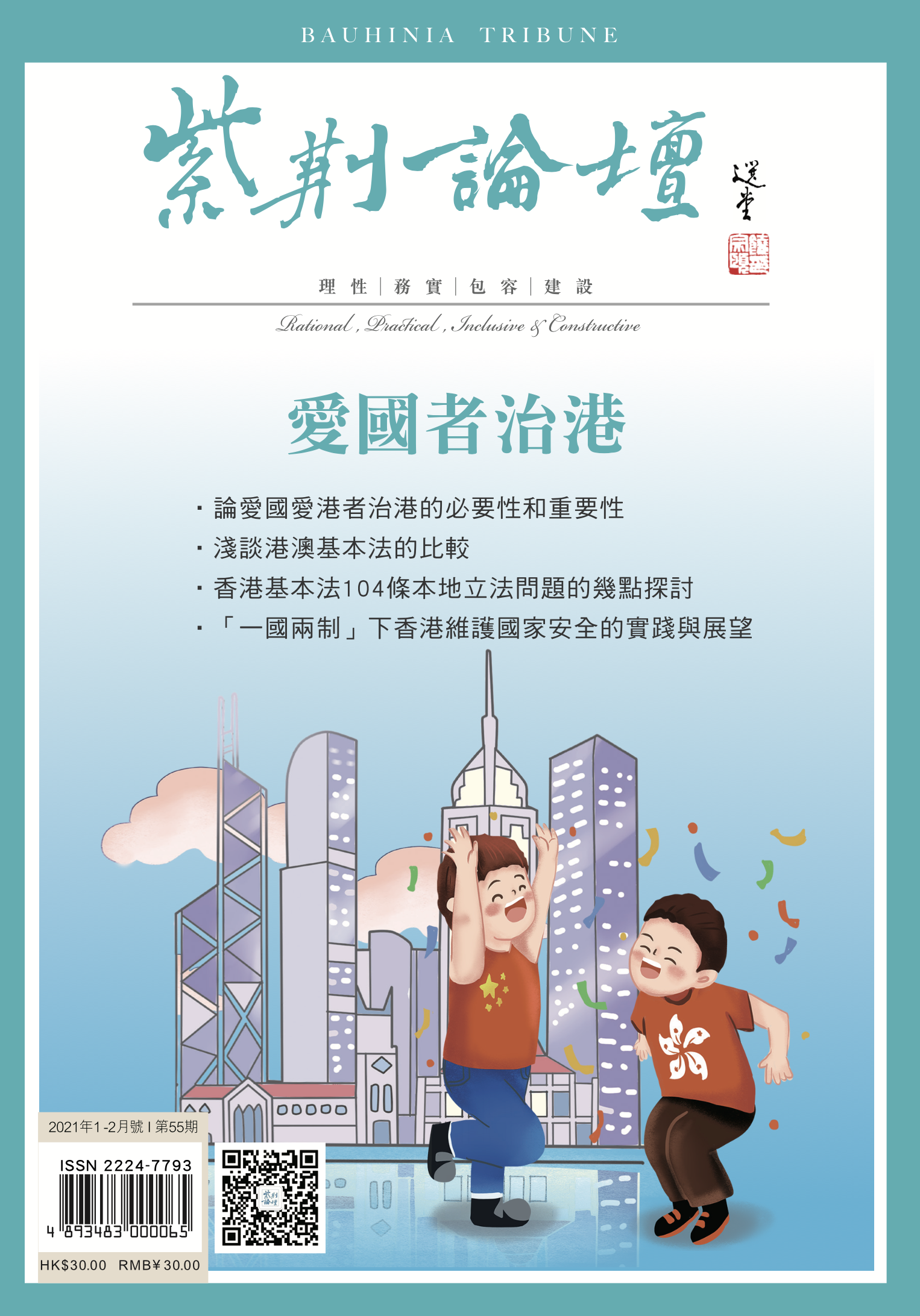
扫描二维码分享到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