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引业 I 重庆大学副教授、香港大学法学博士后
《紫荆论坛》专稿/转载请标明出处

从1985年全国人大批准《中英联合声明》,35年间,涉港「人大决定」共34个,决定主体有全国人大、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人大决定」在回归前、过渡期、回归后的三个时期分别起到奠基、过渡与「定海神针」的作用。35年间,「人大决定」被频繁地运用于处理「一国两制」实践与香港基本法实施中所遇到各种问题,行之有效、作用积极,确保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贯彻与行稳致远。事实雄辩地说明,「人大决定」是中央治港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甫一通过,立即引来反对派的抵制,以及有关合法性的质疑。英国外相多米尼克.拉布甚至公然宣称该决定「明显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这完全是对香港回归的历史缺乏基本了解,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涉港决定的历史缺乏基本认识所得出的错误结论。
事实上,在香港回归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就开始以「决定」的方式解决有关香港的问题。最早的涉港决定可以追溯到1985年全国人大批准《中英联合声明》的决定,到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35年间一共出台了34个涉港「人大决定」,大约每年1个。34个决定中,全国人大8个,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7个,全国人大常委会19个,占比分别为23.5%、20.6%、55.9%。回归前18个,回归后16个,占比分别为52.9%、47.1%。除2020年关于授权制定香港国安法的决定外,回归后其余的涉港决定全部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
全国人大、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时间顺序上大体呈现前后接替的关系,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这三类主体所作决定的历史性作用,那么依次是奠基、过渡与「定海神针」。不过,2020年5月全国人大出台的关于授权制定香港国安法的决定,亦被认为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一、回归前全国人大决定:奠基
1985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两个决定,分别是关于批准《中英联合声明》的决定,以及关于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决定。从国际法的意义上看,关于批准《中英联合声明》的决定具有批准国际条约的性质,但批准《中英联合声明》,实质上就是作出了以「一国两制」的方式收回香港的政治决定,因而又具有以决定实施「一国两制」以及如何实施「一国两制」的国内法性质。此一决定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解读:一方面,由全国人大作出批准决定,体现了中国以「一国两制」方式收回香港的国家意志;另一方面,则具有对外对内,特别是对香港民众的法律承诺。全国人大在通过批准《中英联合声明》决定的同时,还通过了关于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决定,规定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组成、地位事宜。鉴于香港基本法的宪制性,该决定实质上具有为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权和授权香港高度自治作准备的法政意义。
1990年4月4日,在表决通过香港基本法的同时,全国人大还通过了4个与此相关的决定:关于香港基本法的决定,实际上是对香港基本法的合宪性审查,旨在打消香港部分人士关于基本法可能因为被提起违宪审查而撤销的疑虑;关于设立特别行政区的决定,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起始运作时间和行政区划范围;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则正式启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的筹组事宜;关于批准设立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的决定,则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地位、职权、组成等事项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4个决定都是通过香港基本法的配套措施,具有为通过特别行政区制度具体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基础性作用。
随著香港回归日益迫近,为保证1997年能平稳过渡,全国人大又于1993年通过了一个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筹委会准备工作机构的决定,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提供了法律依据。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图为 2020 年 11 月 12 日,十多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举行记者会 (图:新华社)
二、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的决定:过渡
香港回归并非一路畅通,毫无波折。由自身使命及其职责所决定,当面临一些突发和紧急情况,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需要发挥决定的灵活性、针对性强的特点和优势,通过决定的方式及时处理有关问题。
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发布的7个决定中,具有浓厚的保障平稳过渡意义的有3个。1992年,新上任的总督彭定康单方面提出关于香港的「政改方案」,从而与基本法规划的政制背道而驰,这意味著港英时代的最后一届立法局议员无法自动过渡为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原先协定的「直通车」方案无法实施,香港平稳过渡面临严峻的挑战。在反复沟通、谈判无果的情况下,为避免香港在过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立法真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4年8月31日通过的《关于郑耀棠等32名全国人大代表所提议案的决定》中,申明了「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区议会于1997年6月30日终止」的立场,同时根据全国人大关于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授权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组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据此出台了关于设立立法会的决定以及关于设立临时性区域组织的决定。
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另一个具有浓厚过渡意义的决定,是关于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问题。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授权特别行政区就国家安全问题自行立法。1996年11月29日,港英政府单方面修改《刑事罪行条例》,声称虽然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授权特别行政区就国家安全事项自行立法,但这并不代表香港不能在1997年7月1日之前制定一些与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有关概念不符的法律。针对港英政府此一行为,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通过了关于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问题的决定,郑重声明「港英当局的这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的行为,明显违反基本法的规定,严重侵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并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来宣布「港英当局对《刑事罪行条例》修订的有关内容与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相抵触,自1997年7月1日起无效,不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定海神针」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香港的决定一共有19个,其中过渡期4个,香港回归后15个。过渡期的4个决定,分别是关于香港基本法英文本的决定、关于设立特区筹委会预委会的决定、关于郑耀棠等32名全国人大代表所提议案的决定,以及关于根据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条处理香港原有法律的决定。需要重点提及的是第四个决定,该决定最为典型地体现了对「一国两制」的贯彻和落实。一方面,因为恢复行使香港的主权,香港原有法律应当作出适当的改变;另一方面,因为实行「一国两制」,香港原有法律制度需要最大限度的予以保留。「变」与「不变」需要主权机关依据香港基本法决断,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决定的方式予以处理,正体现了此种精神。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回归前后法律制度的「变」与「不变」作出的恰当处理,既完成并体现香港的主权回归,又保持了香港的繁荣稳定,为香港社会的平稳跨越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定海神针」作用在香港回归后延续了下来,并突出体现于有关香港政制发展的决定中。香港回归后,有关政制发展的决定最为瞩目、最受关注。回归后香港的政制发展,集中体现于行政长官与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方面,也就是俗称的「双普选」问题。关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具体产生办法,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条和第六十八条都只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具体实施则由附件一、附件二加以细化规定。然而,附件一、附件二仅规定了2007年前的行政长官、2008年前的立法会的具体产生办法,第一任行政长官任期结束后,如何落实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八条,推动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双普选」就成了一个问题。为引导香港政制健康有序发展,基于中央对香港的政制发展享有主导权的认识,2004年4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主动释法,确立了修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五步曲」,并分别于2004年4月26日、2007年12月29日、2010年8月28日、2014年8月31日作出了4个关于「双普选」问题的决定。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香港社会诸如贫富差距过大、社会阶层固化等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加之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介入,各方势力博弈拉锯。在香港社会各界对行政长官选举办法无法达成共识,香港社会出现泛政治化倾向,进而有可能成为造成香港社会撕裂因素的关键时刻,中央政府没有随著反对派的旗帜起舞,而是保持足够的定力与耐心。一方面坚持对香港政制发展的主导权不动摇;另一方面坚持基本法规定的政制发展中的「实际情况」原则与「循序渐进」原则不动摇,以「人大决定」的形式「一锤定音」,在回应香港民众诉求的同时较好地维护了香港社会大局稳定。
此外,2020年5月全国人大作出关于授权制定香港国安法的决定,2020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某种程度上亦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综上所述,自1985年来的30余年间,「人大决定」被频繁地运用于处理「一国两制」实践与香港基本法实施中所遇到各种问题,行之有效、作用积极,确保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贯彻与行稳致远。事实雄辩地说明,「人大决定」是中央治港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中央正是以「人大决定」的方式一步步推动香港的顺利回归,推动「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落实落地;香港回归后,又以「人大决定」的方式不断化解「一国两制」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一个人、一个组织不能完全无视自己的历史,其存续发展必然具有某种历史的规定性。如果否认涉港「人大决定」的合法性,就无法解释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合宪性,无法解释香港基本法的合(宪)法性,就无法解释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合法性,香港基本法及其所确立的新宪制秩序就失去了根基。「为反而反」根本就不是讲不讲道理的问题,而是利益和立场的问题,是愿不愿讲道理的问题。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1年1-2月号第33-3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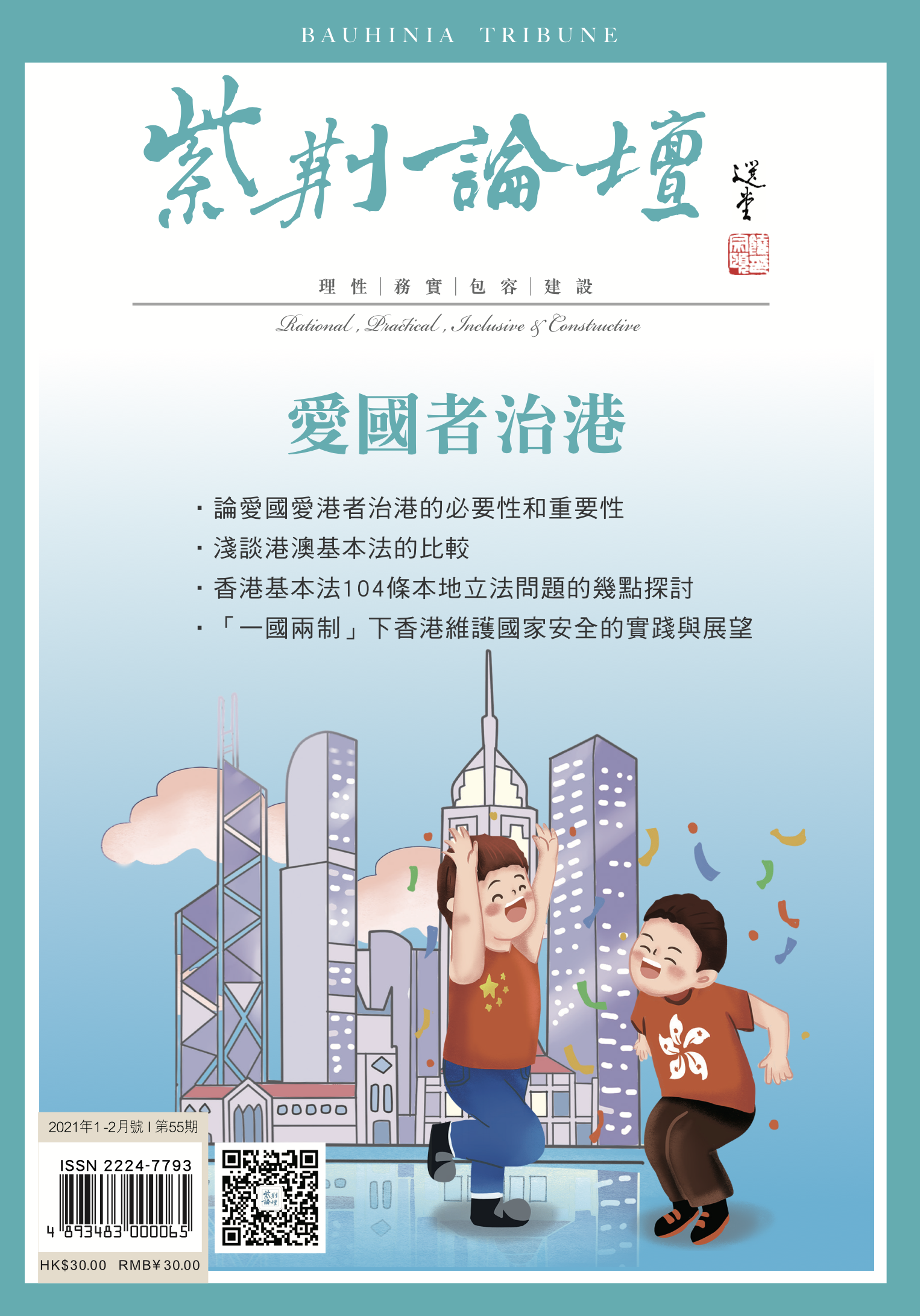
扫描二维码分享到手机














